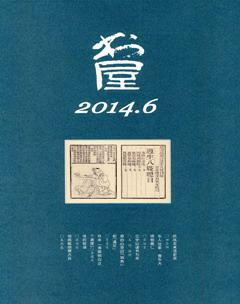立學以讀書為本
王郢++整理
去歲寒冬,本應是萬物休眠的季節。但是,兩位耄耋之年的學者,卻仍然在憂國憂民的思考著中國當前諸多的社會問題。一位是已經一百零一歲的著名歷史學家劉緒貽先生,另一位是八十一歲的武漢大學前校長劉道玉先生,他們既是師生關系,又是志同道合的多年摯友。他們思維清晰,精神矍鑠,應《書屋》雜志之約,就讀書生活、教育問題、知識分子的擔當以及當前國學熱的問題暢談了各自的看法。本刊幸而蒙愛,分四期刊登之,以饗讀者。
劉道玉:緒貽先生是我國著名的美國史學術大師,今天能夠與先生交流,是我一生最榮幸的事,將會受益無窮。北宋歐陽修四歲喪父,母親為他四處借書,他靠抄書和自學成為一代儒宗,是名聞遐邇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因而,他最懂得讀書的重要性,故發出了“立身以學習為先,立學以讀書為本”的醒世恒言。下面,我們請緒貽先生暢談他讀書的經歷、方法和經驗。
劉緒貽:讀書的問題就我來說,剛剛開始并非就是“樂淘淘”的。我小的時候,家里條件是很不好的,使得我最初讀書時,不利條件很多。第一,我父親雖然是一個小學教師,但當時孩子很多,有五個孩子,所以家境清貧。我家里也沒有什么書,只有一個大約半人高的書箱,只有這么一點書,可說是家無藏書,讀書的時間也很少,這是第一個不利的條件。后來,我成人以后,雖然能夠有機會讀一些書了,但卻又遇到了特殊年代,造成知識分子讀書的局限性很大,這是第二個不利的條件。第三個不利的條件,是我學習語言的能力不強。我除了中文、英文以外,還學過半年的德文,自修過俄文,但都不成器,所以,我讀書的語言也只有中文和英文。由于這幾種原因,可以說我讀書讀得不多,不是那種博覽群書的人,是讀書讀得很少的人。
有關我讀書的經歷和所讀過的書,我回憶起來大致分成這么幾個階段。我曾經讀過兩年小學,其余時間讀私塾,一直到二十二歲高中才畢業,我大約五歲開始和我的父親一起開始讀書,一直到我高中畢業,期間我讀過的書,我現在也記不太清,大致有《三字經》、《千家詩》和《唐詩三百首》,這都是和我的父親一起讀的。讀私塾的時候主要是讀《四書》、《左傳》、《古文觀止》、《昭明文選》、《東萊博議》,以及《西廂記》、《水滸傳》、《聊齋志異》、《紅樓夢》、《鏡花緣》、《孽海花》、《封神榜》、《官場現形記》、《儒林外史》等等。
劉道玉:緒貽先生,您讀的書很多,也很“超前”啊,像《西廂記》、《鏡花緣》等這樣的一些書,我到現在都沒有讀過,這些都為您成為學問大家奠定了基礎。
劉緒貽:那個時候,只都讀過這些書,練過“童子功”,笑。到了大學的時候,讀了《西洋文學史》、《西洋哲學史》、《英國文學史》、《堂·吉訶德》、《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我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時候,主要讀了這么幾本:一是《社會變遷》,這是跟著我當時很喜歡的一個老師一起讀的,這本書現在中國有翻譯本。還跟另外一位老師讀了《烏托邦和意識形態》。另外,當時在大學里還特別重視數學、高級代數和高級統計學等等。我在美國期間,在課外還自己讀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杜威的哲學,凡勃倫的《有閑階級》以及《文化人類學》。我對文化人類學特別感興趣,也很喜歡,所以自己讀了好幾本這方面的書籍。1947年回國以后,讀了一些新書,例如《毛澤東選集》、《鄧小平文選》,以及武漢大學校友李銳的幾本書,我都讀了,還有中山大學袁偉時等同志的文章……
王郢:您到現在堅持每天都讀書嗎?
劉緒貽:是的,反正我現在每天在家里也沒有別的事情,讀書和寫作成為了我生活的重要部分。我現在當然精力有限,難以堅持長時間和高強度的閱讀,每天讀書的時間可能也沒有八個鐘頭,但我仍然堅持每天讀書和寫作。在所讀的這些書中,我認為最受益的,是讀了以后能夠背下來的書,能背下來的最有用。中國古人說“開卷有益”,但我并不認為所有的書開卷了就都有益。有一些書我讀完了以后,就幾乎對我再沒有什么關系,例如《封神榜》這本書,雖然我當時讀的時候也覺得很好玩,但對我后來平生做人、為學卻沒有什么影響。有些書是白讀了,但有一些書對我的寫作技巧幫助很大,例如《聊齋志異》、《古文觀止》、《東萊博議》等這些書,就對我的寫作技巧很有幫助。其中,《古文觀止》這本書,它不僅提高了我的寫作水平,還對我人格的形成也很有幫助。《紅樓夢》這本書對我的婚姻戀愛觀也很有影響。
文學家陶淵明說他自己是“好讀書,不求甚解”。但我認為真正要做到讀書有益,最好的辦法還是要背誦。背誦這些讀過的書以后,在寫作的過程中就會自然的流露出來,當然也不是所有的書都要全部背下來,但是能夠背誦的書最好還是要背。
王郢:但現在的書又多又厚,如何能夠背下來呢?
劉緒貽:是呀,現在就很難了,有時候一本書都很難讀完。比如我的老師費孝通先生,說他一生讀書很少有從頭到尾都完整讀完的。以前我在讀私塾時,讀《論語》、《中庸》、《大學》、《孟子》這些書的時候,都要求要背誦,而且都背得滾瓜爛熟,甚至可以倒背。不過我想我讀書背得最熟的是《四書》,其次是《左傳》。《四書》的篇幅不算長,所以我通篇全部背誦下來。
劉道玉:關于背書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但是我認為死記硬背與增強科學的記憶力是不同的。人的記憶力是各種思維能力的組成之一,不可能有記憶遲鈍的天才科學家。我至今仍然保持著比較強的記憶力,這與我在年輕時注意加強記憶力鍛煉有關,這就猶如高爾基所說,記憶力就像肌肉一樣,越練越強。
王郢:對于年輕人,您是否有一些可以推薦值得一讀的書呢?
劉緒貽:我說到的那些書和文章,非常值得一讀。
劉道玉:緒貽先生,我向您請教一個問題。清朝有個文學家叫做張潮,他有一本書叫做《幽夢影》,書里面他寫到:“少年讀書如隙中窺月,中年讀書如庭中望月,老年讀書如臺上玩月。”這是不同年齡對讀書不同的心態和感覺,因為不同年齡對于讀書這件事情的感受是不同的。你現在有沒有“玩月”的感覺啊?
劉緒貽:是的,不同年齡讀書的感受的確是很有不同。因為你年紀很小的時候,由于閱歷有限,所以理解的能力也不是那么強,到了中年,你讀書的時候心境更開闊、視野也更開闊,老年更是如此。endprint
劉道玉:所謂的“玩月”,我的理解是一種欣賞的態度,從一些有價值的書中獲得樂趣。對于我們這些老人來說,基本上沒有了讀書的功利思想,因為文憑、學位、仕途和金錢對我們來說,都沒有任何的吸引力了。我還想提出另一個問題,當前我們的國人不讀書的現象比較嚴重,是世界平均讀書最少的國家之一。不讀書自然也不買書,也不藏書,這是否潛在著文化的危機?您對于這種狀況你有什么建議嗎?
劉緒貽:我當然是要勸人讀書啊。特別是對于到我這里來的那些年輕人,我更是要勸他們一定要多讀書,而且不僅是要多讀書,還要讀進步的書。對于那些課堂上授課的書,倒無需太重視,反而要特別重視社會上廣大群眾、喜歡讀書的人他們所在讀和喜歡讀的書。以前一些到我家來訪問的年輕學生,他們對于剛才我說的那些書甚至都不知道,也從沒有聽說過。他們的視野和思想都非常窄狹,所以好多問題難以做出判斷……
劉道玉:緒貽先生,你是跨世紀的老人,集德高、學高和壽高為一身,一百零一歲仍然堅持寫作,學富五車、學貫中西,是名副其實的學術大師,聽你的一席話我真是終身受益。我讀書和您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你是學社會科學的,我是學自然科學的,你列舉的那些書我基本都沒讀過。我自己讀書大體經歷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私塾教育的傳統文化啟蒙階段。我受了兩年的私塾教育,當然和劉先生您所讀的私塾不能相提并論。當時我在農村的私塾,讀得很淺,就是《百家姓》、《千字文》、《增廣賢文》,連唐詩都讀得不多,但李紳寫的《憫農》一首,是農家孩子必讀的詩句,全詩是:“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由于目睹農民的艱辛,我從小就養成了節約和愛惜糧食的習慣。
第二階段是正規的國民學校教育。離開私塾以后,我上了正規的小學,后來又連續的讀完了初中、高中和大學教育,基本上都是按照當時規定的教科書來讀書。在教科書以外,我基本上沒有讀過小說,我當時抱著這樣的思想:“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數、理、化以外的任何書都不讀,小說也不讀,以為學好數、理、化就真的走遍天下都不怕了,其實這是一個誤導,我就是受了這句話的誤導。在“文革”之前我連小說都沒讀過,我認為那是在浪費時間。當時的我就是讀數、理、化,化學系的課程選了以后我還選物理系的課程,武漢大學的課程讀完以后,我還選毗鄰的武漢水利水電學院的工程力學課。這是我讀書的第二個階段。
第三階段是根據工作需要閱讀教育學著作的階段。文化大革命之后,我被推到武漢大學校長的位置,根據工作的需要,我開始讀教育學的著作,這使我跳出了“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誤區。我讀了很多教育的書,例如柏拉圖的《理想國》、夸美紐斯的《大教學論》、盧梭的《愛彌兒》、紐曼的《理想大學》、杜威的《民主與學校教育》、福祿貝爾的《人的教育》等我都讀過。
劉緒貽:我問一句,蔡元培、梅貽琦的關于教育著作你讀過嗎?
劉道玉:我都讀過。蔡元培的四卷全集、陶行知的六卷全集,我都讀過,而且不止一次的反復閱讀。
第四階段是廣泛閱讀完善自己的階段。我從校長卸任以后,我讀書的境界又開闊了。
劉緒貽:境界提高了,視野開闊了。
劉道玉:是的。因為我沒有負擔了,校長也不做了,化學研究也不做了,讀書也就更開闊了。這個時候我讀的書,包括西方哲學,例如叔本華、康德、羅素、薩特等等人的,我都讀,還有諸如歷史、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等方面的書籍。這個時候讀書比較廣泛,這個階段讀書是為了完善自己,覺得自己以前讀書太少,是一種遺憾,為了要彌補過去的損失,要完善自己,要廣泛讀書。
關于讀書的方法,我們中國是一個書香之國,關于讀書的方法有很多很多,像諸葛亮的觀大略讀書方法,宋朝陳善的出入讀書方法,華羅庚的厚薄讀書方法等等。其中,華羅庚說讀書要從薄讀到厚,再從厚讀到薄,這就是厚積薄發的意思,對我啟發很大。我自己的讀書方法,就是“讀記法”,一邊讀書一邊記筆記。
劉緒貽:錢鐘書也是這樣。
劉道玉:我現在的讀書筆記有幾十本。我雖然已經中風十七年了,右手已經不能寫字,但我仍然堅持鍛煉用左手做筆記,一年至少要寫完兩本十六開的筆記本。筆記的內容,主要有三類:一是一些統計數字。數字雖然枯燥,但有時候數字卻是某些觀點最有力的證明論據。記下來以后,要用的時候就不用再去查找,信手拈來。比如說,中國現在科技期刊有五千多種,其中英文期刊只有二百三十九種,只占到總數的百分之五,但中國的期刊總量占世界期刊總量的百分之五十。可見我國英文期刊的缺乏。更為可惜的是,我們這么多期刊,在各學科中位于世界前三位的學術期刊,卻一本都沒有。二是記錄一些名言警句,例如十九世紀美國作家梭羅有一句名言:“說真話需要兩個人,一個人說,一個人聽。”我曾經就此寫過一篇文章,我說現在說真話難,聽真話更難。第三,記錄一些自己的讀書體會。讀完書以后有什么讀書體會,三言兩語的把它記下來,這是我一生讀書都堅持的方法。
現在我談談讀書的幾點感想:第一,我不太讀中國當代哲學家的書,但馮友蘭的中國哲學、朱光潛的美學等等我還是讀的,艾思奇的哲學書我也是在大學時做教科書就讀了,但現在那些所謂的哲學家的書我是不讀的。我跟青年人談話時,也勸他們不要讀中國當代哲學家的書,因為現在將哲學過于庸俗化了。哲學的真正意義在于追問事物的本源,人從何而來,世界從何而來,這才是真正意義的哲學。
第二點體會,我勸導青年要放棄“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觀點,這是不正確的,誤導了我,我希望現在的青年人不要再被誤導。而且我的體會是,真正要學好數、理、化,必須打好人文基礎,沒有人文基礎,是不可能學好數、理、化的。因為人文基礎給你提供了閱讀的能力、思考的能力、寫作的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沒有這些能力,怎么能學好數、理、化呢?我們化學系就有個教授動手能力很強,能夠解決很多技術實驗問題,但卻連論文都寫不好,一篇論文都沒有。他就是因為人文基礎太差,文字能力太差,寫不出文章來,講課的效果也很差,這就是片面強調數、理、化所帶來的副作用。所以,我要勸告當代的青年真正要學好數、理、化,必須打好人文基礎。人的才華是相通的,現在高考中的文、理分科是不可取的。至于少數具有文科特殊天賦的人才,是錄取時需要掌握的問題,但不能因為有個別的特別有天賦的人,就讓所有人都按照文、理分科來教學,這也是導致當代我國青年人文素質低下的原因之一。
剛才說到張潮的那句話,我覺得我也進入到臺上“玩月”的境界了。讀書的最初階段當然是為了應用,但最高的境界就是為了欣賞,欣賞知識的內核和美。
劉緒貽:我覺得現在青年人,在目前的教育體制下,所學的東西都是設計的課程和實用的知識,課本以外很少有時間或興趣涉獵,只為考試而讀書。這是最大的問題。現在的教育只培養“工具”,而不是啟發人如何追求真理,更談不上“百年樹人”。所以你看那些到我家里來的學生,我問他這些能夠啟發人思想、開闊人視野的書,他們都不知道。他們所讀的東西,多半都是課程內的東西,這真是太可怕了,所以資中筠說,中國的教育這樣繼續下去,人種都要退化。
劉道玉:我完全同意緒貽先生和資中筠先生的意見。我國當前不讀書的狀況確實是非常危險的,應該引起國家高層領導者們重視了。一個西方哲人說過一句很深刻的話:一個人的精神發育史,應該是一個人的閱讀史,而一個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全民族的閱讀水準。因此,我們國人應該清醒了,要銘記高爾基的名言:“熱愛書吧——這是知識的泉源!”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