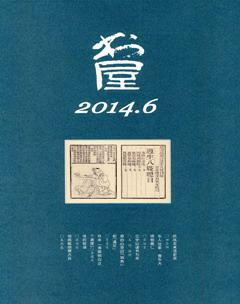蘇、黃和陶淵明
張宗子
一
東坡被貶嶺南,深愛陶淵明和柳宗元。東坡讀陶,蓋在自遣;讀柳,則有同病相憐之感。柳州作文,風(fēng)格勁峭,做詩則幽寒之外,復(fù)又哀婉。柳宗元和劉禹錫因參加二王變法而同遭放逐,處境相同,精神相契。東坡和陶不和柳,是因性情相差有遠(yuǎn)近。然而東坡之和陶,與陶詩面貌近似,氣質(zhì)有別,東坡豁達(dá),而淵明有怨憤;東坡隨和,淵明倔強(qiáng);陶詩率性而作,似淡而腴,東坡和詩則淡而略枯,蓋陶詩并非東坡的風(fēng)格,雖心儀而效仿,畢竟有隔膜。東坡的長處,實(shí)不在他稱道他人的恬淡,而在于胸襟寬廣,博學(xué)多識,有才氣,有想像,瀟灑空靈,又能十分深婉——這是真正的曠達(dá)。黃庭堅(jiān)最知東坡,亦知淵明,《書陶淵明詩后寄王吉老》云:“血?dú)夥絼倳r(shí),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綿歷世事,知決定無所用智,每觀此篇,如渴飲水,如欲寐得啜茗,如饑啖湯餅。今人亦有能同味者乎?但恐嚼不破耳。”嚼破,不靠天分,一小半靠性情,一大半靠經(jīng)歷。東坡一生若都是個(gè)晏殊或歐陽修,他未必就這么喜歡陶淵明,也未必會去和陶詩。黃庭堅(jiān)晚年經(jīng)歷和東坡近似,才有此語。他承認(rèn)年輕時(shí)讀不進(jìn)陶詩,乃是大實(shí)話。
黃庭堅(jiān)說:東坡在揚(yáng)州,《和飲酒詩》只是“如己所作”。至惠州,《和田園詩》“乃與淵明無異”。藝術(shù)乃至人生的某種境界,火候不足,苦求而不能達(dá);火候足了,不求自至。
黃庭堅(jiān)《跋子瞻和陶詩》:“子瞻謫嶺南時(shí),宰欲殺之。飽吃惠州飯,細(xì)和淵明詩。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風(fēng)味乃相似。”作于坡公仙逝之后,字字大白話,如信口而出,其中一往情深,可與杜甫懷李白諸詩相比,技巧精深,卻不見痕跡,故高不可攀。
風(fēng)味相似,是說品格之高相似,不是說詩風(fēng)相似,或性情完全相似。
二
東坡說陶詩“質(zhì)而實(shí)綺,癯而實(shí)腴”,八字定論,眾所周知。黃庭堅(jiān)也有幾處說陶詩的話,大意是,陶詩無雕琢之痕,似稚拙而極自然,而能有氣骨。阮籍的胸襟不如他,謝靈運(yùn)庾信工于錘煉,也不如他:“《飲酒》詩:‘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shí)?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dá)人解其會,逝將不復(fù)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淵明此詩,乃知阮嗣宗當(dāng)斂衽,何況鮑、謝諸子耶?詩中不見斧斤,而磊落清壯,惟陶能之。”“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于為詩也。至于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于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寧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為不智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所指,海印發(fā)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dāng)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謝康樂、庾蘭義之于詩,爐錘之功不遺力也。然陶彭澤之墻數(shù)仞,謝、庾未能窺其者,何哉?蓋二子有意于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耳。”
最后這一條,以有意和無意來區(qū)分三家的高下,只是一個(gè)說法。在意世人對自己作品的評價(jià),希望世人珍愛自己的作品,這是人之常情,誰都不能免,也無可厚非。陶淵明未必?zé)o意于俗人的贊毀,他說“輒題數(shù)句自娛”,是矜持的話。做詩固然是樂趣,偶得妙句,總不成一個(gè)人躲在書齋里,顛來倒去地吟哦,自己一個(gè)勁地叫好。陶淵明寫詩,也不是不贈人的。“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賈島肯定是太迫切了,但知音對于每個(gè)作者必不可少。在意他人的好惡,情理中事,只要不“在意”到趨時(shí)媚俗的地步就好。
陶詩與黃詩迥不相類,與蘇詩亦然,然東坡贊陶詩豐腴,山谷贊陶詩不見斧斤,是詩人之言,也是學(xué)者之言。詩人而兼學(xué)者不多,詩與學(xué)問都好的,更為少見。所以蘇、黃能深識淵明好處。識其好處,不一定非要追隨其風(fēng)格;即使追隨,不一定非求相似。風(fēng)格不同,不學(xué)風(fēng)格,學(xué)其精神。人吃雞肉,不變成雞,吃牛肉,不變成牛。俗人學(xué)習(xí),便只是規(guī)模其表,吃雞而自己變成雞,吃牛而自己變成牛。
老杜得益于庾信最多,韋、柳得益于大謝最多。山谷學(xué)杜,不滿蘭成,大概也是尊題之言吧。其實(shí)大謝和蘭成都自有佳處。
說陶詩難學(xué),引孔子“愚不可及”的話,再真切不過。
三
趙翼說:“香山詩恬淡閑適之趣,多得之于陶、韋。其《自吟拙什》云:‘時(shí)時(shí)自吟詠,吟罷有所思。蘇州及彭澤,與我不同時(shí)。此外復(fù)誰愛?唯有元微之。又《題潯陽樓》云:‘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又怪韋蘇州,詩情亦清閑。此可以觀其趣向所在也。晚年自適其適,但道其意所欲言,無一雕飾,實(shí)得力于二公耳。”白居易的情形,可以和蘇、黃二公參照。白詩得力于陶的地方,也是生活的態(tài)度,白居易的詩風(fēng)和陶詩,也是相差很遠(yuǎn)。
東坡極愛白居易,東坡之號便得名于白居易的詩,他和陶詩也是從白居易那里受到的啟發(fā)。白居易作有《效陶潛體詩十六首》。其中第三首如下:
朝飲一杯酒,冥心合元化。兀然無所思,日高尚閑臥。暮讀一卷書,會意如嘉話。欣然有所遇,夜深猶獨(dú)坐。又得琴上趣,安弦有余暇。復(fù)多詩中狂,下筆不能罷。唯茲三四事,持用度晝夜。所以陰雨中,經(jīng)旬不出舍。始悟獨(dú)住人,心安時(shí)亦過。
對比之下就能看出,東坡的和陶詩文字風(fēng)格上是更接近白居易的。
趙翼指出白詩恬淡的原因,在于白居易“出身貧寒,故易于知足”。他舉了一些例子:“少年時(shí)《西歸》一首云:‘馬瘦衣裳破,別家來二年。憶歸復(fù)愁歸,歸無一囊錢。《朱陳村》詩云:‘憶昨旅遊初,迨今十五春。孤舟三適楚,羸馬四經(jīng)秦。晝行有饑色,夜寢無安魂。可見其少時(shí)奔走衣食之苦矣。故自登科第,入仕途,所至安之,無不足之意。由京兆戶曹參軍丁母憂,退居渭上村云:‘新屋五六間,古槐八九樹。已若稍有寧宇。江州司馬雖以謫去,然《種櫻桃》詩云:‘上佐近來多五考,少應(yīng)四度見花開。忠州刺史雖遠(yuǎn)惡地,然《種桃杏》詩云:‘忠州且作三年計(jì),種杏栽桃擬待花。是所至即以為數(shù)年為期,未嘗求速化。自忠州歸朝,買宅于新昌里,雖湫隘,而有《小園》詩云:‘門閭堪作蓋,堂室可鋪筵。已覺自適。及刺杭州歸,有余貲,又買東都履道里楊憑宅,有林園池館之勝,遂有終焉之志。尋授蘇州刺史,一年即病免歸,授刑部侍郎,不久又病免歸,除河南尹,三年又病免歸,除同州刺史,亦稱病不拜,皆為此居也。直至加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致仕,始終不出洛陽一步。”結(jié)論是:“可見其茍合茍完,所志有限,實(shí)由于食貧居賤之有素;汔可小康,即處之泰然,不復(fù)求多也。”
但東坡和陶淵明的契合,還有另一層意思。這也是前人如朱熹等早已點(diǎn)出的,陶淵明其實(shí)是個(gè)大有雄心壯志的人,也是個(gè)性格剛強(qiáng)驕傲的人。朱熹說他“負(fù)氣”,這和魯迅稱慕的魏晉作家的“師心使氣”意思是一樣的。陶潛和阮籍師心使氣,只是風(fēng)格不同罷了。朱熹舉了陶詩詠荊軻的例子。更婉曲的例子還有。比如陶淵明在《五柳先生傳》里說自己“好讀書,不求甚解”。這“不求甚解”便是極自負(fù)的話,和老杜的“讀書難字過”不同。
東坡兩兄弟,弟弟蘇轍的性格更穩(wěn)重簡淡,東坡則有才子氣,精芒難掩。父親蘇洵早看出了這一點(diǎn),在《名二子說》里說:“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從性情上講,蘇轍更似白居易,詩風(fēng)也當(dāng)如此。但說到陶詩的豐腴和奇氣,那就相反,東坡比白居易和蘇轍更接近陶淵明。
四
《侯鯖錄》里提到東坡關(guān)于平淡的一段論述,有助于理解華麗和平淡的關(guān)系。東坡文字本是極華麗的,不過華麗得如朱熹所云“看不出”:
蘇二處見東坡先生與其書云:‘二郎侄,得書平安,并議論可喜,書字亦進(jìn),文字亦若無難處。有一事與汝說:凡文字,少小時(shí)須令氣象崢嶸,彩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shí)不是平淡,絢爛之極也。汝只見爺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學(xué)此樣,何不取舊日應(yīng)舉時(shí)文字看,高下抑揚(yáng),如龍蛇捉不住。當(dāng)且學(xué)此。只書字亦然。善思吾言。云云。此一帖乃斯文之秘,學(xué)者宜深味之。
今人動(dòng)輒說平淡,說自然,有幾個(gè)知道平淡自然是什么意思?空無一物的大白話就是平淡,不經(jīng)過腦子的話就是自然?華麗和平淡的關(guān)系,東坡此處說得何等透徹。沒經(jīng)過華麗,不懂得華麗是怎么一回事,有何資格說平淡?由華麗漸轉(zhuǎn)為平淡,平淡才如醇酒,經(jīng)得起回味。
歐陽修有兩句詞,王國維贊賞不已:“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fēng)容易別。”要害在“看盡”二字,看盡,你才容易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