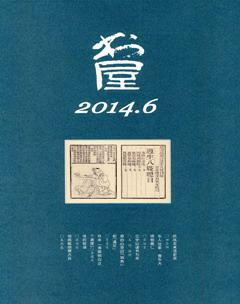抒情傳統:想像中國文學的一種方式
張春田
自從1971年旅美學人陳世驤在美國發表《論中國抒情傳統》,宣稱“中國文學傳統從整體而言就是一個抒情傳統”以后,“抒情傳統”論就日漸成為中國文學研究中一個頗具范式意義的論述架構,在港臺和海外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反響熱烈,相關的研究著作和論文蔚為大觀,簡直可以稱之為“一個現代學術思潮”。
近年來,一些學人嘗試重新反思和激活此一論述體系的生產性價值,以因應今日世界中文學意義及文學研究意義的危機化現象,于是“抒情傳統”論便在新的視野和問題意識之下,突破了原先主要限定于中國古典詩歌的范圍,與全球化時代人們普遍關心的人文議題形成廣泛的對話,同時煥發出嶄新的活力。比如,王德威教授把抒情傳統話題引入對于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化的討論之中,發掘在二十世紀這樣的“史詩”時代中,抒情如何成為革命和啟蒙之外另一種建構中國文化現代性的可能。從沈從文到胡蘭成,從江文也到臺靜農,王德威在《現代“抒情傳統”四論》中將一大批現代文人與學者納入了“抒情傳統”的最新譜系,著意于探討“抒情的現代性”。同樣把“抒情傳統”論作為現代中國一種積極的思想和學術資源的,還有陳國球教授。他與王德威教授合作編選了文選《抒情之現代性》(三聯書店即出),在學術史的意義上考鏡源流,對這一論述的來龍去脈和歷史語境作出了相當全面的梳理,為在廣義的抒情視野中勘探中國現代性重繪了一幅地圖。不僅如此,他更孜孜以求,尋繹“抒情傳統”論本身出現和發展的因由及軌跡,以更為后設的立場提出“為什么我們說(再進而為什么有人說)中國文學是一個抒情傳統”的問題。這就把知識生產背后的話語與權力、關懷與承擔等復雜因素都帶入到聚光燈下,讓我們看到“抒情傳統”論不只是一種關于文類特征的本體性討論,更是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變動和文化轉型的一種回應方式,是特定生存情境和心態的編碼化,是知識分子精神史的一部分。如此,我們方可理解他為何要把窮數年之力寫成的新著題名為《抒情中國論》(香港三聯書店,2013)。這是一本關于“抒情”但更是關于“中國”的厚重之作。
在《抒情中國論》中,陳國球不僅重譯了陳世驤最初以英文發表的關于中國抒情傳統的宣言文本,標明了以往通行譯本中的一些刪削與疏漏,對原文中的關鍵概念“lyricism”和“tradition”給予了比較清晰的界定,同時也勾連出文本出現的特定場合,以及所參考的相關學術資料,使得我們更好地理解到此文采用比較視野和化約式論述策略的因由。進而,在此著主體部分,著者從對多個學者著作的梳理中,呈現出現代中國抒情論述的一條具體脈絡。從周作人、聞一多、朱自清開啟先聲,到魯迅、朱光潛、沈從文各有醞釀發展,再到宗白華、方東美的精深表述,最后在陳世驤、高友工那里總其大成。著者對這一學術脈絡的討論,并不是單單截取若干詞句,而是知人論世,在學者個人的生活史、學術取向與時代風云的互動中,展現學者關于抒情傳統論述的各自風采。陳國球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洞見的看法。比如,他比較聞一多和朱自清對“詩言志”的闡釋,認為聞一多嘗試“把中國文學放在世界的地圖上”,要對中國文學的特點“作出‘起源論的解釋”,這是一種文學史的建構;而朱自清則從文學批評史的立場出發,“關心的是批評一項如何為具體語境和歷史脈絡所‘多重限定”。這一論斷非常透辟地論定了兩人之別。而陳又指出兩人之論有一個共同之處,即都承認抒情傳統的存在。這些是在以往的文學批評研究中是沒有被說清楚的。又比如,陳國球重訪魯迅和朱光潛關于陶淵明的爭論這一現代學術史上的公案,提出“魯、朱之辯也是情感如何安頓的問題”。如何抒情,在現代中國的“的確是一個嚴肅而又難以回避的問題”。陳國球引入沈從文關于新詩和短篇小說的相關意見,以沈從文的文學感應來反觀文學現代性中的困局。沈從文“將生命交付以文字‘抒情之大業”,他的“抽象的抒情”正是對如何安頓主體生命的回應。陳國球這樣的引述,無疑大大拓展了原先抒情傳統論述的范圍,揭示出抒情論述是如何凝定了文學和倫理相互結合的特定時刻。
這種穿透性的洞察,還體現在陳國球對一些學者屢用的概念的重新解讀上。比如,他指出宗白華的“意境”、方東美的“生命情調”等概念和語詞的使用,是有特定的心境與深遠的幽懷貫注其間的。看似“逃避”到純文學和藝術的世界中,其實在在充盈著感時憂國的情懷和文化自省的沖動。他特意引用了宗白華抗戰時期發表的《論〈世說新語〉和晉人之美》一文的“編后語”:“我們這時代是個什么時代?……我們設若要從中國過去一個同樣混亂、同樣黑暗的時代中,了解人們如何追求光明,追尋美,以救濟和建立他們的精神生活,化苦悶為創造,培養壯闊的精神人格,請讀完編者這篇小文。”陳國球以為,“從文學藝術看到追求光明、追尋美以對抗黑暗的精神力量”,是宗白華他們一輩人在戰亂時代的精神信仰,也是陳世驤在去國離鄉之后,選擇英譯陸機《文賦》時的感懷。“將當下的動蕩銜接傳統的連綿,應是抒情論述的主要貢獻”,陳國球如是說。在他看來,現代中國的抒情,不僅作為內在自我的形成和表述的方式而存在,更是一種生存情境的編碼化,一種道德倫理上的回應而存在。而討論抒情傳統,更是需要對此關鍵之處留心,并且承繼發揚。
在我看來,《抒情中國論》并不是一本關于文學史或者文學批評史的著作,而是一本深具理論抱負的著作,那就是在現代性和歷史性的視野中重新思考中國的抒情。這本書關于中國抒情理論的整理和追問,在很多層面,都與當代西方批評理論中的抒情論述,構成了潛在的對話關系。陳國球的著作告訴我們,在現代中國,抒情其實也應該被視為一種結構性、而非單純心理意義的因素。陳國球就像本雅明筆下那個“拾荒者”,在歷史的廢墟中努力將零散的碎片打撈出來,重建歷史沉默時的記憶。在這個意義上,這本書不僅探究了現代史上那些心系抒情的知識分子們的歷史哲學,也傳遞出著者在這個懸而未決的全球化時刻對抒情、對“文學的力量”所抱持的信念。或許正是這樣一種信念,才讓關于中國文學的想像和言說,變得如此重要,如此動人。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