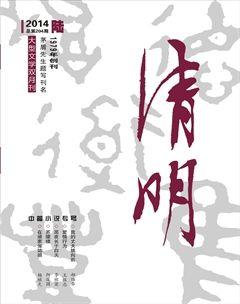黑夜長于白天
2014-07-09 20:08:04季棟梁
清明
2014年6期
季棟梁
1
老埂坪的三月,依然是多風的季節,刮起來就像個打著酒呼嚕的人在山野里撒野,攪得天昏地暗的。然而初八這天,天氣卻出奇的好。盡管被大紅綢子蒙著頭,但我仍能感到陽光有多明媚,大地有多清爽,鳥兒飛過,撒下嘹亮的啼唱,花兒綻放,散發出爽潤的香氣。馱著我的黑叫驢(公驢)也心情大好,不時地仰脖昂昂昂地叫著,聲傳四野。兩個吹手(嗩吶手)每人早晨吃了六碗臊子饸饹面,兩個油餅,喝了三缸子釅茶,肚胞肺潤,蓄足了底氣,直吹得熱火朝天。曲子就在枝枝杈杈的溝谷間亢奮地游走。《萬丈高樓平地起》《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輪流交替。其實他們會吹《打碗碗花》《鬧洞房》《大花轎》,可那年頭只能吹革命歌曲,那些都是四舊。我的嫁妝很壯觀,兩個畫著富貴牡丹的大紅箱子裝滿了成衣、布料、鞋襪,一口袋麥子,一口袋糜子,一麻包洋芋,一大壇腌豬肉,五只雞和一只羊。不要說這是災荒年過后青黃不接的春日,就是在富裕年景,這樣的嫁妝也是厚重與氣派的。但是,誰都看出這支五六十人浩浩蕩蕩的送親隊伍就像從戰場上潰敗下來的殘兵敗將,沒精打采,啞聲悄氣。是啊,我要嫁給一個傻子,誰愿意送這樣一門親呢。
但我沒有流淚,沒有嘆息,胸膛里只燃燒著熊熊仇恨。
這門親事是前天晌午我才知道的。早上,我和她去碾米。莊里的磨家家有,可碾子只有一臺,安在麥場看場的小院里。一口袋糜子碾成米,已是晌午,米和糠裝好后,她坐在碾臺上說坐坐吧,人老了骨就寒了,這日頭好的,能逼出骨里的陰寒。……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