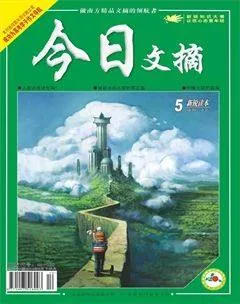中國鄉(xiāng)親要進城
宗和
城市的產(chǎn)生是人類社會的巨大進步。城市是文明的載體,它是行政、教化、非農(nóng)經(jīng)濟活動等的支點。歷史上,城市的演變伴隨著人口的遷徙。
根據(jù)歐美日韓的經(jīng)驗,城鎮(zhèn)化率超過50%后將會經(jīng)歷一段快速的城鎮(zhèn)化階段,即一個人口快速導入城市的階段。
中國的鄉(xiāng)親們,要進城。進城之后,整個社會將面臨哪些主要問題呢?
人口曾多次大規(guī)模遷徙
在20世紀初,世界上只有1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到了20世紀90年代,城市人口已經(jīng)達到42%,即全世界約21億人居住在城市里。有美國學者當時就對中國城鎮(zhèn)化過程中預計的進城農(nóng)民人數(shù)感嘆道,“這真是世間少有,也越顯得問題重大”。
目前,我國城鎮(zhèn)化率剛剛超過50%,如果按戶籍人口計算僅為35%左右,明顯低于發(fā)達國家近80%的水平,也低于許多同等發(fā)展階段國家的水平。差距也是潛力,在未來二三十年里,如果城鎮(zhèn)化率的提高保持在目前水平,每年將有1000多萬人口轉移到城市。
中國是世界城市發(fā)源地之一,古代中國城市與歐洲城市相比,不僅數(shù)量多,規(guī)模之大也是世界所罕見的。從漢代到清代,縣級以上的城市基本保持在1300個左右。《中國建筑史》列舉的世界古代十大城市中前7位的城市都是中國的都城。
中國古代的城市化水平也遠遠居于世界前列。南宋時期,南方的部分城市人口比重更高達20%左右。此后,中國的城市化水平逐漸下降,但直到近代才落后于世界。
180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僅3%,而中國在唐代時城市化水平即達10%。
然而,也不得不提到中國城市的發(fā)展是同社會的發(fā)展相一致的,每當社會繁榮、穩(wěn)定時,城市就獲得大的發(fā)展,而當社會發(fā)生動亂時,城市也遭到破壞。
幾乎每一個王朝的末期,城市都面臨毀滅性的災難,不少城市成為廢墟,生長線中斷,即使幸存的城市也是殘破不堪。因此,古代中國的城市雖然多次出現(xiàn)輝煌發(fā)展,但很難持久,大都隨王朝的興亡而興盛衰落。發(fā)展——衰落——破壞——恢復——發(fā)展——衰落——破壞,如此周而復始的循環(huán),成為古代中國城市發(fā)展的一個特點。
人口遷移往往伴隨著城市的發(fā)展。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出現(xiàn)了城市內的經(jīng)濟企業(yè),在1949~1957年間,城鎮(zhèn)人口以年均7%的速度增長。自1958年末起,城鎮(zhèn)人口的增長受到政府嚴格控制。改革開放之后,隨著南下打工大軍的出現(xiàn),中國人開始每年一度的大遷徙。
特色城鎮(zhèn)曾遍地開花
古代城市化過程中,因為自由地發(fā)展,孕育了各具特色的城鎮(zhèn),避免了千篇一律的怪相。
晚唐以來商業(yè)中心的興起至兩宋而大盛,更促成中國歷史上商業(yè)鎮(zhèn)的出現(xiàn)。這些縣以下的鎮(zhèn)級聚落的發(fā)展,主要依托于自身的經(jīng)濟功能而不是行政功能。
它們其中一些是唐末設置的軍事型鎮(zhèn)所,但大部分卻是不設城墻的。在交通交會處以手工業(yè)或貿(mào)易發(fā)展起來的小城市,當他們發(fā)展至一定規(guī)模時,政府賦予他們新的城市行政身份。
1080年時,在全國的1135個縣中,共有1810個此類鎮(zhèn)。不少鎮(zhèn)是在大型商貿(mào)城市周邊出現(xiàn)的,如在開封府便有31個鎮(zhèn),河南府有22個鎮(zhèn)。在鎮(zhèn)下,出現(xiàn)了更低層次的商業(yè)點——草市。它們?yōu)檗r(nóng)副產(chǎn)品提供了定期的交易場所,其中一些“草市”甚至升格為鎮(zhèn)。
宋代對外貿(mào)的鼓勵以及它的造船和航海的發(fā)達,使興旺的海港成為當時城鎮(zhèn)化的另一個動力,增加了另類城市。在北宋,這些城市便有六個。在南宋又添加了三個,即:鎮(zhèn)江、溫州和江陰。大部分海港城市位于南方,臨近出口產(chǎn)品的主要產(chǎn)地。在陸上的重要通道口,也出現(xiàn)重要的商貿(mào)城市,如天水等。
在北宋時期,人口過10萬的大城市超過40座。因此,兩宋城市規(guī)模已超越中世紀時期的歐洲,它擁有當時全世界最大的10座城市中超過一半的數(shù)量。
唐宋五代十國的紛亂所產(chǎn)生的統(tǒng)一的政權——宋,雖然在軍事上和領域上遠遜于漢唐兩代,然而卻自領風騷成為中國又一偉大時代。其背后三大原因之一是城市居民,即“坊廊戶”的出現(xiàn)。它所涉及的居民身份和房產(chǎn)稅,是城市和農(nóng)村分離與出現(xiàn)不同性質的開始。
兩宋的城市居民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從事工業(yè)制造、貿(mào)易、營商和演藝娛樂的自由,這些自由在城市內幾乎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但同時也導致城鄉(xiāng)之間的分別。
“十國”時代中國南方的區(qū)域間貿(mào)易已很蓬勃,至南宋更盛。當時出現(xiàn)了區(qū)域的經(jīng)濟分工,比如河北盛產(chǎn)銅和鐵,太湖地區(qū)產(chǎn)稻米,福建產(chǎn)茶和甘蔗,四川和浙江造紙、印刷和出版,湖北湖南和浙江產(chǎn)漆器,開封(汴京)和后來的浙江產(chǎn)瓷器等。當時的國內貿(mào)易以一般消費品為主,而外貿(mào)則集中在奢侈品如香料、珠寶、象牙、珊瑚、犀牛角、藥材沉香、絲、上等的茶和瓷器等。
守好天下糧倉
土地制度改革一直是牽涉到中國人吃飯問題的最核心部分,它經(jīng)常帶來社會深遠改變。
因為耕地的開拓、新技術的應用導致生產(chǎn)率的提高(特別是水稻)和經(jīng)濟作物的推廣,使土地市場形成,導致農(nóng)地的兼并和大莊園的出現(xiàn)。
宋代人口由初期(970年)的2100萬人增至1110年的8560萬人,但是農(nóng)業(yè)人口的比率卻在下降。在11世紀時的北宋,14%的人口擁有了全國77.5%的耕地面積。農(nóng)業(yè)具有高效率,不少農(nóng)民失去土地,被迫流入了工、商及服務性行業(yè),促進非農(nóng)經(jīng)濟和城市化的發(fā)展。
清后期代表了中國歷史發(fā)展的一個新分水嶺,卻曾面臨另外一種局面。傳統(tǒng)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已發(fā)展至超前飽和,出現(xiàn)了重大的不可持續(xù)危機。新儒學賴以支撐的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在清中葉已經(jīng)發(fā)展到盡頭。
沒有新的農(nóng)業(yè)技術,本身已很難支撐下去。道光中期,人口增長至4億,有1億人無地可耕,或者難以通過中國的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自給。由此導致的田地、米糧的自然漲價,使新儒學的“民為本”的統(tǒng)治目標難以落實,社會出現(xiàn)嚴重危機。
守好天下糧倉,確保糧食安全,再怎么強調都不過分。
201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發(fā)布2012年《城鄉(xiāng)一體化藍皮書》認為,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的快速推進導致土地要素流出糧食生產(chǎn)領域,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與糧食生產(chǎn)相互爭地的矛盾日漸突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國家糧食局科學研究院考察調研時指出,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是整個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的根本基礎和重要支撐。“守住管好‘天下糧倉,實質上就是要把好耕地紅線、打牢農(nóng)業(yè)基礎、確保糧食安全”。
然而,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中國人均耕地面積僅為1.38畝,約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耕地質量總體偏差,“三廢”污染等問題嚴重。李克強強調:“推進‘新四化必須要以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作為支撐。沒有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那我們的糧食產(chǎn)量就很難上去,質量更難提高。”
(馬達薦自《特別文摘》)
責編:易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