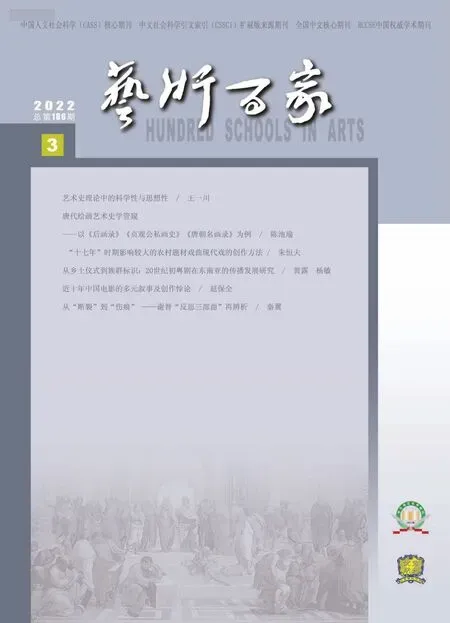宗炳、王微山水畫觀差異及對宋元山水畫的影響*
曹愛華
(南京信息工程大學傳媒與藝術學院,江蘇南京210044)
南朝的宗炳和王微各寫了一篇山水畫論,分別是《畫山水序》和《敘畫》。這兩篇文章為中國山水畫理論研究開了頭,直接引領中國山水畫的發展方向,吹響了山水畫獨立解放的第一聲號角。宗炳所著的《畫山水序》是古代第一篇專門談山水畫的理論文章,此文以”形神”問題為中心,論述了山水畫創作的實質以及山水畫所具有的價值,并對山水畫創作方法中的形體空間和透視等技術層面進行了探尋性論述。文中許多原創理論觀點如“以形媚道”、“寫山水之神”、“以形寫形,以色貌色”和“遠小近大”等等都是開歷史先河的,對后世繪畫尤其是宋初山水畫有著極大的影響;略遲于宗炳的《畫山水序》,王微寫了《敘畫》一文。《敘畫》的主旨是:繪畫不只是技藝,成當“與《易》象同體”。此外,文中對繪畫創作的本質與技巧,以及山水畫的欣賞等的論述有異于宗文。王微認為繪畫是“明神降之”,是創作主體的精神產物,所以山水畫“寫心”、“寫意”便是重中之重了。這些觀點成為以后百代繪畫的理論基礎。兩位山水畫理論的開山者,通過各自的探索豐富了山水畫理論的發展。
他們的理論是中國山水畫和山水畫論萌動的第一片嫩芽,為山水畫的開花散葉做了理論上的奠基。后世山水畫無論是宋畫還是元畫都有兩者影響的深深印記,但它對后世的影響卻各有偏重。《畫山水序》對于山水畫創作要求和方法顯然對宋代山水畫的影響巨大;而王微的審美觀點則幾乎為元代文人畫家所全盤接受。
宗炳的《畫山水序》認為“形神”問題是山水畫的核心問題,這是早期繪畫獨立發展首先要面對的問題。萌芽階段的山水畫亦然,宗炳認為山水畫創作遵循的最基本原則之一就是“以形寫形,以色貌色”。在宗炳看來,因為自然山水“質有而趣靈”,“山水以形媚道”。那么,在真山實水中游歷絕不是漫無目的地游蕩和簡單地欣賞,而是品味、探究圣人之道。然而,“老之將至。愧不能凝氣怡身,傷跕石門之流”,只能“畫像布色,構茲云嶺,于是乎“凡所游履,皆圖之于室”。臥游其中通過味山水圖像來體悟山水之中的圣人之道。顯然,其臥游的紙上山水是模擬自然界的真山實水,是真山水的替代。所以,其筆下的山水之于自然山水必然是“以形寫形,以色貌色”。此論樸素地反映了山水畫萌芽階段的對于表現自然客體真實性的本能要求,此時的山水畫實踐尚未能達到創作過程中主體情感投入的高度自覺。(盡管王微超前地提出了,但是實踐上只能留待后世的文人畫家來完成。)這完全是一種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其“以形寫形,以色貌色”重心完全落在自然美之上,這迥異于王微創作重心在“寫心”情感說的主張:“豈獨運諸指掌,亦以明神降之,此畫之情也。”
五代宋初的荊浩最先吸收消化了宗炳的“以形寫形,以色貌色”觀點,并結合實踐創作得出“度物象而取其真”,“遠則取其勢,近則取其質”的以形寫神觀點。而后,對于自然“圖真”式的客觀描寫被宋人直接繼承并完善,北宋著名的山水畫大家郭熙對于山水畫功能的要求近乎宗炳,其理論是在宗炳形神論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完善和發展的。郭熙有云:“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窮泉壑……此豈不快人意,實獲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貴夫畫山水之意也。”出發點都是對真山水畫的熱愛,都是由于客觀的原因而不能親近真山水而以山水畫來替代之。不過,宗炳是用山水畫代替真山水來“臥游”以明心見性,悟道修身;而以郭熙為代表的北宋山水畫家們則是以山水畫替代真山水來滿足朝廷官宦士大夫之流因困于朝堂,失于親近自然的心理補償。這必然對于山水畫有著肖似自然的要求,不然這山水畫何能“可行”、“可望”、“可游”、“可居”?
宗炳、荊浩、郭熙為代表的北宋山水畫創作追求體現了“無我之境”觀,李澤厚說,宋畫的“無我”不是說藝術家在山水畫的創作過程中沒有感情的傾注,只是在純客觀的描寫對象時其主觀情感含而不發,面對著真實的自然,“身即山川而取之”,“以形寫形,以色貌色”。北宋山水畫造景重理法、重質趣、重寫實的風格特點皆基于宗炳的“以形寫形,以色貌色。”而生發。
此外,宗炳對于山水創作上一些技法問題的論述也對宋畫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認為“豎畫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千里之迥”,“坐究四荒,不違天勵之叢,獨應無人之野,峰岫繞嶷,云林森渺。”期望咫尺之內描繪出千里之景,顯然是著意表現畫面最大限度的空間層次、結構和山水畫崇高氣勢。浩大的天地場景,真實而全面的境界,宗炳時代山水創作的技法發展程度還不足以嫻熟而充分地表現出來。盡管宗炳從理論上提出了表現山水形質和氣勢的手法,但要組織和構造這樣的山重水復、浩大的畫面,這樣的歷史使命只能由造型能力和組織能力均達到歷史新高度的北宋畫家來完成。郭熙《林泉高致》中雖然論說山水畫有“三遠”,但是北宋山水畫大多取“高遠”之勢,“豎畫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千里之迥”。山水圖式多為上留天、下留地全景式大山大水,畫面嚴謹,雄奇、險峻、壯美,氣勢磅礴,可謂“峰岫繞嶷,云林森渺”。從宗炳到關仝、荊浩、范寬、郭熙等為代表的宋代山水畫家追求全景構圖的現實主義創作觀念是一脈相承的。
王微是最先明確把繪畫提高到和圣人經典同體地步的理論家。其說“圖畫非止于藝”字面背后隱含著更為深邃的含義:既然“圖畫非止于藝,成當與易象同體”,那么創作這些繪畫的人呢?很顯然,絕不會是方伎、雜役、卜筮等社會地位較低的匠人,只會是王微他們這些學習圣人之道的文人士大夫之流。蘇軾作為北宋文人畫家的代言人對王微這種思想進行了拓展和深化,以中國文人特有的高傲提出了“士人畫”以區別院體和工匠畫:“士人畫和畫工畫不同,前者注重‘意氣’,后者只取皮毛。”這樣,基于文人畫家群體的立場、身份地位和知識涵養與后兩者的差異,引發了山水文人畫化一系列的審美準則和形式內容新標準的建立,文人畫從理論到實踐和工匠畫、院體畫拉開距離。這對元畫為代表的文人畫影響深遠而深刻,到了元代,文人畫徹底地和院體、工匠畫分道揚鑣。
王微在山水畫創作上最先提出以情入畫的觀點:山水畫“非以案城域,辨分州,標鎮阜,劃浸流”;“豈獨運諸指掌,亦以明神降之,此畫之情也”。在王微看來,山水畫是形而上的,是高尚的精神藝術思維,不是物質上的實用和科學上的準確。因此,應該將創作主體的情感傾注于其中,使人的精神熔鑄為山水畫的精神,天人合一。王微還從審美角度來深化論述其這一觀點,“本乎形者融靈,而動變者心也”,“望秋云,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這種想象的怡悅情性,往往和人的愿望、情感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突出強調了審美主體的想象、情感在審美感受中的能動作用。這和宗炳《畫山水序》所說“應目會心”,“應會感神,神超理得”有著極大的區別。宗炳認為山水畫是其領悟體驗圣人之道、佛家之理的媒介,所以畫家在創作時必然高度理性;王微則認為山水是畫家抒情寫思的載體,此說經劉勰生發為:“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直至元山水畫“畫不為人,自娛而已。”說白了,畫山水畫是文人自己怡情悅性。
王微認為山水畫創作應當“以判軀之狀,盡寸眸之明”,“擬太虛之體”,這和宗炳“坐究四荒,不違天勵之叢,獨應無人之野,峰岫繞嶷,云林森渺”的觀點恰恰相對立。王微認為人的眼睛欣賞景致的范圍有限,所以看到的景致往往是片面的,面對眼前片面的自然,不能“以形寫形,以色貌色”,更無需“不違天勵之叢,獨應無人之野,峰岫繞嶷,云林森渺。”創作者必須要超越于實景,以少少許勝多多許,以“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擬太虛之體”實即“寫心”論,從歷史上的美術文獻來看,最早接受“擬太虛之體”的是姚最,在此論之上姚最升華為“立萬象于胸懷”,進一步主張“寫心”。而后,張璪又發揮為“外事造化,中得心源”。到了元代,元文人畫家以畫寄情,借客觀自然抒發他們的主觀精神境界,抒寫“胸中逸氣”成為文人畫的主旨所在(誠如倪瓚所云“聊寫胸中逸氣爾”)。“寫心”論則是在宗炳“以形寫形,以色貌色”的自然主義基礎之上更進一層。此論遙遙地開啟著以元代為代表的“重寫心”、“有我之境”的山水畫風。
王微對筆墨也有超前的認識和闡述,其論“曲以為嵩高,趣以為方丈,以友之畫,齊乎太華。枉之點,表夫龍淮”。這里分明就是在談論山水畫形體的筆墨表現:論述吸收書法中不同的筆勢、點畫來表現不同地形地貌的山水之境,歸屬點是畫用筆。其目光有著驚人地前瞻性。數百年之后的趙子昂說畫家作畫應當掌握書法之“八法”:“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于八法通”,這顯然和王微思想是相通的,是王微書畫同源觀點的延續和升華。它追求的境界恰如李澤厚所說:“‘有我之境’重點不在客觀對象的忠實再現,而在精煉深永的筆墨意趣,畫面也就不必去追求自然景物的多樣(北宋)或精巧(南宋),而只在如何通過或借助某些自然景物、形象以筆墨趣味來傳達出藝術家主觀的心緒觀念就夠了。”這段話似乎是對宗炳和王微山水畫觀和追求的山水畫境的區別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