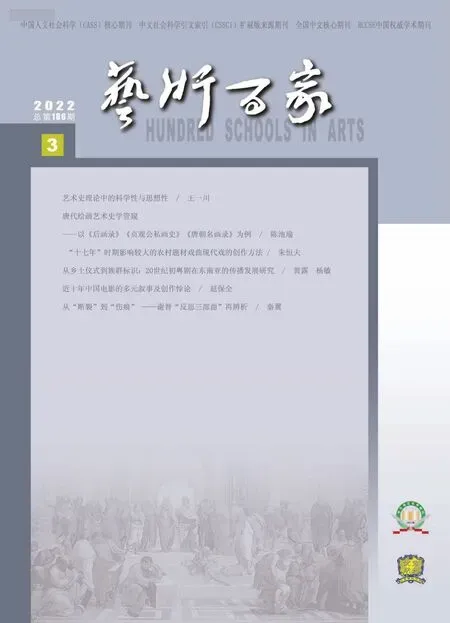禮制與多元審美文化角逐下的旗袍設計變遷*
張錦莉,孫曉勇
(1.中國海洋大學 藝術系,山東 青島266000;2.蘭州大學 藝術學院,甘肅 蘭州730000)
一、旗袍的文化背景
漢代劉熙《釋名·釋衣服》:“袍,苞也。苞,內衣也。”袍是繼深衣之后產生的又一種長衣,初見于戰國,普及于秦漢。自隋唐始為圓領,寬衫大袍、褒衣博帶是其特點。旗袍的誕生既與滿族的女性袍服有著重要的關系,又融合了漢、藏、蒙等其它民族的服飾之美,是服飾文化元素精粹的集合。
滿族由歷史上的女真族演化而來,在其跨越千年的歷史沿革中,與北方的蒙古族、鄂倫春族、達斡爾族、鄂溫克族、赫哲族等交往十分密切。他們都曾經是行圍打獵的游牧民族,有著類似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環境。這些類似的客觀條件使他們在著裝上也做出了一個共同的選擇——都以上下連體的一段式袍服作為自己的外服,選擇袍服是北方各民族御寒、騎獵的需要。滿族對袍服的改進起了重要作用,特別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民族后,“滿化”的旗袍開始了“漢化”的歷程。二百多年潛移默化的影響使旗袍在中華民族的生活中扎下根來,逐漸成為了“國服”。清初旗袍,其基本樣式為圓領(無領)、右衽、掩襟、扣袢,兩腋部位收縮,下擺寬大、兩面或者四面開衩,窄袖、袖端呈馬蹄狀;至清代中期,除了圓領之外,又有狹窄的立領,袍袖也較以前寬大,下擺垂直地面;晚清時期,旗袍衣身寬博,造型平直硬朗,衣長至腳踝,“元寶領”遮腮掩面。清代旗袍造型的直身式、外衣型,裝飾上的端莊、華麗、威嚴,以及高翹掩面的立領、封閉包裹的底襟,強烈地反映出封建社會的倫理道德規范和保守禁錮的審美傾向。
“旗袍”從興起時便寫下了多元文化與禮制的濃郁關系及歷史帷幕的拉開。清軍入關時,滿族服飾“上下同服”。皇太極當政時,為了建立一個統一、封建等級制王朝,決定實行服飾改革,規定皇帝穿龍袍,官員穿蟒袍;皇太子穿杏黃色,皇子穿金黃色;皇族宗室的長袍開四衩,端坐下來四下散開,袍身上小下大;宮廷服裝紋飾尤為講究,盤錦滿飾,大鑲大滾,百官中文官繪禽,武官畫獸,不同品第的官員補服繡不同的飛禽走獸圖案以“昭名分,辨等威”,以示威嚴;唐朝武則天當政就實施了這一規定,歷經明代,清滿人沿用下來。滿人為保持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民族習性,規定不改服飾,目的是為了消滅“強大”的漢民族意識,數千年強大的中原漢族的發展一朝被東北滿人代替,入主中原從此開始了清王朝,面對悠遠厚重的中原歷史他們無力湮滅,時刻防備漢人卷土重來;運用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馴化臣民的思想、意識,堅固清王朝的政權,付諸于服飾政策在開朝初期嚴令禁止穿漢服,面對數千年的文明,“君臣父子,尊卑有序,仁愛與和思想”,滿人亦折服了。如同“被俘的希臘反使蠻族的主人成為俘虜,她把藝術帶給粗野不文明的拉丁姆。”希臘尤為發達文明的思想、文化藝術融入到歐洲文明的起源中。無論是蘇麻拉姑參與了清朝早期的袍服改革,還是慈禧追求服飾美,末代清朝皇后婉容帶動了袍服的時尚,都影響著“旗袍”向著典雅、時尚、完善發展,禮制約束下的袍服在中原盛行了三百余年。
今天的旗袍依然在東方傳統文化沉淀的民族性與多元文化的融合中升華。自20世紀二三十年代,旗袍在漢族婦女中間也逐漸流行起來,經過演變和發展,并吸收了西方設計觀念,而形成了新式旗袍,拋棄了舊式旗袍寬大的袍身和繁復的式樣,以實用、簡練為宗旨,以凸現女性腰身曲線為設計特點,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如何在旗袍中根植民族傳統文化基因,貼近東方女性的顰笑婉約,彰顯女性的自信與典雅,凸現民族性符號的細節精致設計,是其躋身于世界流行多元時裝的根本。
二、禮制約束下旗袍的規格設計發展
“禮治”,統治者依照“禮”所確定的社會等級次序關系和名分規定來治理國家,從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從諸子百家學說中脫穎而出,儒教“禮論”:“異即使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行為規范,只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學禮制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的理論。儒家的禮也是一種法的形式,它是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如違反了“禮”的規范,就要受到刑的懲罰。李澤厚的《華夏美學》認為:禮既然是在行為活動中的一整套的秩序規范,也就存在儀容、動作、程式等感性形式方面。這方面與美有關,所謂“習禮”,其中就包括各種動作、行為、表情、言說、服飾、色彩等一系列感性秩序的建立、要求。滿清用“旗袍”來禮治天下,在服飾上確立了王權宗法等級倫理的綱常,受禮制左右,并附加滿人的民族傳統習俗的審美。
禮制制約著后宮服飾的等級規格和設計,嚴禁著裝方面的僭越行為。張愛玲《更衣記》說,“中國人不贊成太觸目的女人”,因為觸目代表著個性的張揚。而中國傳統的文化是貶抑個體的文化,是“中和”的文化。服飾文化也如此,在這種道德規范下的旗袍式樣只能是千篇一律,沒有任何的個性發揮。
在清代以前,由于人們長期接受的是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所以在著裝上一般表現為含蓄、端莊、嚴謹和大方。用寬松的袍服將人體包裹,崇尚人與衣的自然和諧之美,習慣于褒衣博帶,對于衣對人的適體與否不予關注,這對于審美根本無關緊要,重要的是服裝本身層面上的裝飾和美化。在歷朝歷代的服飾中,除盛唐之外均采用的是平直的線條和寬松的造型,胸、肩、腰及臀部都呈現平面化的狀態。而清代的旗袍就是這種思想觀念和制衣觀念的最好體現,它將東方女性的削肩、平胸、細腰、窄臀完全隱藏在寬大的袍身當中,反映了東方女性的含蓄、內斂和鋒芒不露,符合傳統的倫理道德和人們的審美意識。在這種造型的基礎上,又將各種繁雜的裝飾加諸袍身之上,加強了旗袍的華麗與繽紛,使清代旗袍形成了這種只重視細節刻畫而忽視整體塑造的特點。禮制之下的旗袍裝飾重點在于繡、滾、嵌、盤的堆砌 ,其精美絕倫的刺繡工藝和復雜的鑲滾技巧至今仍讓人嘆為觀止,也反映了當時絲織染繡技術的進步。清初旗袍衣身繡以各色花紋,袖端、衣襟、衣裾部位鑲滾各色緣飾,稱之“寬鑲密滾”,少則一、二道,多則達十八道,稱之“十八鑲”。旗袍寬松的造型覆蓋人體的曲線美,女性天然對美的希翼和追求只能用繡花、鑲邊等表綴性裝飾手段來代替和修飾人體美。這恰恰符合道家“天人合一”的思維模式,把自然社會、宇宙人生中的一切事物發生、變化都看做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諧平衡的有序運動,把實現“天人合一”當作整合天人關系的最高理想境界,追求人的身心自由。以道家的思想為指導,吸收百家之說,融會貫通而成《淮南子》書中提到:“氣為之充而身為之使”。中國審美文化中早有“美由氣生”之說,這種穿衣重在人氣之說,似乎也可以解釋為何滿清三百年中京派旗袍的具體形式無大的變化。面對滿人對社會權利的掌握,滿人的社會認同感,漢人也無奈地穿上同樣的“旗袍”,期望通過服飾上的模仿,迎合主流社會的生活方式,求得心理上獲得與其地位同等的優越慰藉。
禮制的“敦厚”使得千百年來女人“和”顏悅色。求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最大特點,《論語·庸也》:“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在這樣一種思維方式的約束下,使得國人的著裝特別講究和諧、適度。傳統旗袍的總特點是線條平穩、造型簡潔。但簡潔不意味著簡單,小小的旗袍卻包含著萬事萬物的宇宙法則。中國傳統審美心理要求客體“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也就是要求“和”,旗袍的敦厚、平穩也恰恰符合了中國人的審美習慣。傳統的旗袍一般都是比較寬松的款式,外表看起來沒有棱角,這樣較好地掩蓋內心的欲望,讓人僅從外表的裝飾看不出內心的變化,這同樣是追求“和”。幾千年來,中國傳統婦女一直恪守“三從四德”的教育,足不出戶,相夫教子。她們穿著心平氣和的旗袍,心平氣和地過著祥和、安穩的日子。
當以禮治為中心的王朝湮滅后,旗袍的變遷及盛行又以多元審美文化為基礎延續升化。
三、多元審美文化角逐影響下旗袍設計的變遷
多元審美文化角逐禮制撼動傳統的旗袍樣式。使旗袍在發展中由注重禮制的“形式美”到追求自然、簡約、時尚的“人性美”,在旗袍設計中融入傳統美學的意境美,以寫意、抽象設計消融傳統服飾設計的拘謹化與格式化,在濃濃民族風中把女性的曲線美、觸覺感官獨特的敏銳性盡情舒展,把中華傳統文化魅力寫進多元文化美學風范中,以傳統吉祥符號來承載并體現在精微細致盤扣等散點式的現代設計品格中。
旗袍圖案設計裝飾和細微精致小設計體現大文化,要挖掘民族傳統吉祥圖案,以現代設計整合民族風,滲透自然的清新質樸和文化博大精神,昭示傳統文化由“衣”至內的魅力文化沐浴,切實提高旗袍女性的文化氣質品味,張揚古老旗袍的美學與文化的凝聚力,以真正實現“衣”與人的相宜。
至此,高雅審美文化風格與質樸生活“俗”的結合使旗袍從一位貴族夫人到典雅麗質風情自信的普通女性,完成了其漫長歷史角色的轉變,歷經西學東漸、東西美學文化的不等量地吸引,至彰顯傳統文化魅力與絲路風采及華夏文明悠遠傳承的驕傲,轉化為最簡約、符號、時尚與傳統攜手的旗袍品牌設計。這一過程體現了透過服飾對歷經封建舊體制、舊思想殘害下女性地思想解放,是現代旗袍對女性肌體的一種溫和解放,沐浴六朝古國文化,張揚現代女性的自信,以微笑回歸自然,以“衣”尋求對人與自然的和諧生息。
總之,旗袍的演變體現了多元文化的融合,其發展體現了人與衣的自然、和諧、簡約美學設計,其傳承中烙上了民族性強悍的符號,并以傳統服飾美學文化魅力來征服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