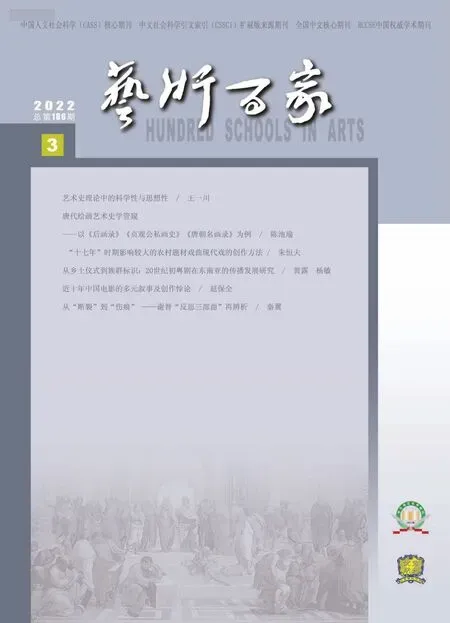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融合:巴托克《小宇宙》創(chuàng)作手法探析*
郭 超
(福建江夏學院人文學院,福建福州350108)
貝拉·巴托克出生于1881年,是匈牙利現(xiàn)代音樂領(lǐng)袖、民族主義作曲家及鋼琴演奏家。與同時代的作曲家不同,他極其重視民間音樂,在作品中融入大量的匈牙利民間音樂元素,因此創(chuàng)作風格既富有民族特色,又兼具現(xiàn)代氣息。此外,在創(chuàng)作上也融入20世紀現(xiàn)代音樂的作曲技法,例如打破了傳統(tǒng)大小調(diào)的束縛,大膽運用調(diào)式和音階,創(chuàng)造出多調(diào)性的風格等。創(chuàng)作于1926-1939年間的作品《小宇宙》就是巴托克眾多優(yōu)秀作品中的代表。
一、調(diào)式音階運用中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手法的融合
(一)八聲音階的運用
在現(xiàn)代音樂作品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許多作品在調(diào)式音階的運用上呈現(xiàn)出不拘一格的創(chuàng)作手法,《小宇宙》便是典型之一。其作品除了傳統(tǒng)的大小調(diào)式、中古調(diào)式音階之外,還出現(xiàn)了很多調(diào)式音階,比如:同主音大小調(diào)交替調(diào)式音階的運用;同中音調(diào)與平行調(diào)的混合交替調(diào)式音階;某些特殊旋律或和聲處理而形成的特殊音階,如在一個八度內(nèi),由半音與全音的反復連續(xù)做音階式級進而構(gòu)成的八聲音階等手法的運用,凸顯出巴托克作品中的現(xiàn)代因素。
八聲音階的基本形式有“半音—全音”的連續(xù)交替構(gòu)成和“全音—半音”的連續(xù)交替構(gòu)成。八聲音階的運用出現(xiàn)在巴托克作品《小宇宙》第99首作品中,這是其突破傳統(tǒng)轉(zhuǎn)向現(xiàn)代作曲的一次嘗試。
從音階層面分析,不難看出這首作品中融入現(xiàn)代手法的創(chuàng)作特征。首先,此作品采用隱藏調(diào)號的方式把上方和下方的音各安排在兩個不同的調(diào)性上面,調(diào)號相異,突破傳統(tǒng)記譜方式中上方聲部與下方聲部調(diào)號相同的原則,顯示典型的現(xiàn)代作品特征。其次,上方聲部的音列按照最后結(jié)束的主音依次排列出來為C、D、bE、F、B;下方聲部的音列按照最后結(jié)束的主音排列出來為C、#F、#G、A、B;然后把兩個音列綜合在一起排成 C、D、bE、F、#F、#G、A、B、C,是一個按照全音半音關(guān)系排列的八聲音階,在現(xiàn)代作曲中是常用的技法。再次,上方聲部與下方聲部所運用的調(diào)性也不同,在樂曲陳述過程中,上方音列較明顯強調(diào)了C音的主音地位,下方音列則圍繞著A音進行了一系列的級進運動,所以上方聲部與下方聲部是兩個主音與音階結(jié)構(gòu)都不相同的調(diào)式,呈現(xiàn)出雙調(diào)性的特征。
最值得關(guān)注的是巴托克在作品中雖然運用八聲音階的現(xiàn)代作曲技法,卻始終未能摒棄傳統(tǒng),把民族傳統(tǒng)的作曲技法也滲入其中。其一,雖然上方聲部與下方聲部合起來是一個八聲音階,但是單獨看二者所使用的具體音階,則都是傳統(tǒng)的自然調(diào)式音階,上方使用的是c和聲小調(diào)音階,下方使用的則是a旋律小調(diào)音階。其二,采用了平行調(diào)關(guān)系的雙調(diào)性,最后結(jié)束音歸并于主音。其三,上方聲部與下方聲部都采用了五音音列,具有濃郁的五聲音階音響效果。
八聲音階除了上述五音音列采用了復調(diào)化織體,在不同聲部的橫向運動中顯示出八聲音階的結(jié)合方法外,也可以通過非音階式的旋律運動結(jié)合在一起。如《小宇宙》中第109首《來自巴厘島》的例子。這種八聲音階的排列方式就是將八聲音階分為兩個四音音列,#G、A、B、C,和 D、bE、F、bG,通過分層對位,橫向以增四度、減五度、小二度的方式排列,表現(xiàn)出極強的現(xiàn)代風格。
(二)傳統(tǒng)中古調(diào)式音階的運用
在巴托克《小宇宙》作品中,除了運用到像上述20世紀音樂中出現(xiàn)的人工音階外,中古調(diào)式以及匈牙利民族調(diào)式也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作品中。中古調(diào)式除了我們較為熟悉的利底亞調(diào)式、弗里吉亞調(diào)式外,還有一個我們并不常用的洛克利亞調(diào)式。在強調(diào)調(diào)式化和聲的現(xiàn)代音樂創(chuàng)作方面,由于中古調(diào)式中的洛克利亞音階具有現(xiàn)代的功能特殊性,常常被作為一個富有特色的音階,被運用或經(jīng)過一些引申變化出現(xiàn)在一些作曲家的作品中,例如德彪西《夜曲》第一章《云》的主題等。同樣,在巴托克的作品《小宇宙》第25首的《模仿與轉(zhuǎn)位》中,經(jīng)過他的發(fā)展變化又引申出減五度小調(diào)的五聲音階。
在《小宇宙》第25首《模仿與轉(zhuǎn)位》中,巴托克從調(diào)號上省去了#F的記號,沒有將#F音升高,整個樂曲的特征音程即為減五度與小二度。減五度音在旋律中體現(xiàn)了暗淡的色彩效果,又由于小二度關(guān)系在和聲上也產(chǎn)生了暗淡色彩。這種在傳統(tǒng)中古調(diào)式基礎(chǔ)上引申出來的減五度音階結(jié)構(gòu)運用,具有和聲和旋律的雙重色彩,是在傳統(tǒng)基礎(chǔ)上發(fā)展運用的一種現(xiàn)代手法。
(三)調(diào)式中增音程的運用
《小宇宙》調(diào)式音階中除了出現(xiàn)減音程外,調(diào)式音階中的增音程也經(jīng)常被運用在巴托克的作品中。例如在東歐一些民間音樂里,運用比較多的就是包含有增二度以及增四度的音程。巴托克《小宇宙》中具有的民族風格調(diào)式,與傳統(tǒng)的中古調(diào)式是分不開的。
《小宇宙》中的第58首樂曲,名為《東方風格》,創(chuàng)作素材來自于巴托克1913年在北非所收集的阿拉伯音樂,旋律帶有明顯的阿拉伯風格。此曲為“g”小調(diào),結(jié)尾是半終止式的,旋律采用了五聲音階,這五個音分別是G、A、bB、#C、D,由此構(gòu)成了一個增二度(G—bB)和一個增四度(G—#C),體現(xiàn)了東方音樂的風格特征。
二、和弦運用中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手法的融合
(一)和弦類型的選擇與運用
近代和聲的和聲材料,其類型和數(shù)量之眾多,非傳統(tǒng)和聲體系所能比擬,從二度和音至三度疊置和弦,直至各種音程的疊置與各種可能的組合。在巴托克作品《小宇宙》中,也常采取一些變化處理的方式,比如運用了三度疊置的和弦,同時也運用了許多非三度疊置和弦,這使得整體的音響色彩有了傳統(tǒng)大小調(diào)體系以外的音響色彩。另外,以利底亞、弗里幾亞調(diào)式為基礎(chǔ)的五聲音階使巴托克的《小宇宙》充滿了民間音樂的風格。五聲音階在匈牙利民間音樂中經(jīng)常運用,旋律有時會出現(xiàn)四度的跳進,在《小宇宙》作品第107首《霧中的旋律》中,四度、五度和弦的運用尤為突出,而縱向運用的和弦全是二度、四度和五度疊置的,橫向的一些線條性旋律都是縱向的那些二度、四度和五度和弦的分解。
在低音聲部一開始的小節(jié)中,就出現(xiàn)了一個連續(xù)三小節(jié)都相同的和弦。G、A、C、D,可以有兩種理解的意思,第一種,可以看作是兩個二度音程,分別是G-A和C-D,按照四度關(guān)系疊置成一個根音與三音、五音、七音形成的二度、四度、五度和弦;第二種看法就是兩個四度音程G-C和A-D按照二度關(guān)系,疊置成一個二度、四度、五度和弦。具有五聲性風格的四、五度和弦形態(tài)構(gòu)成了低音聲部從頭至尾的音響,很有趣的一個現(xiàn)象就是高音聲部緊隨其后的構(gòu)成和弦為bA、bB、#C、bE,根據(jù)等音原則關(guān)系,這幾個音為#G、#A、#C、#D,從物理音響層面與低音聲部的音做比較,其實是把低音聲部的音做了高半音的移位,但是巴托克沒有把高音聲部的和弦寫成是高半音的形式。高音聲部bA、bB、#C、bE的這個和弦,在譜面上可以把這個和弦看作是三度疊置的一個和弦,排列出來為bA、#C、bE、七音省略、bB,它并不是一個常態(tài)的九和弦,而是一個對主和弦有一定分化作用,省略了七音的九和弦。
(二)和弦進行
作品《霧中的旋律》中還體現(xiàn)出和弦進行中民族性與現(xiàn)代手法的結(jié)合。不僅高音聲部的寫法使全曲從五聲風格中抽離出來有了現(xiàn)代化的風格特征外,在和弦的進行方面與音響層面上,現(xiàn)代化的音樂風格特征也是十分明顯。高音聲部和低音聲部依靠兩個和弦明顯分為兩個層次,并且兩個和弦是貫穿始終的。高音聲部的和弦從音響上來講是一個二度、四度、五度和弦,但是從寫法上來講它是一個不穩(wěn)定的和弦,有解決的傾向,高音、低音旋律對應(yīng)兩個層次的和弦自始至終的貫穿全曲,相互有音響上的聯(lián)系但都沒有解決。
三、調(diào)性的靈活運用
(一)對比性雙調(diào)疊置
“多調(diào)性”是現(xiàn)代音樂中一種新的調(diào)性處理方式,它的特點是在一首樂曲或一個段落的不同層次中,不同的調(diào)性同時做縱向的結(jié)合。巴托克是20世紀較早使用“多調(diào)性”的作曲家之一,而充滿民族特色的五聲調(diào)式以及中古調(diào)式則構(gòu)成了《小宇宙》的調(diào)式背景。在《小宇宙》第105首《游戲中》,運用了傳統(tǒng)的兩個不同主音的五聲調(diào)式,采取對位性雙調(diào)疊置的方式,把上下兩個聲部做了對比式的結(jié)合。
從調(diào)號上我們就可以清晰判斷出這首樂曲是兩個調(diào)式的并置組合。在織體上采用了復調(diào)式,上下兩個聲部先做平行進行,10小節(jié)后反向模近,27小節(jié)又做平行進行的處理。上方聲部采用以“a”為主音的五聲調(diào)式,下方聲部采用了以“#c”為主音的五聲調(diào)式,構(gòu)成了對比性雙調(diào)疊置(a和#c),打破了高低音兩個層次在同一時間內(nèi)由同一個調(diào)性控制的傳統(tǒng),最后終止在屬和弦上。
(二)同音列并置調(diào)式
上述的例子是在兩個音列上的兩個調(diào)式。在第30首《五度卡農(nóng)》中,兩聲部先后以相隔五度方式做模仿對位,最后落在不同的結(jié)束音,上方聲部采用了 C、D、E、F、G五音音列,下方聲部采用了G、A、B、C、D五音音列,最后落于“G”音,形成了兩個不同主音的五聲音階調(diào)式并置。把這兩個五音音列綜合起來,便可以看出是一個G密克索利底亞調(diào)式,是一個同音列的并置調(diào)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