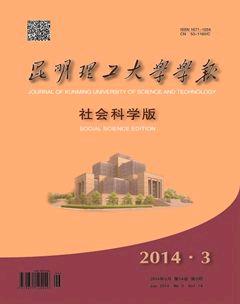逆防衛的許禁之爭及其適用條件分析
作者簡介:魏漢濤(1973-),男,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外國刑法、中國刑法研究。
摘要:
原不當侵害人對不當防衛能否進行逆防衛,理論上存在贊成與反對兩種觀點。當面臨生命或重大健康安全時人會本能地反擊,這是人性的表面,國外立法和我國正當防衛制度都沒有否定原不法侵害人的逆防衛權。著眼于加害與被害的關系,否定逆防衛人的逆防衛權有脫離現實之嫌。但逆防衛畢竟是一種特殊的防衛,如果按正當防衛的一般條件要求逆防衛人,不利于原防衛人權利的保護,因而還必須為其設置一些特殊的限制條件。從逆防衛的特殊性出發,除滿足正當防衛的一般條件外,逆防衛的成立還要滿足四個條件:一是不當防衛必須嚴重危及人身安全;二是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不當防衛非常緊迫;三是對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不允許進行逆防衛;四是逆防衛人必須履行躲避義務。
關鍵詞:逆防衛;許禁之爭;嚴重危及安全;緊迫性;躲避義務
中圖分類號:D91434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1-1254(2014)03-0032-07
On the Debate of Permitting or Banning Reverse Defense
and Its Applicable Conditions
WEI Hantao
(Law School,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Kunming 650500, Yunnan, China)
Abstract:There are two theoretically opposite views on whether the original infringer could conduct inverse defense against the defenders or no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verse defense has no legal basis. Focusing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victim and the infringer, we cannot deny inverse defense. However, inverse defense is, after all, a special kind of defense. If we inquire inverse defense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conditions of self-defense, it is not conducive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victims. Therefore, we must set more stringent applicable conditions for inverse defense. Except from meeting the general conditions of self-defense, inverse defense must meet three conditions as follows: first, the improper defense must seriously jeopardize personal safety; second, the serious threat to personal safety is very urgent; third, it is not allowed that the violent crimes seriously endanger the personal safety against the defense; fourth, the original infringer must fulfill the obligations of escaping.
Keywords:reverse defense; debate against permitting or banning; seriously jeopardizing safety; urgency; obligations of escaping
真理是有條件的,真理向前邁進一步就會變成謬誤。正當防衛作為一種法定的正當化事由,有其嚴格的適用條件。如果跨越了它的適用場域與條件,就會蛻變成為一種具有危害性的不法侵害行為。那么,對這種特殊的不法侵害行為能否進行再防衛呢?例如,對普通的小偷小摸行為,且行為人赤手空拳,如果防衛人用尖刀進行防衛;再如,對日常生活中的諸如拳打腳踢之類的輕微暴力侵害,被害人若用致命武器進行所謂的防衛,且直指不法侵害人的重大生命健康。對這種類型的不當防衛,如果不允許逆防衛人進行逆防衛,就很難避免遭受不必要的重大人身傷亡。由此可知,逆防衛人是否有逆防衛權,或者說逆防衛人能否進行逆防衛,將直接影響到逆防衛的性質。逆防衛涉及到逆防衛人的利益與原防衛人利益的平衡問題,處理不當可能會造成多方面的負面效果。在筆者看來,不僅要論證逆防衛的必要性問題,更要研究逆防衛的適用條件。然而,國內有關逆防衛適用條件的研究,大多套用正當防衛的一般條件,而對成立逆防衛應當滿足的特殊條件近乎無人研究。有鑒于此,本文嘗試對是否應授予逆防衛人逆防衛權,以及進行逆防衛應滿足的特殊條件略抒管見。
一、授予逆防衛權的必要性
逆防衛是指逆防衛人為了免受來自防衛人不適當的防衛,而針對防衛人實施的反向防衛行為。由于逆防衛人所面臨的不法侵害是自己招致的,對這種特殊的不法侵害逆防衛人是否可進行逆防衛,理論界存在分歧。
(一)逆防衛的許禁之爭
逆防衛人對自招的不法侵害能否進行逆防衛,有些學者持肯定的態度。例如,德國著名刑法學家李斯特也認為,可以針對過當反擊而轉變成不法攻擊進行防衛,即可以對防衛過當的行為實施正當防衛[1]。我國也有學者贊同逆防衛,主張“在不法侵害給逆防衛人的合法權益造成急迫傷害,尤其是生命、重大健康即將遭受不可彌補損失的場合下,應允許不法侵害人進行自衛”[2]。學界認可逆防衛的理由有兩點:第一,當防衛超過必要限度給侵害人的合法權利造成威脅時,正當的防衛行為就轉變成為不法侵害,法律不能期待逆防衛人任由對方侵犯自己而不采取任何防衛措施。我們知道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采取防衛是符合人道主義精神的,如果僅僅因為自己是原侵害人就剝奪了這種保護生命的權利,那么顯然是不符合法的宗旨的,也是不符合人的生物本能的。第二,如果不授予逆防衛人逆防衛權,就很難保證正當防衛的適用條件得到有效遵守,有可能造成不應有的損害。
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4卷
第3期魏漢濤:逆防衛的許禁之爭及其適用條件分析
與此相反,有學者對逆防衛持反對態度。例如,已故馬克昌教授曾經指出:“逆防衛人無權對防衛過當人進行所謂的‘正當防衛。”[3]對逆防衛人來說,防衛過當行為仍然是防衛行為,而且這是由于其自身的不法侵害所引起的,并且防衛過當與否在當時的具體情況下很難分清。如果允許逆防衛人對防衛過當的行為人實施正當防衛,無異于為其提供了一個繼續實施不法侵害行為或者實施新的不法侵害的理由。再如,黃明儒教授認為,正當防衛的前提條件是必須存在危害社會的不法侵害行為,“對下列幾種行為不能或者不宜進行正當防衛:(1)對正當防衛行為不能進行反防衛。(2)對法律所允許的緊急避險行為不能實行正當防衛。(3)對防衛過當、緊急避險過當不宜進行正當防衛。”[4]還有學者認為“在正當防衛中遭到反擊的不法侵害者,就不能借口保護自身權益而對正當防衛者再進行防衛”[5]。反對授予逆防衛人逆防衛權的理由有兩點:第一,如果授予逆防衛人逆防衛權,被害人同違法犯罪作斗爭的積極性就會受挫,不利于國家、集體、個人合法權益的保護;第二,當前中國的治安形勢較為嚴峻,如果授予逆防衛人有逆防衛權,不利于一般預防,不利于警戒潛在的犯罪人。如果不授予逆防衛權,則相當于告誡那些膽敢實施不法侵害的人,實施不法侵害不僅可能遭到更猛烈的反擊,而且還會受到法律制裁,從而達到鼓勵見義勇為、減少犯罪的效果。
在立法層面,是否承認逆防衛人的逆防衛權也存在分歧。意大利刑法典規定:“只要對權利的威脅是非法的,即使這種非法威脅是權利人自己引起的,均可對這種威脅進行合法防衛。”[6]很明顯,在意大利逆防衛是合法的。在美國,有些州的立法直接規定了逆防衛權。如有些州的刑法明確允許原侵害人在兩種情況下可以進行自衛:第一,如果行為人只是企圖激起非致命性爭斗,而對方卻使用致使性武力反抗,則行為人可以運用致命性武器進行防衛。例如,A輕微地敲打了B,但B將爭斗升級為致命性的,用刀威脅A。此時,A便可以運用致命性武力進行防衛。第二,侵犯者已經放棄了攻擊,并明確告知了被侵害者。如果此時被侵害者仍然使用暴力進行所謂的“自衛”,則原侵犯者就有權進行自衛[7]。但是,大多數國家的刑法沒有明確規定是否可以進行逆防衛,司法實踐中通常對逆防衛持否定態度。我國刑法也沒有明確逆防衛合法與否的問題。
(二)有限授予逆防衛的必要性
對現實的不法侵害有自衛權,這是一項自然法規則。當不法侵害人面臨現實的重大不法侵害時,這一規則同樣有效,只不過條件可能更為嚴格。
1盡管我國刑法沒有明確逆防衛權,但允許逆防衛是正當防衛制度的題中之意。眾所周知,法律為正當防衛設定了嚴格的適用條件。這表明立法者在設立正當防衛制度時并非片面地保護防衛一方的利益,而是同時要兼顧不法侵害一方的利益。既然法律沒有漠視原不法侵害一方面的利益,那么,原防衛人實施了不當防衛,嚴重威脅到了逆防衛人的重大身體健康甚至生命時,逆防衛人也應該有權尋求自力救濟。換言之,在防衛的場合,法律盡管否定原不法侵害人的不法侵害行為,但否定的僅僅是與其侵害行為相適用的相關權利,對其他權利仍予以肯定和保護,法律并沒有剝奪其保護自己合法權利的權利。因此,立法者在設立正當防衛制度時已為逆防衛留出了空間。立法者之所以要為逆防衛留出空間,是因為有限地允許逆防衛既有利于保護逆防衛人的合法權益,也有利于挽救原正當防衛人,避免其從正義走向不正義。正當防衛作為一項保護合法權利免受不當侵害的權利,原不法受害人可以享有,逆防衛人也可以享有。日本著名刑法學者大冢仁教授指出:基于過失的挑撥行為,其過失輕微時,以及預料到對方會實施輕微的反擊行為而進行了挑撥,對方卻實施了侵害異常重大法益的反擊行為時,對其尚有允許進行正當防衛的余地[8]。無可質疑,對無辜者的權利保護應優先于對不法侵害人的權利保護, 然而這種優先只能是有條件的優先,即可以為逆防衛人進行再防衛設定更嚴格的條件,但絕不能因為要優先保護無辜者的權利而徹底否定逆防衛人的防衛權。否定逆防衛人的逆防衛權,就意味著“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憲法規定在不法侵害人那里不適用。“既然公民有正當防衛權,犯罪人也是公民,他們也有正當防衛權”[9]。
2著眼于加害與被害的互動關系,否定逆防衛人的逆防衛權有脫離現實之嫌。在英美法系中,“不要責難被害人”是基石性的格言。可能因為如此,人們習慣于把罪犯看成是“壞人”對“好人”的傷害,犯罪人犯罪以假設受害人無辜為前提,如果犯罪人錯了,那么我們(包括被害人)者是對的。然而,現實生活并非如此,并非所有案件都是純粹的“加害-受害”的單向關系,不少案件中受害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德國犯罪學家漢斯·馮·亨蒂經過研究發現,“與犯罪人單獨的行為相比,許多刑事事件更多地表現出主體與客體的相互關系。……在長期的過程中逐漸導致了非法的結果,債權與債務之間的區別并非總是明確的。”[10]現代犯罪學研究表明,犯罪發生的過程更多地表現為“被害”與“加害”相互作用。由此可知,在現實生活中,加害人與受害人的身份或地位并非總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常常相互轉換,如受害人由于防衛不適時或防衛過當而由受害人轉變為加害人。現實生活中的不少案件是由于彼此的過錯、矛盾的積累最終爆發所致,在這種情況下, 簡單地將一方定為加害人,將另一方視為受害人是不適當的,很可能雙方都同時具有加害人與被害人的雙重身份,彼此在前后相繼的兩組互動關系中構成了加害與被害[2]。既然逆防衛人可能因防衛人之嚴重不當防衛而成為受害人,加害人與被害人的地位可能發生轉變,就沒有理由片面地否定逆防衛人的自衛權。
3否定逆防衛人的逆防衛權與人性相悖。法律不能強人所難,防衛是人的本能。在遠古時代,人們戰勝獵物以求得生存,面對來自動物的攻擊,人們本能地進行各種反抗。隨著生產的發展和分工的完善,人與人之間的矛盾逐漸凸顯,于是這種與生俱來的反抗不再是人和動物的較量,而是延續到了人與人之間。私有制的出現,國家的產生,那種“同態復仇”,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私力救濟權利統一由國家所支配。但國家畢竟不可能全天候地保護每一個人的權利不受侵犯,為了被侵害的權利能及時得到救助,國家對人本能的自衛權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確認,允許他們在迫不得已的緊急狀況下實施自救。貝卡里亞指出:“一切違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的命運,就同一座直接橫斷河流的堤壩一樣,或者被立即沖垮和淹沒,或者被自己造成的漩渦所侵蝕,并逐漸地潰滅。”[11]換言之,即便在國家法主導社會秩序的時代,法律沒有也不可否定人的自衛權,因為對外來的侵害進行反擊是人性的表現。無辜者對外來侵害的反抗是人性的表現,逆防衛人對原防衛人不當的防衛進行逆防衛也是人性的表現。當生命、重大健康面臨緊迫的不法侵害時,任何人都會做出本能反抗,我們不能否認他的這種“自救”。逆防衛人的這種自然權利并不因為其引起非法侵害而喪失,法律也不能期待逆防衛人不進行這種本能的反抗。
概言之,在防衛中,防衛人可能為了保護一個較小的法益而實施可能給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人身傷亡的防衛行為,也可能不法侵害根本不具備緊迫性而防衛人卻采取了不必要的防衛手段,還可能逆防衛人已經放棄了侵害或者喪失了繼續侵害的能力,不需要繼續進行所謂的防衛,防衛人卻采取了可能給侵害人造成重大損害的暴力行為。在這些情形中逆防衛人進行自衛,只要方式適當,程度無明顯偏極,我們就應承認他的逆防衛權。通過允許逆防衛,有兩個方面的效果:一是可以告誡公民,法律雖然允許以私力救濟的方式進行防衛,但這種防衛權是有條件的,否則就會從正當行為轉化為不當的侵害行為,從受害人轉化為侵害人,受到對方的反擊,進而促進正當防衛的適用條件得到遵守;二是可以有效地避免原防衛人借防衛之名行侵害之實,避免給社會造成不必要的損害。
二、逆防衛的適用條件之檢討
論證逆防衛的必要性可能并不困難,因難的是如何為逆防衛設定適用條件,因為逆防衛畢竟是一種特殊的防衛,不能簡單地套用正當防衛的適用條件。在中國期刊網全文數據庫中檢索不難發現,我國有關逆防衛適用條件的研究成果不多。現有研究中,有人提出,逆防衛只有滿足五個條件才能成立:必須存在不當的防衛;不當防衛正在進行;只能是逆防衛人對不當防衛人進行逆防衛;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能進行逆防衛;必須純粹以制止不當防衛的侵害為目的[12]。有人認為,逆防衛的成立要滿足以下五個條件:不當防衛實際存在;不當防衛正在進行;針對不當防衛人;具有防衛意識;必須迫不得已,且有嚴格的度的限制[13]。還有人主張,逆防衛需要具備以下五個要件:必須針對防衛人的不當侵害;必須針對正在進行的不當防衛;必須有防衛意圖;必須在必要限度以內實施;逆防衛不適用刑法第20條第3款有關特殊防衛的規定[14]。有人倡導,成立逆防衛要滿足七個要件:必須存在暴力性的不當防衛;暴力性的不當防衛正在進行;必須要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能實施逆防衛;逆防衛的主體不限于逆防衛人;只能針對不當防衛人進行逆防衛;必須有防衛意圖;不能超過必要的限度[15]。應該說,上述學者為逆防衛設定的條件都有一定的合理性,甚至有些學者考慮到了逆防衛的特殊性,為逆防衛設定了個別特殊條件。然而,這些觀點在以下兩個方面值得商榷:
(一)基本上沒有注意到逆防衛的特殊性
細心比對不難發現,上述四種觀點在形式上有所差異,或者說表述上有所差別,要么排列順序有所變化,要么增減了個別條件,但實質上沒有本質差異,基本上都是在正當防衛成立條件的基礎略加修改而成,是正當防衛的一般成立條件在逆防衛領域的具體化。不可否認,逆防衛也是一種防衛,當然要滿足正當防衛的一般條件,將正當防衛的一般成立條件在逆防衛中具體化是必要的。但僅僅如此是不夠的,因為逆防衛畢竟不同于一般防衛。既然逆防衛是一種特殊防衛,逆防衛的成立條件就要體現特殊性,否則就沒有必要將逆防衛的條件從正當防衛的成立條件中獨立出來。事實上,逆防衛者所面臨的不法侵害是由行為人自己招致的,如果單純用正當防衛的一般條件要求逆防衛人,明顯對原防衛人不公。而且,應根據逆防衛的特殊性,為其設定一些更嚴格的限制條件。
(二)不利于保護原防衛人的利益
面對復雜的社會現實、多元的利益訴求,法律不能單純滿足一方利益而忽視他方利益,也不能追求一種價值目標而漠視另一種價值目標,往往只能在多元利益與價值目標之間進行妥協與平衡。例如,刑法既要保障人權,又要維護社會秩序。如果一味地強調對社會秩序的維護,刑法就會變成洪水猛獸,德國納粹時代的災難很可能會再次重演;如果片面地突出人權保障,不僅訴訟效率低下,而且會使許多犯罪人逃脫法網,最終同樣可能會造成社會混亂。在被害人利益與加害人利益的矛盾沖突中,制度的設計應在兩者之間做出某種程度的妥協與平衡。但這種平衡不是均等的保護,而是有所偏向或優先。在正當防衛中,法律要優先保護被害人的利益。在逆防衛的場合,如果根據正當防衛的一般成立條件授予逆防衛人逆防衛權,即優先保護逆防衛者的權利,對原防衛人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正當防衛權的行使。因為不當的防衛行為是由逆防衛人所引起,對這種不法侵害逆防衛人有過錯。換言之,不當防衛人是第一受害者,逆防衛人是第二侵害者,在這種情況下,法律應優先保護第一受害者的利益。對自己招致的不法侵害,如果不法侵害不是特別嚴重,行為人就有忍受的義務。
三、逆防衛的特殊適用條件之我見
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原防衛行為是由逆防衛人的不當侵害行為引起的,且在緊急情況下防衛人很難把握防衛的限度。有鑒于此,為防止逆防衛人借逆防衛之名繼續實施侵害行為,必須嚴格限制其適用條件,壓縮逆防衛的空間。基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逆防衛除應具備正當防衛的一般條件之外,還要滿足以下幾個特殊條件:
(一)只有對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不當防衛才能進行逆防衛
如前所述,逆防衛人所面臨的不當防衛是自己招致的,逆防衛人對這種不當防衛有過錯。根據有過錯就應分擔責任的法理,像對自招的危險不能避險一樣,逆防衛人對一般的、非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不當防衛不能進行逆防衛。只有不當防衛可能危及重大人身安全時,法律才不能期待逆防衛人不進行逆防衛。法律不能強人所難,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有進行逆防衛的必要。基于這種理由,以財物為對象的不當防衛,以及輕微暴力的不當防衛,不能進行逆防衛,因為對這種自招的不當防衛,法律期待其忍受。只有非暴力性的不法侵害、一般輕微暴力侵害所招致的不當防衛嚴重危及到原不法侵害人的生命或重大健康時,原不法侵害人才可能進行逆防衛。
(二)對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不允許進行逆防衛
為了抑制嚴重的暴力犯罪的發生,我國1997年刑法確立了無限防衛權。《刑法》第20條第3款規定:“對正在進行行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于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根據這一規定,對這類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行為進行防衛,不存在防衛過當。因此,如果原不法侵害人對自己實施行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而招致的防衛,不存在逆防衛的空間。對這類不法侵害所招致的防衛行為不能進行逆防衛,在美國刑法中有明確的規定。美國有關致命性武力的運用規則中規定,對那些企圖造成他人死亡或者身體嚴重損傷而受到對方武力反抗的人,禁止使用“致命性武力”進行反擊。例如,A誘發一場爭斗的目的旨在造成死亡或嚴重身體損傷,則A不能以自衛危害B。除非A中途放棄、停止爭斗,一旦停止了爭斗,則其便恢復了防衛的特權[16]。
(三)只有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不當防衛非常緊迫時才能進行逆防衛
關于防衛過當的標準,理論上存在“必要說”“手段不當說”“相當說”等多種學說。根據我國刑法規定,只有“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才是防衛過當。結合我國無過當防衛之規定,防衛過當在我國應滿足兩個條件:一是防衛手段、方式與不法侵害明顯不相稱;二是造成重大損失。如果僅僅是手段不適當,但沒有造成重大損失;或者僅僅是造成了重大損失,但只要手段適當(如無過當防衛),都不是防衛過當。在防衛中,重大損害通常是重大人身傷亡。根據這一標準,只有造成重大人身傷亡,才可能是防衛過當。但如果要等到已經造成了重大損害才允許進行逆防衛,那么逆防衛權就形同虛設,因為造成重大損害后逆防衛人就不可能再進行有效的逆防衛。因此,只有在重大損害發生以前進行逆防衛,這種權利才有現實意義,才符合避免不法侵害發生這一防衛制度的初衷。由此可知,逆防衛的前提條件——不當防衛,不能以防衛過當為標準,即不能以造成重大人身傷亡為標準。但是,在重大損害發生前通常不易判斷防衛行為是否適當。如果不對不當防衛進行嚴格限制,很可能導致嚴重的負面效果。基于這種理由,只能從手段、方式上限制不當防衛的范圍。筆者認為,只有防衛行為與原不法侵害行為明顯不相稱,且這種不當的手段或方式可能造成重大人身傷亡的威脅已相當緊迫時,這種防衛行為才是不當的防衛,對這種不當防衛行為才能進行逆防衛。
需要說明的是,對質的不當防衛和量的不當防衛都可以進行逆防衛。在德國和日本,防衛過當分為質的過當與量的過當。質的過當是指超過必要性與相當性程度的情況,即以正當防衛狀況為前提,在防衛的強度中超過必要防衛程度的場合,如能用拳頭防衛卻用槍射殺的場合。量的過當是指最初作為正當防衛實施的結果,盡管對方停止了侵害,但繼續追擊的情況。例如,由于最初的反擊行為,不法侵害人已被制服或打倒,其侵害的態勢已經結束,但仍然進行所謂的防衛[17]。對量的過當,雖然有學者認為沒有正當防衛的余地,但因為對最初的正當防衛行為完全看作一系列的防衛行為是妥當的,所以應當認為作為全體看可能有防衛過當的適用[18]。換言之,可以對不當防衛的范圍做擴大解釋,除典型質的不當防衛外,防衛人在不法侵害的現實威脅不是十分明顯、緊迫的情況下,或者在法益不再處于緊迫、現實的侵害、威脅的情況下實施的防衛,也可以視為不當防衛,逆防衛人可以進行逆防衛。
(四)僅在逆防衛人無法躲避時才能進行逆防衛
在正當防衛的場合,如果被攻擊者能安全地躲避,從而避免攻擊時,是否還有必要進行防衛呢?傳統普通法規則要求,在使用致命性暴力進行防衛時,行為人必須履行躲避的義務,僅在退到絕路時才可以使用致命的暴力手段進行防衛[19]。現在這一規則已被不少國家或地區的法律所廢止,不再要求行為人在防衛時履行躲避的義務。理由是:第一,假如人們在面臨攻擊時必須逃跑,那么那些小流氓和好打架的人就會用它來驅趕和平的民眾,只要他們想在那里建立自己的統治。這將與法律要保護和平秩序的原則不相一致[20]441;第二,要求一個人像“懦夫一樣退縮”是錯誤的,至少是不現實的。對非法攻擊理直氣壯的反應是用暴力進行反擊,不用躲避,這是伸張正義的需要;第三,正確永遠不必為錯誤讓路,要求一個無辜的人躲避違反了這一原則;第四,呼吁人民躲避的規則可能最終使無辜者在沒有退路時也試圖尋找退路,因而增加無辜者死亡的風險[21]。既然如此,那么逆防衛者是否也不需要履行躲避義務呢?在筆者看來,答案是否定的。理由有兩點:其一,一般而言,由逆防衛人挑起的攻擊,逆防衛人有承擔容忍輕微損害的義務,不能進行防衛。如上所述,盡管當防衛人的不當防衛可能危及人的重大生命健康安全時,可以進行逆防衛,但這種防衛畢竟是一種特殊的防衛,對其應進行嚴格的限制,要求其履行躲避的義務就是重要的限制措施之一;其二,這樣要求是兼顧了生命健康價值的重要性。對危及重大健康、生命的不當防衛,逆防衛的后果通常是造成生命、重大健康的損害。如果在可以安全躲避的情況下要求逆防衛人躲避,既沒有增加逆防衛人的風險,又減少了不必要的死傷結果的發生,符合保護生命的原則,體現了法律的文明。事實上,只有在無法躲避的情況下,法律才不可能期待其不顧自己的生命任人宰割。“如果不可能進行躲避,那么就必須使挑釁者能夠進行緊急防衛,因為他不允許根據法律被放置在沒有出路的境地,從而要么必須毫無抵抗地把身體或者生命奉獻給攻擊者,要么必須自己承擔刑罰。”[20]446
普通防衛與逆防衛的重要區別是:普通防衛人所面臨的不法侵害完全應歸咎于他人,在法律上甚至在有道德上防衛人沒有可譴責性;逆防衛人所面臨的不法侵害是由逆防衛人的不當挑釁所引起的,他對這種不法侵害應承擔一定的責任。在普通正當防衛的場合,正義與邪惡界限分明,正義不必向邪惡屈服,所以法律并不要求防衛人履行躲避義務,甚至鼓勵防衛人與不法侵害者抗爭。在逆防衛的場合,黑白并非那么明顯,是逆防衛人的不當挑釁才激起了他人的過激反擊, 盡管逆防衛人后來轉化為新的受害人,但他原來的過錯并不能因此而一筆勾銷。如果原受害人的防衛輕微過當,不會危及生命或重大身體健康,法律可以要求逆防衛者(逆防衛人)忍受;如果顯著過當,危及生命或重大身體健康,法律可以要求他履行退避的義務,只有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才能進行逆防衛。事實上,之所以作這樣要求,是為了便于區分正當的逆防衛與防衛挑撥。防衛挑撥是指行為人出于侵害目的,以故意挑釁、引誘等方式促使對方進行不法侵害,而后借口防衛加害對方的行為。從形式上看,防衛挑撥與逆防衛極其相似。如果不要求逆防衛人履行躲避義務,就很難區分他先前不法侵害行為的真正意圖,有些不法犯罪分子就可借逆防衛之名行挑撥防衛之實。
參考文獻:
[1]費蘭茨·馮·李斯特. 德國刑法教科書[M]. 徐久生,譯.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221.
[2]章蓉,單家和. 特殊防衛權起因條件的反思——我國逆防衛制度構建的進路[J]. 西南政法大學學報, 2011(2):63-68.
[3]馬克昌. 犯罪通論[M]. 武漢: 武漢大學出版社, 2010:724.
[4]張世琦,牛麗. 433種犯罪——定罪量刑指南[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2.
[5]黃明儒. 刑法學[M]. 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142.
[6]意大利刑法典:引論[M].黃風,譯.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18.
[7]儲槐植. 美國刑法[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6:89.
[8]大冢仁. 刑法概說[M]. 馮軍,譯.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2:327.
[9]張遠煌, 徐彬, 論逆防衛[J]. 中國刑事法雜志, 2001(6):15-22.
[10]HANS VON HENTIG. The criminal and his Victim, Studies in the Sociobiology of crime[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84.
[11]貝卡里亞. 論犯罪與刑罰[M]. 黃風,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36.
[12]劉剛.論逆防衛的適用條件及其正確把握[J]. 廣西社會科學, 2004(12):102-106.
[13]祝凱,何劍. 反向防衛解析[J]. 河南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2005(12):26-28.
[14]王喆驊. 淺析反向防衛之構想[J]. 犯罪研究, 2004(2):64-66.
[15]徐文轉,張弋. 論逆防衛的正當化根據及構成要件[J]. 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3(4):127-132.
[16]約書亞·德雷斯勒. 美國刑法精解[M]. 王秀梅,等,譯.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231.
[17]張明楷. 外國刑法綱要[M].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168.
[18]馬克昌. 比較刑法原理:外國刑法學總論[M]. 武漢: 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366.
[19]魏漢濤. 刑法從寬事由共同本質的展開[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12:231.
[20]克勞斯·羅克辛. 德國刑法學總論:第一卷[M]. 王世洲,等,譯.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5.
[21]JOSHUA DRESSLER. Understanding Criminal Law[M]. Matthew Bender & company,1987:197.
收稿日期:2014-04-06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人大監督司法實施制度研究”(11CFX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