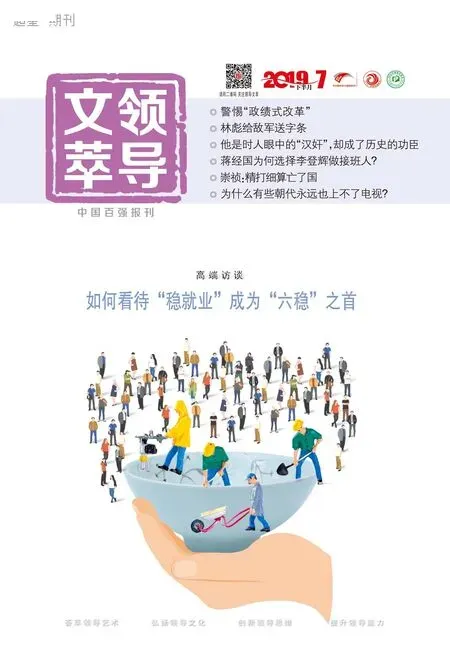美國對外用兵要過幾道坎?
對外宣戰與授權用兵
根據美國憲法,國會享有宣戰權。歷次美國對外正式宣戰的程序基本相同:總統首先向國會提交書面請求,或親自出席國會兩院聯席會議并提出請求;在宣戰請求中,總統會闡明其宣戰的迫切原因,這些原因包括對美國領土或其公民的武裝攻擊,以及對美國主權權益的侵犯或直接威脅。所有宣戰書都以法案或決議的形式,由國會兩院多數票通過,然后經總統簽署成為法律。
這些宣戰書大多采用相近的措辭:宣布美國與另外一個國家之間存在戰爭狀態;強調戰爭是另外一個國家強加給美國的;授權和指示總統使用美國的全部軍隊和政府資源對某國政府實施戰爭;為了成功地終止沖突,美國國會承諾提供國家的全部資源。
回顧美國對外用兵的歷史,不難發現一個現象,那就是,美國對外宣戰的次數出奇地少。據美國國會研究人員統計,建國之后的200多年間,美國大大小小的對外用兵有數百次,而對外宣戰僅有11次。這些宣戰分別發生在5場不同的戰爭中,分別是1812年的美英戰爭;1846年的美墨戰爭;1898年的美西戰爭;一戰期間,美國于1917年分別對德國和奧匈帝國兩國宣戰;二戰期間,美國于1941年分別對日本、德國和意大利三國宣戰,于1942年分別對保加利亞、匈牙利和羅馬尼亞三國宣戰。
還有一種情況,美國國會有時雖然授權總統對外用兵,但并未宣戰。其程序與宣戰類似:總統為了獲得授權而向國會提出對外用兵的具體請求,國會兩院以立法的形式通過授權,由總統簽署成為法律。這些法律通常授權總統對某個特定國家或一個特定地區內未指明的敵對國家動用武力。大多數情況下,總統會請求較為廣泛的權力,而國會有時會對總統請求的權力加以限制。
冷戰期間,美國國會正式授權的對外用兵有4次,主要是為了應對地區緊張局勢。1955年,國會授權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總統為了保護臺灣和澎湖列島免遭武裝攻擊,而以必要的方式使用美國的武裝部隊,隨后1955年2月,美軍在臺灣海峽集結了包括6艘航母在內的數百艘軍艦,但其時并未與中國發生沖突;1957年,國會授權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總統必要時使用武裝部隊協助中東國家,反對國際共產主義控制的國家“侵略”中東國家;1964年,國會授權林登·約翰遜總統使用武力保護東南亞條約組織(編注:旨在鎮壓東南亞地區民族解放運動的軍事政治集團。該組織根據1954年9月簽訂的《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而設立,1955年2月19日在泰國曼谷舉行的一次條約合作伙伴的會議中正式成立,1977年6月,該組織不復存在)的成員國,這就是著名的“東京灣決議”,允許總統對越南北部使用武力,為美國全面卷入越戰鋪平了道路;1983年,國會授權羅納德·里根總統在黎巴嫩部署海軍陸戰隊。
冷戰結束后,美國國會正式授權的對外用兵有3次,其中2次是為了對伊拉克動武,1次是為了報復“9·11”事件的謀劃者。1991年,國會授權喬治·布什總統對伊拉克動武,為美國發動海灣戰爭開了綠燈;“9·11”事件后,2001年,國會授權喬治·沃克·布什總統使用一切必要且合適的武力,打擊謀劃、批準、協助或參與了“9·11”恐怖襲擊的國家、組織或個人,為美國綿延10多年的反恐戰爭拉開了序幕;2002年,國會授權喬治·沃克·布什總統使用一切必要且合適的武力打擊伊拉克,為伊拉克戰爭開了綠燈。
二戰后為何“無戰可宣”
從上文的歷史回顧中,人們不難發現,盡管美國對外征戰綿延不絕,可是美國的所有宣戰行為都發生在冷戰之前,主要是一戰和二戰期間,與此相對,國會的對外用兵授權卻在各個歷史時期都有。宣戰與授權用兵有何區別?為何二戰之后美國“無戰可宣”?
二戰后,不僅美國不曾對外正式宣戰,世界各國都不曾這樣做。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當代國際法不再將戰爭視為解決國際爭端的合法手段。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浩劫后,人類充分意識到了戰爭的危害性,世界和平成為各國人民的共同愿望。1928年簽署的《非戰公約》規定,各國放棄以戰爭作為國家政策的手段,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或沖突。1945年簽署的《聯合國憲章》規定,在國際關系交往中,各會員國不得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只有聯合國安理會有權認定侵略行為,并決定是否對侵略國采取武力行為,戰爭只是自衛的手段。基于上述原因,二戰后,為了規避國際法,各國普遍不再使用“戰爭”的概念,轉而使用“武裝沖突”這一說法。美國也概莫能外。“戰爭”的概念基本不再使用了,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其實已經“無戰可宣”。
三權分立下的戰爭權之爭
或許美國不會再對外宣戰,但美國政治體制內部圍繞戰爭權的斗爭,卻似乎會一直繼續下去。在美國憲法確定的三權分立的體制下,國會享有宣戰權,以及建立軍隊、為軍隊撥款等權力,而總統是武裝部隊的總司令,有進行戰爭的權力。憲法之所以將宣戰權賦予國會,是因為作為民意代表機構的國會能夠體現人民的智慧和意見,對問題進行深思熟慮,作出謹慎的判斷。戰爭是國家大事,可能引起災難性后果,需要由國會對其必要性和適當性進行審議。憲法之所以將戰爭指揮權賦予總統,是因為作為國家元首的總統能團結民眾、迅速反應、果斷決策、主動作為,而戰爭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戰場形勢瞬息萬變,需要由總統集中調用國家資源和軍隊,實施靈活高效的指揮。
曠日持久的戰爭會不斷強化總統的權力,二戰后美國總統的權力達到了巔峰狀態,成為“帝王式總統”。冷戰期間,迫于巨大的戰略安全壓力,國會在對外用兵上一貫尊重總統的決策,往往淪為事后批準的“橡皮圖章”。例如朝鮮內戰爆發后,杜魯門總統就決定出兵朝鮮,但直至美軍部署到朝鮮兩天后,杜魯門才向國會通報出兵的決定,而國會對此沒有任何異議。
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美國深陷越戰泥潭。越戰,美軍最終鎩羽而歸,這促使國會反思自身在戰爭問題上一味追隨總統的做法,于是開始限制總統的戰爭權,減少戰爭決策的隨意性。1973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戰爭授權法》,強化了國會的戰爭權。該法規定,總統作為武裝部隊總司令,只有在3種情況下才能動用武力:(1)國會已經宣戰;(2)總統已經得到了專門的法律授權;(3)美國本土、領地或武裝部隊遭到進攻,并進入緊急狀態。該法還規定,如果總統未經國會宣戰或專門授權而采取了以下3種行為,須在48小時內報告國會:(1)總統使美國軍隊進入或者即將進入敵對狀態;(2)將準備戰斗狀態的美國軍隊部署至他國領土;(3)大幅增加已經位于他國的部隊的數量。國會將在60至90天內決定是否授權總統使用軍隊,如果國會拒絕授權,總統必須撤軍。 不過,對于《戰爭授權法》,歷屆美國總統并不買賬,稱這部法律違憲,侵犯了總統作為武裝部隊總司令的權力。從尼克松到奧巴馬,美國總統向來的態度是,歡迎國會以法律授權的方式支持總統海外用兵,但并不認為總統必須要獲得國會的授權。例如2011年美國對利比亞發動空襲時,奧巴馬并未尋求國會的事先授權,聲稱這是不必要的,因為有限的軍事行動并非“憲法所規定的‘戰爭”。
既然已有先例,因而對于敘利亞問題,奧巴馬政府其實大可不必尋求國會授權,完全可以擇機開展軍事行動。實際上,一旦動武時機成熟,內外條件具備,無論有無國會授權,奧巴馬都會毫不遲疑地發動戰爭。當然奧巴馬不會說“戰爭”這個詞,而會說“人道主義干涉”或“軍事行動”,或其他“新鮮”名詞。
(摘自《世界軍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