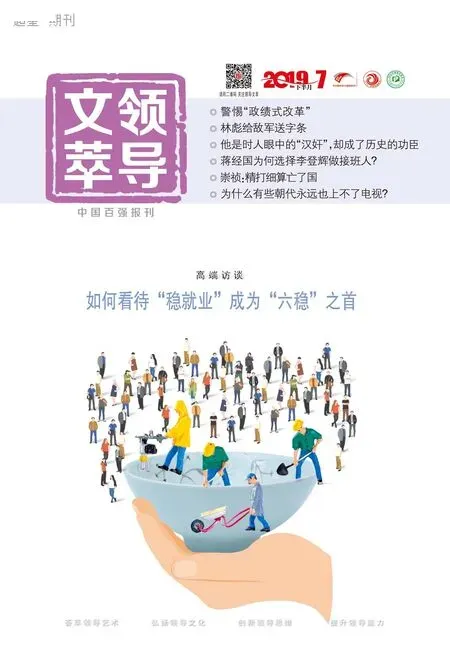人民和朝廷哪個是目的?
資中筠
培根說“歷史使人聰明”,其前提是寫真相的歷史,長期生活在歷史謊言宣教中的民眾只能日益愚昧。
官史,基本上是給皇帝看的
世界上歷史悠久的民族頗有幾個,好像沒有像我們那樣特別重視歷史文本,對史書賦予如此沉重的使命。最常見的說法是“以史為鑒,可知興替”。這里“替”是關鍵,為什么不是“興衰”?就是一個皇朝由盛而衰,最后被下一個朝代“替換”了,這才是最重要的。所謂一個朝代實際上是一個家族掌權,然后又被另一個家族奪走了,換了姓。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是為了本朝能千秋萬代永遠繼續,避免被別的朝代“替”掉。
誰最該吸取這個教訓?當然是皇帝和他的家族。他的謀士、帝師的職責就是教皇帝如何保住這個皇位,老百姓是無權參與,也無能為力,所以歷史首先是寫給皇帝看的。中國二十四史只有第一部《史記》例外,是異類。盡管司馬遷本人的職務是史官——太史公,但他著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不是為了皇朝的延續。他的心胸非常博大,包含整個他目光所及的世界,要找出規律,不是為了漢朝統治能夠永遠持續。所以他膽子很大,一直寫到當代。他是漢武帝時代的人,《武帝本紀》他也寫出來了,而且對武帝沒什么好話,并非歌功頌德。要是看《史記·孝武本紀》,對漢武帝得不出很好的印象。而且《史記》還有點像布羅代爾所提倡的寫生活史,給各類人都寫列傳,包括《游俠列傳》、《刺客列傳》、《貨殖列傳》等。中國人歷來是輕商的,但司馬遷給商人也列傳。還有酷吏、循吏,都分別列傳,按照他自己的評判標準。
所以司馬遷的《史記》,是中國歷史書里的一個異類。是為記錄史實,也是寄托他自己的情懷,不是給皇帝看的。但從此以后,包括《漢書》,歷代所謂“正史”,也是官史,基本上是給皇帝看的。
《資治通鑒》的最后附有一封給皇帝的信
沒有列入二十四史,卻最權威、最重要的一部編年通史干脆就叫《資治通鑒》,顧名思義,目的鮮明,是幫助統治者如何鞏固統治權的。《資治通鑒》的最后附有一封給皇帝的信,大意說我所有的精力都已經放到這里邊了,此書是在宋英宗時奉命編寫的,完成時已經是宋神宗當政了。他請當朝皇帝好好讀一讀這部書,并明確提出,每一個朝代的興衰有什么樣的規律,宋朝應如何吸取經驗教訓,才能持續興旺下去。
說穿了,歷史著作的最高目標就是如何使皇朝能夠千秋萬代永存下去。為達鞏固統治的目的,其中有一條就是得民心。所以得民心是手段,不是目的。就是說民眾的需求和他們的福祉,是必須要顧及的,任何一個統治者都不能不顧及,但這是手段,目標是為了維持王朝。就像唐太宗那句膾炙人口的話:水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民是水,舟是皇權。
當然也可以說這是一種以民為本的思想,因為水還是最基礎的。但歸根結底,水的功用是什么呢?是為了承載上面的皇權寶座。能夠明白這一點,重視民眾這個基礎,就算明君了。但后來因為在皇宮里待久了,皇二代、皇三代以后,連這樣的道理都不明白了,習慣于掌握生殺予奪之權,以為自己可以呼風喚雨,為所欲為,一意孤行,結果起了風浪,把船給掀翻了。
不論如何,歷史著作的最終著眼點是鞏固一家皇權的統治。
從這一功能派生出來,史書還有一個功能是對當朝統治者起一定的監督和約束作用,這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中國古代史書有一以貫之的價值觀,這是從孔子著《春秋》時定下來的。遣詞造句都代表著褒貶,叫做“春秋筆法”,所以有“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之說。是“流芳百世,還是遺臭萬年”,一般草民不在乎,中國士大夫卻很在乎,當國者更在乎,他們特別在乎自己死后的歷史地位,史書上是把他當成明君還是昏君。
要想歷史把他寫得好,就要做得好。做不好,在歷史上就會是昏君,亡國之君。所以對于皇帝或統治者來說,史書起到一定的監督作用,使他們還有所敬畏。所以顧準說中國的文化是“史官文化”。這個傳統在皇權專制時期能保持近千年,很不簡單。到唐太宗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怕史官記下來,堅持要看自己的“起居注”,褚遂良等人頂不住,就破了這個規矩。后來隱惡揚善、歌功頌德就逐漸多了起來。不過總的來說,史官還是有一定的獨立性,心目中有一個榜樣,治史者對后世有一份責任心,對真相心存敬畏,不敢胡編亂造。
不能以皇朝的興衰為主線
自19世紀中葉,中國人開始放眼看世界以來,再講歷史,就不限于中國,而是世界各國的歷史了。“以史為鑒”也包括以他國的興衰為鑒。中國人研究外國歷史,最開頭的著眼點是:為什么他們能打敗我們?這也就是中國學生回答美國教授為什么學歷史的問題——是為了救國。不管學中國史還是學外國史都是為了救國,這是當時知識精英的共同情結。
但是“他們”為什么強大,就不能以皇朝的興衰為主線了。因為歐洲從中世紀以后的發展途徑,就不是一國一家的王朝興衰。歷史發展是以生產力、思想的進步和制度的改變為主線。因此,我們在學歐洲的歷史時,總是要學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宗教革命、科技革命、工業革命,什么時候有了蒸汽機之類。既跨越王朝,也跨越國界。
幾年以前,中央電視臺的紀錄片《大國崛起》曾引起熱議。一般觀眾自然而然會想到“中國崛起”,思考從其他國家的興衰中看出什么規律。比如紀錄片中提到荷蘭這個蕞爾小國,卻曾經一度因其最自由、最開放、最有創新而領先歐洲,稱霸一時;比如德國作為歐洲的后來者,特別重視教育,19世紀德國的教育在歐美國家處于領先地位,德國也以此興國。
這實際上是從人類文明發展的角度看歷史,脫離了帝王家譜的體系,顛覆了為皇朝服務的歷史觀。從這個意義上講,《大國崛起》這部紀錄片無形中起了一些突破性的作用。
培根說“歷史使人聰明”,其前提是寫真相的歷史,長期生活在歷史謊言宣教中的民眾只能日益愚昧。多一些人,早一點清醒地對待歷史,明確人民與朝廷哪個是目的,哪個是手段,最終要“保”的是誰,這是百姓禍福、民族興衰的關鍵。
(摘自《國家人文歷史》)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