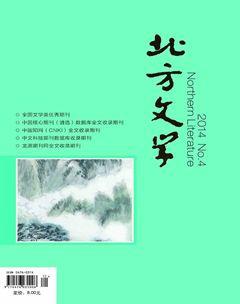《傻瓜吉姆佩爾》的象征意義
摘 要:短篇小說《傻瓜吉姆佩爾》是美國猶太作家艾?巴?辛格的成名之作,通過描述善良的吉姆佩爾備受屈辱和欺騙的一生以及他對天堂美好生活的期待,辛格表達了他對受苦受難的猶太民族的美好明天的向往,堅信和平的人道主義終有一天會到來。在這篇短篇小說名篇中, 辛格運用了豐富的象征手法來深化這一主題。
關鍵詞:《傻瓜吉姆佩爾》;艾?巴?辛格;象征手法
一
一九七八年,瑞典科學院授予辛格諾貝爾文學獎,表彰他在文學上的成就。諾貝爾獎委員會在頒給辛格的獎金證書中特別指出,辛格獲獎是因為“他的洋溢著激情的敘事藝術,不僅是從波蘭猶太人的文化傳統中汲取了滋養,而且還將人類的普遍處境逼真地反映出來。”[1]美國著名文學評論家、紐約大學文學教授歐文﹒哈沃也認為:辛格作為一個意第緒語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不僅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絕后的。由此可見辛格的作品受歡迎和受推崇的程度。
辛格的小說中,以短篇居多,其中最廣為人知的一篇就是《傻瓜吉姆佩爾》,它是辛格的成名之作。通過描述善良的吉姆佩爾備受屈辱和欺騙的一生以及他對天堂美好生活的期待,辛格表達了他對受苦受難的猶太民族的美好明天的向往,堅信和平的人道主義終有一天會到來。在這篇短篇小說中, 辛格運用了豐富的象征手法來深化這一主題。
象征手法在文學作品中的運用非常普遍,早在文學形成的早期就已經被廣泛使用。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英雄史詩《貝奧武甫》中就有象征主義手法的運用。《農夫皮爾斯》一詩中,威廉?朗格蘭就把象征手法運用得恰到好處。約翰?班揚的《天路歷程》中象征手法的使用更是到了顛峰。但什么是象征? 文學上的象征手法,是指在特定情景下,用某種具體的事物暗示出另外的在某些方面與之有某種程度相近或相似的思想或事物。也就是說,作品中雖然只出現一種具體的事物,但同時卻包含兩種意義:一種明意,即作品中直接出現的具體事物;另一種暗意,即由具體事物所暗示出來的意義。正由于暗示,我們常發現,象征的結果,明意(即意義的表現)也許是單一的,但暗意〔即意義)則往往是復雜的。由明到暗,由單一到復雜,這中間的距離,是通過暗示這座橋梁架通的。所以大凡使用象征手法的文學作品都比較含蓄,有時也隱晦。
普列漢諾夫指出:“藝術既表現人們的感情,也表現人們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現,而是用生動的形象來表現。藝術的最主要特點就在此。”[2]車爾尼雪夫斯基也明確說:“‘美是在個別的、活生生的事物,而不在抽象的思想。”[3]象征手法的特點,與他們所論述的這條美學規律是相符合的,它能用具休個別的事物,給人以直接的形象觀照,消除藝術中那些抽象的東西,給予人們以美感享受,并引起感情上的共鳴。也許正是這個原因,才使象征手法在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風格的作家作品中存在。象征手法運用不但使抽象的概念具體化、形象化,使復雜深刻的事理淺顯化,而且,使文學創作由外部世界轉向了更加隱秘內在的精神世界,擴大了寫作的題材范圍,改變了人們表現世界的方式。由于象征手法的運用,作者可以避開原先有所顧忌的事物或事理,采用曲折隱諱的表現方法,大膽放手進行敘述或描寫,因而也就可以更深刻的揭示被象征物即本體的本質。同時象征手法所創造的特有藝術意境,增強作品的表現力和藝術效果,它所引起的更廣泛的聯想,延伸了文章的內蘊,使文章具有了永恒的藝術魅力。
二
吉姆佩爾是個誠實勤勞的孤兒,卻一輩子被人欺侮。從小吉姆佩爾就被大伙兒送到面包房去當學徒,每個人都來捉弄他;當他準備要離開弗拉姆波爾到別的鎮上去的時候,鎮上的人們合伙欺騙他娶了尖酸刻薄不守婦道的艾爾卡并讓他當上了六個私生子的父親;雖然艾爾卡一次又一次給他戴上綠帽子,他還是對她很著迷,并且非常疼愛艾爾卡生下的孩子。盡管吉姆佩爾全心全意在付出,他卻從來沒有得到過任何的回報:艾爾卡不但從來不讓他享受作為丈夫的權利,還總是對他惡言相向并不斷地背叛他;她的那個小弟弟(私生子)不但不感激他的養育之恩,反而常常打得他青一塊紫一塊;他對鎮上人們的善良和輕信得到的不是同情,而是變本加厲的嘲笑和捉弄。當他去拉比那里求救時,拉比告訴他說“書上寫著:當一輩子傻瓜也比做一小時惡人強。你不是傻瓜。他們才是傻瓜哩。凡是令其鄰人感到羞恥的人,自己就會失去天堂。”[4] 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拉比的女兒在吉姆佩爾準備離開的時候也捉弄了他。
從表面看來,辛格似乎講述的是一個傻瓜悲慘的一生。然而從深層次來看,吉姆佩爾實際上是一種象征。他的孤兒身份代表著整個以“邊緣人”身份存在的猶太民族;他身上所反映出來的精神折射出猶太民族的傳統文化心理;他對另一個“真實的,沒有紛擾,沒有嘲笑,沒有欺詐”的世界的憧憬,表達出了猶太民族對全世界人民和平友愛相處的期待,體現了作者和平的人道主義的理想。那么辛格筆下的吉姆佩爾是如何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來詮釋這一切的呢?
首先,吉姆佩爾是個孤兒,無依無靠,任人欺侮,任人捉弄。他其實并不傻,因為他心里知道人們編來騙他的那些話根本就不是真的,但是,他卻不能不裝出相信人們說的話,因為如果他表現出不相信的樣子,就會引起眾怒,大家就都會拿他當靶子。他的孤兒身份正是整個猶太民族現在所處的境況的反映,而他備受欺侮的一生就是猶太民族幾千年的流散與苦難歷史。公元135年,猶太人被逐出耶路撒冷以至整個巴勒斯坦,流落到世界各地,成了沒有國家、分散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孤兒”。由于多種原因,歷史上歐洲對猶太人屠殺習慣成自然,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殘酷程度令人發指。“集體屠殺所留下的痛苦回憶,將在幾代猶太人的歷史和思想意識中起決定性的作用。沒有哪一個民族經歷過如此殘暴的行徑,沒有哪一個民族有過這樣的遭遇。”[5]
其次,現實生活中的吉姆佩爾,被世人欺騙,受妻子虐待,遭學徒羞辱,甚至連學校的教書先生都幫他妻子的不忠行為說話,糊弄他。但是吉姆佩爾并沒有怨天尤人,因為“肩膀是上帝給的,負擔也是上帝安排的。”[4]作為一個虔誠的猶太教徒,他堅信一個人“一輩子不吃點苦頭,那是不可能的,也不應抱這樣的期望。”[4]吉姆佩爾堪稱是以德報怨的典范,他從來不會因為別人欺騙他就侮辱和報復別人。當他不斷受到周圍人群的捉弄時,他總是告訴自己:算了吧,“至少我希望這樣做對他們也有點好處。”[4]正因為如此,人們才總是可以隨心所欲地捉弄他。當他偶然發現妻子艾爾卡背著他與別人有私情時,他最終還是原諒了她,還“決心始終要相信人家對我說的話。不相信有什么好處呢?今天你不相信自己的妻子,明天你就連上帝都不相信了。”[4]艾爾卡臨終前向他懺悔:六個孩子沒有一個是他的。他經過痛苦的思考,仍然決定不報復任何人,并且把自己所有的積蓄拿出來分給這些孩子們。當世人欺騙他、魔鬼誘惑他時,他也擋住了誘惑,不欺騙世人。在吉姆佩爾身上體現著猶太人民的苦難意識和深厚的猶太教博愛、寬容的精神。他身上所反映出來的精神折射出猶太民族的傳統文化心理:有十個煩惱比僅有一個煩惱要好得多,只有一個煩惱時,痛苦一定是深刻的,而有了十個,就不一樣了。沒有一個自殺者是因為有了十個煩惱,全是為一個煩惱而死的。所以猶太人雖然苦難多多,但他們并不懼怕,而是以極大的勇氣正視一切的苦難與不幸。
最后,吉姆佩爾憑著自己超然的忍耐力獲得了上帝的認同,他滿懷期望,盼著自己到達那個“真實的,沒有紛擾,沒有嘲笑,沒有欺詐”的地方,“在那里,即使是吉姆佩爾,也不會受騙。”[4]古老的猶太民族終日流離失所,經受著苦難與毀滅,富于歷史感的猶太人民,承受了太多的苦難,背負著太多的責任,但善良的猶太人民一直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忍耐著、承受著,內心里呼喚著、尋找著、期待著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友愛、團結、互敬,并且在默默地為之受難、漂泊、流浪和犧牲。猶太人相信,只要他們遵守摩西十誡,只要他們信仰上帝,與人為善,終有一天他們會得到上帝的救贖,去到他們的應許之地。
三
這所有的一切概括起來,實際上就是一位真誠的人道主義作家對一種和平的人道主義的渴求。辛格從小受到嚴格的猶太傳統教育,他不但熟悉猶太教的一切宗教儀式及猶太法典,而且熟悉猶太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各種風俗習慣和傳統,更使他對猶太人的苦難和不幸有著深深的感觸。辛格自己極其廣泛的生活閱歷,尤其是對猶太民族苦難歷史和現狀深刻的切身體驗,引發了作者對自己民族歷史和民族未來出路的思考。正如他自己曾經說過的:“我的民族承受過人世間瘋狂到無以復加的沉重打擊。作為這個民族的兒子,我對即將到來的危險豈可掉以輕心。無奈多次的努力始終找不到真正的出路……”[1]這句話道出了辛格作為一個具有強烈民族責任感的作家,在其寫作過程中對本民族命運和未來的深切關懷和焦慮的心情。他的各種題材和主題的小說,無不承載著他強烈的民族意識,無不承載著他在各種“出路”之間的試探、挫折和失敗后的憂傷。正是苦難的歷史和流浪生活促使辛格將整個猶太民族的生存寫照全部凝聚在吉姆佩爾的身上,把猶太民族在夾縫中求生存的處境真實地反映在吉姆佩爾以“愚人”身份生存在弗拉姆波爾小鎮中。吉姆佩爾是辛格借以抒發情感的象征。實際上,吉姆佩爾就是辛格,代表了辛格等猶太人的共同愿望:和平的人道主義終有一天會到來。到那時候,吉姆佩爾在上帝面前會享受平等的待遇,猶太民族就會不再受歧視、迫害和欺辱,猶太人民也有自己的家園,不再漂泊流浪了。這就是辛格的信念,這就是他對于人類深思的結論。
參考文獻:
[1] 《諾貝爾文學獎頒獎演說集》[M],毛信德,蔣躍,韋勝杭譯,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
[2] 普列漢諾夫,《論藝術》[M],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1973.
[3] 車爾尼雪夫斯基,《藝術與現實的審美關系》[M],周揚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4] 艾薩克﹒B﹒辛格,《傻瓜吉姆佩爾》[M],劉興安 張鏡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1.
[5] 阿巴﹒埃班,《猶太史》[M],閻瑞松譯,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作者簡介:黃芳(1981-), 女,湖南新田人, 湘南學院外國語學院教師,碩士,研究方向為英美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