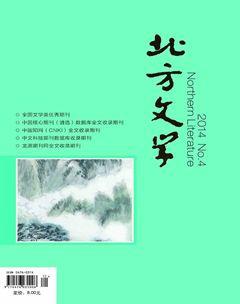未生怨故事的結構性初探
摘 要:列維-斯特勞斯用結構理論的方式處理俄狄浦斯王故事,開創了結構主義重構神話的方式。而在佛教的故事題材中,未生怨王故事與俄狄浦斯王故事有一定的相似性,擬借助結構主義理論將故事肢解為十一個相互獨立又具有聯系的片段,直尋彼此之間及子結構與整體之間的關系。
關鍵詞:未生怨王;結構性;整體
阿阇世王是佛教故事題材中一位頗具張力的人物,諸多經典中都有記載,尤其以《觀無量壽經》和《阿阇世王經》中最為突出。即使在佛滅后,為佛教的第一次經典結集有著不可磨滅的功勛,但也無以開釋其早先對佛陀的構害,由是一生與佛結緣。經典以文字為載體傳承,在接受群體上勢必受到一定限制,迫使其指向精英群體和案頭文學而放棄一般受眾,顯然不利教義宣傳、推廣和普及。漸而派生出新的藝術形式,即經變畫。阿阇世王題材在此類樣式中的比例可見一斑。特別是在盛唐時期,形成了以《觀無量壽經》居中為主體,“未生怨”(即阿阇世王故事)和“十六觀”為兩翼各居兩側的固定模式。敦煌石窟的第148窟、172窟是此類模式的典范代表。
現將未生怨故事從經變畫中抽繹而出,則構成一個單向的、線性的故事結構:
(一)頻婆娑羅(古印度摩揭陀國國王)老來無子,請相師占卜;
(二)相師陳說山中有道人,死后會投胎為王子;
(三)頻婆娑羅派人殺死道人;
(四)道人轉世成兔子,又被追殺釘死;
(五)韋提希夫人(王后)懷孕;
(六)占師預言此子長大后弒父;
(七)太子出生不久,就被國王和王后從樓上拋下;
(八)太子幸存,但折斷手指(故而又稱“未生怨王”、“折指”);
(九)阿阇世(太子)長大,篡奪王位,幽禁父親;
(十)韋提希探望,并將食物涂在身上為國王充饑;
(十一)阿阇世囚禁母親,殺死父親。
當然其后還有韋提希夫人向佛禱告、阿阇世王周身惡瘡、母子皈依、問佛涅槃悶絕蘇醒等故事情節,考慮到以“未生怨”身份和名稱由來,以及人物的張力則不作贅述。在這個無可逆轉的敘事格局里,似乎每一個事件都會成為后一相繼事件的引子,后來的事件又在不斷地回應著初始事件,表達完整、結構緊湊。再將這十一個故事片段依照一定規律分列,則可得出表1:
注意到,Ⅰ列(即(一)、(三)事件)、Ⅱ列(即(二)、(四)、(六)事件)、Ⅲ列(即(五)、(十)事件)、Ⅳ列(即(七)、(八)、(九)、(十一)事件)的動作主體分別為頻婆娑羅、通靈異者(包括道人和占師)、韋提希、阿阇世。一列之內,情節的推動者固定唯一,并成為故事構成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也為整個故事蓄勢,且具有內在的一致性。“與形式主義相反,結構不在意不愿使具體事物與抽象事物對立,也不承認后者的特殊價值……它(指結構)本身就是內容,可以理解為是實在物的屬性的邏輯組織中的內容。”[1] P114所以在結構主義看來,結構的整體和部分同樣顯示價值和意義,不論組合抑或分割。試想若把十一個事件當中的任何一個剔除,故事的完整度和連貫性必然受損,可以斷言十一個事件的結構和整個故事結構的內指性保持了一致,但不可忽視般地從屬與整個故事。
再看四行中除第二行的其他三行,忽略空格處,每一行的第一個事件與最后一個次事件保證了較強的因果關系,起始和終止之間的一個或兩個事件或阻拒結果或加速結果,都不能影響到終結性事件的出場。它們的在場與否只能為事件的發展增設波瀾,不論正性的還是負性的,扭轉乾坤的設想總是徒勞。譬如第一行中的(二)、(五)事件中,就便相師和韋提希不在場,頻婆娑羅老來無子也強烈地暗示著王位有人繼承,否則事態戛然而止,故事本身也無發展必要。雖然兩個事件正性地積極地催生阿阇世,但無法決定阿阇世存在與否,就便沒有韋提希的受孕,也會有另一個王儲填補空白。總之,“老來無子”的命題必須打破,以便單個結構絕佳地服務于主體結構。第三行中的(四)事件仿佛完全可以抹去,毫不干擾后續事件,但它不是可有可無的。它的在場為結構內在張力儲備一支力量,不然王子日后不擇手段地幽禁父親則乏善可陳。況且,道人的不幸遭際對凸出“未生怨”主題的功用尤甚。道人一世被殺是為滿足國王求子心切,轉世再遭屠戮則積怨甚深,無形中加快了王子弒殺父親的節奏,也是結構的“邏輯組織”中不可或缺的因子。第四行中的(十)事件就其本身來看,意義屬性設置為零也未嘗不可,唯有將之置于(六)向(十一)的區間內才有阻擋拒絕的意味。然而這種阻拒性也未能翻轉占師預言導致的王子弒父,它在由第一行第一列到第四行第四列的對角線路徑上徒增微弱漣漪而后銷聲匿跡復歸平靜——國王無以拜托命喪黃泉的終結,不以任何獨立結構和我們認定的邏輯為轉移。“和弗洛伊德一樣,他(指列維-斯特勞斯)想找到對全人類的心理都有普遍有效的思維構成原則。這些普遍原則(假使它們存在的話)……被我們社會環境的認為條件所要求的各種特殊邏輯覆蓋了。”[2] P63顯然,在結構性的役使之下,“普遍原則”涉及“集體無意識”之時尚有一絲氣力。未生怨故事若隱若現地將“普遍原則”幻化為通識靈異的相師、道人、占師,企圖讓他們共同承擔一種結構負頡頑抗,降解邏輯的重重傾覆。怎奈它們曇花一現,在經變畫故事里演繹著業報、因果與輪回,可相較于對“普遍原則”的操練而言,姑妄是一種的嘗試。
回到故事結構,按從(一)到(十一)的排序毋庸置疑屬環環相扣式,從前到后層遞推衍,保障了受眾有跡可循地介入故事的結構中。單個結構就在各自的陣營里發揮著最大限度的功用,藉以使得故事得以順利開展。對于結構規則的恪守維持在“1+1≤2”的格局,以便對整體結構有超驗的依從。在第一行第一列到第四行第四列的對角線路徑上就標舉出父子關系的異種結構:即以“生”和“死”為直徑作圓,由生到死的π弧度所對應的正是頻婆娑羅,他從寄望得子到被子所殺而終結一生。由死到生的π弧度所對應的則是道人轉世化生的阿阇世,他從被國王所殺到重新降臨人世而開啟一生。誠如羅蘭?巴特所言,“我不覺之中曲解了死亡(就象彎彎曲曲的鑰匙一樣),我想想死亡就在一邊。這一奇思完全出于不假思索的邏輯。我讓生死相互對峙,由此我便游離于連結生與死的不可避免的兩極之外。”[3] P5富于張力的阿阇世與父親在生死的兩極對立,建構著文本結構的對峙與沖突。乍看之下,與其他題材在探討生命終極問題的取法上一般無二,但每一個獨立結構的無一例外地指稱著父子生死的二元對立,從屬于大文本結構而無疏離。
既然文本結構具備了無可比擬的優越性和邏輯上的優先性,每一個故事片段都有依附性并可以折射出文本結構,那么是否可以確證單個結構完全可以另立門戶、獨木成林?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未生怨故事中每一個子結構的在場無一不是指向最終的生死對抗,這是按部就班之后的回溯,帶著確定的結局返照各個子結構。拋開整體結構的終極指向,孤立地理解每一個子結構,無疑是困難的、易于偏離的。(一)至于(十一)的步步逼近構造出鏈條式的單向故事結構,再由父子二元關系加以統攝,韋提希充當著結構中的轉捩點,從而形成了一張關系網。由此透視,個中子結構的脈絡才清晰可見。
參考文獻:
[1] [法]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著,陸曉禾、黃錫光等譯.結構人類學——巫術?宗教?藝術?神話[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9.
[2] [英]埃德蒙?利奇著,王慶仁譯.列維-斯特勞斯[M].北京:三聯書店,1985.
[3] [法]羅蘭?巴特著,汪耀進、武佩榮譯.戀人絮語——一個解構主義文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作者簡介:時旭,新疆師范大學,碩士在讀,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