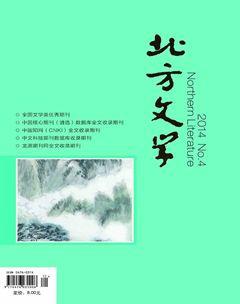論非語言信息的口譯
吳瑕 李俠
摘 要:作為和語言同樣重要的溝通渠道,在口譯研究中受到長期忽略的非語言信息應該得到更多重視。文章分析了非語言信息的定義、分類和功能,探索在口譯中處理非語言信息的方法。文章提出翻譯非語言信息的總體策略和具體措施相結合的方法。首先,譯員應該根據聽者的文化背景決定相關的總體策略。然后在口譯過程中,譯員根據具體情況采取具體措施,例如把說話者表達的非語言信息用非語言或者語言的形式譯出。
關鍵詞:非語言信息;口譯;文化
1.引言
近年來,口譯相關研究大量增加。然而,這些研究主要以口譯活動中的語言信息為對象,非語言信息受到嚴重忽視。
語言只是人類交流的一部分,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對非語言信息的研究表明,人類溝通一半以上是通過非語言行為而不是語言達到的。事實上,在溝通交流中(不管是一般的溝通交流還是口譯活動中的溝通交流),從說話者發出的信息大多數時候是語言信息加非語言信息,有時候則只有非語言信息。
在相同的語言和文化環境中,溝通順暢不僅是因為聽者可以完全聽懂說話者所講的內容,還因為聽者有相關的文化知識,能夠通過聽講話者的副語言,觀察講話者的體態語,來判斷講話者的言外之意和真實意圖。在不同語言和文化中,就需要譯員來擔任這方面的工作。
議員的主要職責之一就是達成有效的溝通如果說話者傳遞的信息包括語言信息和非語言信息,為了達到口譯的效果,譯員必須盡可能完全忠實地傳遞語言信息和非語言信息。在某些情況下,譯員的目標還包括要為其雇員工作,達到雇員想要的結果。而非語言信息包含了關于講話者意圖的豐富信息,更應該得到傳遞。這就要求譯員要有傳遞非語言信息的意識,能正確理解非語言信息,能以適當的方法處理非語言信息。
2.口譯中的非語言信息
2.1 口譯中非語言信息的定義
過去的研究者給非語言信息下過各種不同的定義。在文章中,非語言信息定義為在口譯活動中用于溝通的一切語言信息之外的信息。也就是說,作者從廣義的角度,口譯活動的范圍,以溝通為目的來討論非語言的信息。
2.2 口譯中非語言信息的分類
畢繼萬在其《跨文化非語言交際》一書中把非語言信息分成了四類:副語言,體態語,客體語和環境語。這四大類非語言信息都會影響溝通,但前兩類在口譯活動中最為重要,因其和語言信息緊密相連,并且承載了一定的文化內涵。
副語言,又稱類語言或伴隨語言,是伴隨、打斷或臨時代替言語的有聲行為。它通過音調、音量、語速、音質、清晰度和語調起到言語的伴隨作用。副語言主要包括音質(音幅、音速、聲調控制、發音控制等)、聲音特點(笑聲、哭聲、嘆息聲、呵欠聲、清嗓子聲等)、聲音的修飾(聲強、聲高、聲音的長度)和聲音分隔(嗯、啊、呃等)。此外,沉默停頓、插話聲音、話語失誤等一般也包括在內。在口譯中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對待沉默的態度、話輪的轉換和非語言聲音方面的文化差異。
體態語指的是傳遞交際信息的表情和動作,包括動作、姿態和規范。動作就是包括表情、手勢在內的身體運動。與動作相比,姿態是靜態的并且在交流中意義更少,但是有時候姿態反映了一個人的態度。規范是指體態語中人們習得的社會認同的部分,比如歡迎的方式。
語言、副語言、體態語共同構成了口譯活動中的完整信息。
2.3 口譯中非語言信息的功能
要了解非語言信息在口譯活動中的功能,必須從兩個方面來看待:語言方面和文化方面,即非語言信息和語言、文化分別的關系。
非語言信息和語言的關系可分成兩個大類:第一種,非語言信息通過重復、強調或者否定來補充語言信息。大多數情況下,語言信息和非語言信息是和諧一致的。比如肯定的語言加上一個微笑。但是有時候,講話者傳遞出來的非語言信息和語言信息正好相反,只有敏感的譯員才能觀察到,這時候就面臨對決策的選擇。第二種,非語言信息獨立于語言信息而存在。這種情況可能是由于語言信息的有限性或者講話者的主動選擇,例如講話者可以只做一個手勢讓別人走近。
文化是一個包羅萬象的概念,與語言信息、非語言信息都關系密切,但是文章只討論文化與非語言信息的關系。非語言信息通常都有豐富的文化內涵。除了個人風格的差異(無系統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無法理解非語言信息主要是因為文化差異。原因之一就是,一種文化中的非語言信息在另一種文化中沒有完全對等的表達。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方人很常用的那個在空中打引號的手勢,通常表示講話者說的話應該打上引號,并不是字面意思。另一個原因則是,同樣的非語言信息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意思有所不同或者完全相反。特別是當完全相反的時候,譯員必須干涉非語言信息的傳達。
議員應該明確非語言信息和語言、文化的密切關系,在口譯活動中以語言信息為主,兼顧處理好三者。
3.口譯中對非語言信息的處理
3.1 口譯中處理非語言信息的基本策略
譯員首先應該根據聽眾的文化背景來選擇在口譯活動中處理非語言信息的基本策略。選擇何種基本策略要由口譯服務的接收者的語言文化水平來決定。接受者在單向口譯中是固定的,在雙向口譯中是來回變換的,有可能是個體,也有可能是背影各不相同的群體。最后這種情況下,譯員決定基本策略難度更大。
本質上來說,采取何種基本策略取決于信息接收者對于信息發出者的文化的了解程度。在極端的情況下,信息接收者可能完全不了解信息發出者的文化,無法注意到講話者發出的非語言信息或者注意到了也理解不到。在這種情況下,譯員應該采取“最大化策略”,即翻譯所有相關的非語言信息,確保語言完整傳達。在全球化的今天,這種極端情況很少發生。另一種極端是,信息接收者來自多語背景,完全了解信息發出者的語言和文化,在不需要譯員的情況下能夠完全明白講話者的語言信息和非語言信息。在這種情況下,譯員當然可以對非語言信息采取“最小化策略”。
然而,這是兩個假設的極端點,在這兩個極端點之間有一條線性的連續統一性,這才是日常口譯活動中最普遍的需要處理的情況。在這個連續統一體上,信息接收者對發出者的文化理解從完全無知到完全掌握在不斷遞進,譯員應該根據具體情況先選擇一個處理非語言信息的基本策略。
3.2 口譯中處理非語言信息的具體方法
選擇了基本策略后,譯員需要運用一些具體方法來處理非語言信息。
第一種方法是用語言信息來翻譯非語言信息。因為語言信息和非語言信息聯系密切、相互補充,所以譯員可以把非語言信息轉化成語言信息。但這也是一種危險的方法,容易造成“過度翻譯”。
第二種方法是用非語言信息翻譯非語言信息。在大多數情況下,直接把原來的非語言信息傳遞到聽者是無意義的。但是在交替傳譯時,如果不再次傳遞非語言信息將會造成非語言信息和語言信息的分離,譯員可以選擇這種處理方法。此外,譯員在某些情況下也需要把講話者文化中的非語言信息翻譯成聽者文化的非語言信息。這需要譯員在語言表達、文化知識、非語言信息上有很高的修養,對譯員要求較高。
第三種方法是與雙方進行翻譯內容之外的溝通。這種方法運用于譯員不能完全理解非語言信息,或者不產生額外的溝通無法完全表達此信息的情況下,特別是當非語言信息和語言信息相矛盾的時候。如果涉及到的非語言信息太重要,不能忽略,譯員應該和講話者進行必要的溝通。
4. 結語
非語言信息在口譯中作用重大,在口譯研究中應該受到更多重視。一部分非語言信息可以直接從講話者傳遞給聽者,另一部分則需要譯員的幫助。由于非語言信息和語言、文化的密切關系,譯員處理非語言信息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文章探索了處理非語言信息的方法,那就是將基本策略和具體方法相結合。先根據聽者的文化背景選擇基本策略,然后在口譯過程中使用具體的方法。
為了提高非語言信息處理能力,譯員、口譯培訓者、口譯研究者都應該首先增強這方面的意識。處理非語言信息的能力可以通過自我訓練、口譯課程中的系統訓練、公開演講訓練和同聲傳譯訓練提高。模仿和錄像也是有用的輔助措施。深厚的文化底蘊更是至關重要。
參考文獻:
[1]Buhler, Hildegund.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A Multichannel Communication Phenomenon” [A], Meta: Translators Journal, 1985, 30:1:49-54.
[2]Ekman, Paul & Wallace. V. Friesin. “The Repertoire of Nonverbal Behavior: Categories, Origins, Usage, and Coding” [A], Semiotica, 1969, 1:1:49-98.
[3]Gile, Danial. Getting Started in Interpreting Research[M],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4]Munday, J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5]Pochhacker, Franz. 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6]Pochhacker, Franz and Miriam Shlesinger. et al. eds. The Interpreting Studies Reader[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205-336.
[7]畢繼萬/著,《跨文化非語言交際》[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
布羅斯納安/著,《中國和英語國家非語言交際對比》[M],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1
[8]常暉/文,“跨文化交際中非語言行為作用分析” [J],《重慶工商大學學報》2007,第5期
[9]高蕊/文, “談跨文化交際與非語言交際” [J],《語文學刊(外語教育教學)》2009,第6期。
[10]霍爾/著,何道寬/譯,《無聲的語言》[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
[11]李少彥/文, “口譯中超語言信息探析” [J],《中國翻譯》2011,第3期
[12]賈國偉/文,“語言與非語言符號的功能—語言交際中的體態與運用” [J],《海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第1期。
[13]李永生、張俊玲/文,“論非語言行為的語義特征” [J],《青島教育學院學報》 2001,第2期
[14]連淑能/著,《英漢對比研究(增訂本)》[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15]樓有根/文,“跨文化交際中的非語言行為問題探討” [J],《長江大學學報》2006,第2期
作者簡介:吳瑕(1988-),女,四川人,碩士,四川大學錦江學院外國語學院助教,研究方向:翻譯與英語教學;李俠(1985-),女,四川人,碩士,四川大學錦江學院外國語學院助教,研究方向:翻譯與英語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