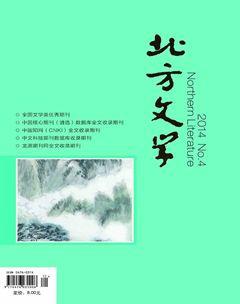《漢書?藝文志》體例
摘 要:《漢書?藝文志》(以下簡稱《漢志》)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古典文獻目錄著作。欲通知《漢志》,必先明其體例。《漢志》以劉歆的《七略》為藍本,然二者不盡相同,體現之一便是《漢志》有所謂的“出”、“入”、“省”。文章對此書中的“出”、“入”、“省”語例作了窮盡性地統計,并對前人的見解作了詳盡性的羅列,同時對其歷史意義予以歸納分析,此文屬于一篇總結性的文章。
關鍵詞:漢志;出;入;省;意義
《漢志》是東漢班固依據劉歆的《七略》所著,約于唐宋之際,《七略》亡佚,《漢志》便成為我國最早的一部文獻目錄著作。了解并掌握《漢志》的著書體例是我們研讀《漢志》的首要工作。班固稱于《七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而成《漢志》,他的修書宗旨究竟是怎么實踐的,本文僅從“出”、“入”、“省”入手來探討《漢書》的著書體例,并簡單分析它們的歷史意義所在。
一、語列羅列
在對《漢志》中“出”、“入”、“省”體例進行辨析之前,我首先羅列出了文中的全部語例,分別如下:
(一)“出”
《漢志》中僅有3處于篇目總數后注出了“出”這一字樣,它們分別是:
1、《六藝略 ?樂》:“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 。”[1][P1711]
2、《諸子略 ?大序》:“出蹵鞠一家,二十五篇。” [1][P1745]
3、《兵書略 ?兵權謀》:“出《司馬法》入禮也。”[1][P1757]
(二)“入”
《漢志》中有7處于篇目總數后注出了“入”這一字樣,這一頻率顯然多于“出”,它們分別如下:
1、《六藝略?書》:“入劉向《稽疑》一篇。” [1][P1706]
2、《六藝略?禮》:“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1][P1710 ]
3、《六藝略?小學》:“入揚雄、杜林二家,二篇。” [1][P1720]
4、《諸子略? 儒》:“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 [1][P1727]
5、《諸子略? 雜》:“入兵法。” [1][P1724]
6、《詩賦略? 陸賈賦之屬》:“入揚雄八篇。” [1][P1750]
7、《兵書略 ?兵技巧》:“入蹵鞠也。”[1][P1762]
(三)“省”
《漢志》中僅有3處于篇目總數后注出了“省”這一字樣,它們分別如下:
1、《六藝略 ?春秋》:“省《太史公》四篇 。”[1][P1714]
2、《兵書略 ?兵權謀》:“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重。”[1][P1757]
3、《兵書略? 兵技巧》:“省墨子,重 。”[1][P1762]
從所羅列的語例來看,我們也許會對“出”、“入”、“省”有一個初步的認識,那這一體例究竟怎么理解,它們之間是否存在關系,我們首先來看前輩們對這一體例的理解。
二、前人觀點
1、顏師古在《漢志》注中曰:“此凡言入者,謂《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與此同。”[1][P1706]
2、《漢書藝文志注釋匯編》引用章學誠《校讎通義》內篇二:“注省者,劉氏本有而班氏省去也。注出入者,劉錄于此,而班錄于彼也。”[2][P51]
3、曹慕樊認為:“出,班固認為《七略》對一書分類不當,作了調整;入,新增原為《七略》所沒有的書籍。省有幾種情形:一是在書目上刪去,多半是班固認為《七略》把同一書分入兩類,便在一類中刪去它。二是省篇,在一書中刪去若干篇把它另歸一類。三是省文,如蒙上而省例。”[3][P38]
4、姚明達認為:“所入之書僅劉向、揚雄二家之作,為向、歆校書所未收者。所出諸家,則原文重復,故省之也。”[4][P208]“非但有所增減必加注明而已,即移動一書入他類,亦已注明。”[4][P208]
5、顧實認為:“至于師古所云新入者,書家之劉向《稽疑》一篇,小學家之揚雄、杜林三篇,儒家之揚雄所序三十八篇,賦家之揚雄八篇,皆班氏所新入也。”[5][P30] “兵權謀、兵技巧皆有班氏注省《伊尹》、省《墨子》云云,蓋本《七略》兩載而《班志》省之”。[5][P66]
通過對以上各家觀點的仔細比較與分析,我們會發現五家的觀點大體一致,然仍存在分歧。首先,五家除了章學誠(所收五家的概念除了曹慕樊先生作過系統的闡釋外,其余各家的觀點都是在著作中零星收集的,可能存在缺漏)以外都談及到了“入”,而且看法一致,都認為是班固新增加的篇目,然根據《漢志》中“入”的語例來看,我們不難會發現,其實“入”的對象不僅包括新增加的篇目,還包括調整以后的篇目,即姚明達所說的“移動一書入他類”的篇目,這些篇目顯然是《七略》原有的書目。
五家唯獨顏師古沒有談及到“省”,其余各家的觀點一致,即刪除《漢志》中重復篇目的標志用語。
于“出”這一用語,顏師古一筆帶過,“其云出者與此同”,[1][P1706]不知所言,章學誠認為出與入是對分類不當者的調整用語;姚明達在闡述“出”與“省”的關系時過于含糊,他沒能指出“出”的功能所在,似乎二者相當,對初學者難免會造成誤導,不過欣慰的是他之后又闡釋道,“非但有所增減必加注明而已,即移動一書入他類,亦已注明。《兵書略》之‘出<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禮>,實為《漢志》對《七略》部類之唯一變動。”[4][P208]從這一句話我們可知“出”的用意所在;曹慕樊對“出”的解釋很明確。
三、我們的觀點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對“出”、“入”、“省”得出以下理解:“出”是班氏對分類不當篇目的調整的用語,如:《六藝略 ?樂》:“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 。”[1][P1711]“入”是班氏指出新增加的篇目與篇目調整之后去向的用語。新增加的篇目有劉向、揚雄、杜林三家,如:《六藝略?小學》:“入揚雄、杜林二家,二篇。” [1][P1720] 表明篇目調整后的去向的如:《六藝略?禮》:“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1][P1710] “省”是刪除《七略》中重復收錄篇目的用語,《兵書略 ?兵權謀》:“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重。”[1][P1757]
四、意義簡析
“出”、“入”、“省”是《七略》與《漢志》不同的表現之一,那班固的此番改動的歷史意義何在,在此作簡要闡釋:
1、班固對《七略》著錄的篇目的改動之處,特別注出了“出”、“入”、“省”的字樣,并未直接改動而不作說明,這才使得后人可據《漢志》考察《七略》的原貌,可見班固治學的嚴謹與慎重。
2、“出”某“入”某字樣的出現,我們可以看出班固對《七略》所收篇目的適當調整,如《兵書略?兵權謀》:“出《司馬法》入禮也。”[1][P1751] 再如陶志曾認為,《諸子略?雜》家“入兵法”前脫“出蹴鞠”三字,陶氏的觀點很是合理。
3、《漢志》中新增收了劉向《稽疑》一篇,揚雄的《倉頡訓纂》一篇,《揚雄所序》三十八篇,《揚雄賦》十二篇,杜林的《倉頡訓纂》和《倉頡故》,這些都是《七略》之后的新著,雖然撰述者和篇目的數量很是有限。
4、“省”這一體例的制定,可見班固“深知書目的體裁,堅持史志的特點”[3][P44],他認為《漢志》是總目,目的在于通載一代或者數代的書,不是很注重所收書目的內部結構。
以上我詳盡地羅列了《漢志》中的“出”、“入”、“省”的語例,并結合前人的研究對三者的定義以及它們的歷史意義作了簡要分析,以期加深對“出”、“入”、“省”的認識與理解。
參考文獻:
[1]班固.漢書[M] .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3.6.
[2]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匯編[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 1983.6.
[3]曹慕樊.目錄學剛要[M].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4.
[4]姚明達.中國目錄學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5]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
作者簡介:馬躍(1989-),女,漢族,陜西人,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2013級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方向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