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忠信:“直立”的爬行者
李淳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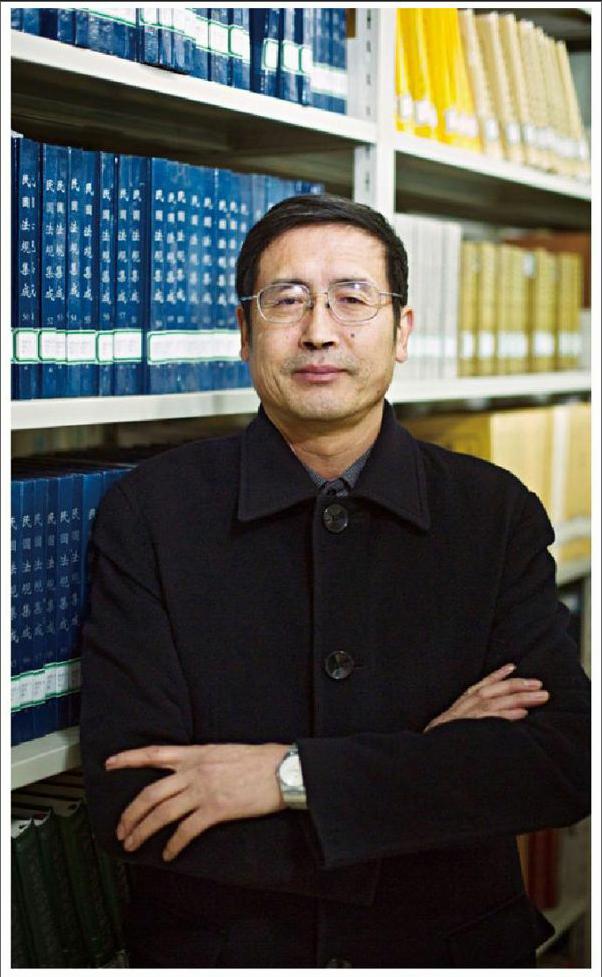
范忠信在做民間批評,又似乎被體制認可接受。在思想上,他希望真正“直立行走”,那是“人”的定義的一部分。這一次的爬行,他也是在闡釋著這個定義。
2014年1月15日夜晚6點半,杭州。
路燈下,寒風中,范忠信身著一件筆挺的黑色大衣迎了出來,他那筆直的站姿,讓人印象深刻。而在半個月前,新年的第一天,他卻以爬行的姿態為世人所知。
這個印象是矛盾的,正如他矛盾著的人生經歷和思想沖突。
賭約
2014年元旦來臨之前的一段時間里,范忠信一直困擾于一個一年前的賭約。
2013年1月1日,他在微博公開打賭:“我堅信,2013年里,除了民族區域自治的地方外,其他所有省市會實現縣鄉級公務員財產公示。要不信,咱們打一個賭。如果我輸了,說明我的智商不如豬,罰自己爬行一公里。”
時間快到了,縣鄉級公務員財產公示渺無蹤影,許多人開始在他的微博上跟帖鼓噪。“怎么樣?爬不爬?什么時候爬?在哪里爬?”
“都在那催,還給他做倒計時。”范忠信的妻子段老師說,“爬不爬呢,當時確實矛盾。我怕他身體受不了,一公里那不是鬧著玩的,而且這畢竟是有失斯文的事。”
有同事、朋友提醒說,不能爬,最好把以前發的微博刪個干干凈凈,當作沒這么回事。段老師是這次行動的堅定支持者,她認為得爬。
“你不去,別人以后都看不起你,你以后什么事都沒有資格說話了。”段老師說:“這樣的話,我寧可你爬出點什么問題,也不能把這事擱置下來,一直讓人罵。”聽妻子一敲鼓,范忠信說,爬就爬唄,小時候什么重體力活都干過,這點小事兒能把我身體怎么樣?
決定了要爬行,范忠信就在微博上表示將履行諾言,這時候更多建議又來了。他的一個學生,也是當教師的,覺得光是爬還“不到位”,應該穿一件白襯衫,胸前背后掛幾塊牌子,寫上“公務員財產公示”“政改爬行”之類的內容。段老師說,那不行,那就把事情給鬧大了,“我們的目的僅僅是兌現諾言”,不是示威,不是發泄怨氣。
現在只剩下爬行地點的問題了。范忠信想,既然是履行諾言,是不是應該到人多的地方去?這樣有人看得到,能夠證明你做過了。剛這么一想,他就接到了一些電話,讓他不要有任何妨礙秩序的行為。范忠信此后連續發了幾條微博,承諾::第一,將選擇在荒郊野外進行;第二,不會與任何人同行。“這樣大家都放心。”
范忠信住在余杭鎮,家附近幾百米就是南湖,是一個泄洪區,荒郊野外,野鴨成群,行人稀少。元旦這天,他和妻子來到了南湖邊,他爬行,妻子從旁錄像作為證據。
一開始選擇的是南湖西岸泥土碎石鋪成的鄉村土路,但只堅持了百米左右。“手掌被石子硌得很痛,一會兒膝蓋就磨出了血。另外因為陽光太強,手機屏幕一片漆黑,錄像時根本看不清人是否在鏡頭里。”
于是他換到了路下邊湖濱草地上。枯黃而修長的草,遠看很柔軟,一接觸才知道,短草茬子、小刺球遍布,照樣傷掌破膝。范忠信自我安慰:總比石子路上好,這已經是最舒服的一個選擇了。
范忠信先用步子丈量出50米、100米、200米的距離,插根木棍或擺塊磚頭作標記。標好之后,開始來回爬,斷斷續續,中間休息了多次。連石子路上爬的那一段一起,一共爬了7段,或100米或200米,累計下來正好夠1000米數,他才收工。
爬行的時候,也有人騎著摩托車經過,看著新鮮,問他在干什么。范忠信說是在做“脊椎保健”。對方看了一會,反反復復也就一個姿勢,沒啥特別,扭頭走了。
體制邊緣
當天下午兩點多回家,不及洗沐,就開始整理視頻、照片。4點左右,范忠信開始在新浪微博上傳視頻,花了近7個小時,一直到晚上快11點才傳完。
微博中,他僅僅介紹了自己履諾的經過,沒有附加別的什么說辭和引申。他說,爬行舉動,除了履行承諾,本身已經表達了另一層意思,即“一名公民對于加快廉政建設法制化的愿望”。
就后者而言,范忠信認為自己是膽怯、懦弱的。“果真是男子漢大丈夫,要爬就到大庭廣眾之下去爬。然而,一方面受不了眾目睽睽之下的尊嚴掃地,另一方面事先接到各方善意提醒,我知道如果去人多的地方,也許根本無法開始。”
視頻公布之后,喝彩者居多,“幾乎是一邊倒”。范忠信有個老同事,因為立場觀點不同已經很久不相往來了,但這回看到消息和視頻,也發微博說,這是個爺們兒,我們還是朋友。
“總體看來,正面效果遠遠大于負面影響。因為我知道,如果我不去爬,連我的學生都會看不起我。”
懷疑者寥寥,懷疑的方向僅是,范忠信是不是在炒作?是某種行為藝術?對于這樣的質疑,他說應該坦然面對。傳統、刻板的范忠信,一者自稱根本無意炒作,二者他很清楚,對自己過去數十年在法學圈子留下的名聲來說,任何“炒作”將意味著前程毀棄,他坦承自己目前還沒有這個膽量。
他知道這有可能帶來麻煩,然而要讓更多人關注公務員財產公示,別的方式似乎不管用。決定要爬行之后,妻子段老師明確告訴他,真要有麻煩,也要敢承擔;不能說既要這么做,又不想承擔任何后果。范忠信說,那是自然的。
反響比想象中好。公務員財產公示的話題再一次成為熱門,這是他希望看到的。作為一名法學學者,看到現實中的許多做法公然與自己精熟的法理或國家法律原則相悖,二者無法互相印證,精神上的苦悶難以避免。
所以,2013年元旦,看到十八大后的全面加快和深化改革的新政氣象,看到縣鄉公務員財產公示在很多地方試點成功,聽到“12·4”憲法實施30周年紀念日“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他“特別興奮”,他感覺到了理論與現實相銜接的可能。于是他發出了樂觀的賭約。
這一賭,也許太過樂觀,但范忠信說,只有基本認同體制、寄望溫和改革的人,才會如此樂觀。
履約后幾天里,不斷有人在網上或打電話來,邀約“接力爬行”“多人爬行”,效仿“黑色幽默”的意見表達方式,推動公務員財產公示。范忠信一直謝絕:該表達的已經表達完了。endprint
“無論立場左右,事實上大家都不會反對公務員財產公示,政府也不否定這一訴求的積極性。但現實可能比自己想象的要困難,需要更多的時間。”爬行過后,范忠信似乎“清醒”了許多。
和許多言辭激烈的公共知識分子不一樣,范忠信并不愿意將自己打扮成一個斗士。“坦白地講,我不愿意被體制視為異端或異己者,因為我對現體制并沒有完全失望,我認為它可以通過溫和漸進的法制改良,實現更遵奉人類文明共同成就的進步。”
范忠信說,在體制內或以改良體制的口氣去說話,聽的人不會格外緊張反感,從建設性角度去看去聽的人反而還會更多。反之,習慣于高聲整體否定體制,好意都會被從最壞的方向去揣測,不但沒有人聽,很快還會喪失說的機會。
“所以我盡管率性,卻還是有自己的分寸的。”
公共空間的分寸
把握分寸是個技術活兒,范忠信其實也并不擅長。
去年三四月份,他發了個微博,談自己對大學發展的意見,認為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必須首先解決學術自由、學校自治問題。
他由此受到了一些嚴肅的忠告,也感覺到了一些壓力。
“有人天天把這些微博復制舉報到公安局或有關部門,學校領導要我注意分寸,新浪網管也不時刪帖提醒。”
發言分寸是否適合,自認為“尚有分寸”的范忠信常常自己渾然不覺。
他的文盲老母親,主動幫他把握分寸,83歲的老母親3次電話提醒兒子:“聽說你老在外面說話,領導聽了不太高興。你能不能不說,好好教你的書,好好寫你的文章?別惹麻煩。”
“我很奇怪,老母親怎么會知道我在微博上說什么?”
原來是當中學教師的大妹妹告訴了母親。她跟母親說,有個薛蠻子在網上說話很多,后來又有違法行為,就抓了起來,關進去了,還到中央電視臺承認自己在微博上發言有錯誤。薛蠻子是高干子弟,都有這樣的后果,二哥一個農家子弟,還亂說話,真讓人擔心。
面對母親,范忠信只有唯唯諾諾。
現在范忠信的新浪微博,粉絲7萬多,算不上有多大影響力。被舉報和批評后,他顯著減少了上微博的頻率,有時一周都不看一眼。他甚至發出微博,宣布將“休博”。
他并不想成為一名公共知識分子,而更希望做一個純粹的學者。他擔心在微博上活動太多,可能會影響學術研究、學術心態和學術視野,或者讓同行覺得熱衷名利,喜歡拋頭露面。
這也是范忠信的“分寸”的一種反映。他認為,批評應該是在學術基礎上的理性說理,沒必要情緒化,激烈地去表達。“冷靜或激烈,說的其實還是同樣的道理。”
因此人們看到,范忠信一方面在做民間批評,另一方面又似乎被體制認可接受。
2009年,他入選中央政法委和中國法學會的“雙百講師團”(百名法學家百場報告會)成員。“講師團”專給地方黨政干部上課,講法治理念、法治體制、權力制衡、防止權力濫用的古今中外經驗教訓。
他講課,都是放開了說,“不會為了迎合誰而去扭曲學術理論本身”。講完后一起吃飯時,他會半開玩笑地詢問干部們的聽課感受:“有沒有意見?會不會舉報我呀?”
有官員回答:“還好。有的老師也是講一樣的內容,但言辭激烈些,聽著刺耳;你講的不太刺耳,雖然不一定贊成,但也不覺得有什么大問題。”
這次爬行諫言以后,還會不會有單位敢請自己講課,范忠信有點拿不準了。
性格與思想的矛盾體
范忠信的名字是母親起的。母親是個文盲,但給自己的3個兒子起了3個十分“高大上”的儒家名字:忠恕、忠義、忠信。
母親是個共產黨員,很正統,她認為世界應該都由白求恩、張思德們組成。對孩子,她的嚴厲在全鄉出了名。在母親的認識體系里,對與錯都很絕對。
范忠信回憶,上小學第一天,回家興奮地對母親說:“老師很矮很矮,我打得過他,我不怕。”話音剛落,就挨了母親重重的竹尺懲戒,母親憤怒地說:“再矮小,那也是你的老師,他教給你知識,讓你將來做個有用的人。沒有文化,以后你就是廢物,一輩子要記得,永遠敬重你的老師。”
對錯的絕對,讓范忠信后來的成長歷程顯得很矛盾,撕裂。
他自小就在革命英雄主義的教育中成長,艱苦奮斗,英雄氣概,工農兵戰天斗地,這些宣傳內容對他的影響極大。“初中以前老是想,為什么我的身邊就碰不到那些破壞分子,也讓我能去舉報或搏斗,從而成為英雄呢?”他甚至埋怨家鄉沒有鐵軌供壞人破壞,也沒有什么人落水供自己去救。
后來上了大學,感受就變了。1980年上本科,1984年讀碩士,都是改革開放后思想最解放的年代,他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三個百花齊放的時期”。
大學時接受的思想,和從小接受的教育,形成強烈的反差,精神上十分沖突。
現在的范忠信,看上去似乎處理好了這一矛盾。他把自由的思想、獨立的精神、自主的人格作為學術研究和教學工作的準繩,而把“革命英雄主義”、“艱苦樸素的作風”留給了日常生活。
生活保持著嚴謹、規矩、勤儉、質樸的習慣,每天聞雞起舞,跑步鍛煉。現在,嚴重的霧霾天讓這個習慣難以為繼。
范忠信說,在思想上,他希望真正“直立行走”,那是“人”的定義的一部分。這一次的爬行,他或多或少也是在闡釋著這個定義。
作為典型的80年代大學生,他也曾被激情燃燒所振奮,被新學所啟蒙。1988年秋,《瞭望》周刊發起“我與這10年”的征文,29歲的范忠信應征并獲獎,文章題為《從臣民到公民》,他覺得是對自己和那一代人精神面貌巨變的一個闡釋。
學生評價范忠信,生活上像個“老勞模”,思想上卻像個“幫教對象”。作為一個體制內的思考者,盡管范忠信已經盡量委婉地發言,學生依然認為他太激進。
范忠信說,自己沒有變,是學生變了。現在的學生,對他們那一代人的理想似乎早已沒有同感。除了考研、考公務員、考司法、考外語,考數不清的證件,其它的似乎都不關心,除了考試需要背誦的“兩課”內容和時事政治之外,國家大事似乎與他們毫無關系。
“不成熟!”這是不少學生在他爬行之后的反應。少年二十,卻批評知天命的老師不成熟,范忠信心情沮喪。
讓他有時不得不放棄“聞雞起舞”的霧霾天,學生們也不關心。他們可以天天戴口罩,但那口罩也像是“封口膠”一樣,讓他們同時失去了為爭取藍天白云而說話的能力。
“只要不是馬上有生命危險,就還可以容忍,反正又不是我一個人受罪。”范忠信說,包括政治上的、社會生活上的“霧霾”,學生們也是這么看的。
他所在的法學界,也呈現出一種特別的逆反規律—越年長的學者思想越解放,越年輕的越是老成持重、謹小慎微。“江平、張思之、郭道暉、李步云、漆多俊等老先生,都80多歲了,往往思想解放如‘五四時代的青年。下一波,是我們這些在上世紀80年代成長起來的人,思想較為解放,尚有批判精神,但比起老前輩又似乎力道差一些。再往下,‘80后‘90后,似乎都成熟冷峻得出人意料,任何事情,只要與自己眼下找工作掙大錢無關,都可以‘心如止水。”
現在的社會情形已經與80年代對調,現在是年輕人在袖手冷觀中老年人的社會責任擔當行為,評判長輩們的“另類”“不成熟”。范忠信感嘆,年輕人的腦子,似乎已被格式化了。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