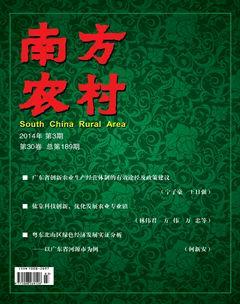江蘇省農民收入的區域分異及格局演化
李釵,馬曉冬
摘 要:利用2001-2011年江蘇省農民純收入數據,分析了江蘇省農民純收入變化的區域差異及格局演化。結果顯示:江蘇省農民純收入持續增長,但是地區間絕對差異逐漸增大;農民純收入的高收入區和較高收入區在蘇南地區集聚,中等收入區、低收入區和較低收入區在蘇中和蘇北地區連片分布;從增長速度看,2001-2005年農民純收入增長速度較快的縣域集中分布在蘇南地區,2006-2011年則集中分布于蘇北地區,兩個階段發生了明顯的南北轉換;依據農民純收入水平和增長速度將江蘇省劃分為五種類型區:高收入高增長型、中收入高增長型、中收入低增長型、低收入高增長型、低收入低增長型。
關鍵詞:農民純收入;區域分異;時空格局;江蘇省
中圖分類號:F323.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2697(2014)03-0040-05
一、引言
農民收入差異一直是學術界和政府相關部門關注的熱點,從區域差異的視角對農民收入進行綜合分析也成為人文地理學研究的重點。江蘇省農民收入的區域差異明顯,特別是蘇南和蘇北地區農民純收入的擴大,不利于區域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深入分析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區域差距對于推進江蘇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一些學者主要從農民收入結構的視角,分析影響農民收入結構的主要因素[1],對江蘇省農民收入與三次產業之間的關聯度及收入來源結構進行分析[2],指出江蘇省農民收入主要來源于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收入[3];從農民收入區域差異的視角,分析農民收入區域差異狀況及其變化趨勢[4-5],得出農民收入水平相似的地區在空間上集聚分布的結論[6-8],并揭示了農民收入差異的空間格局及其演變態勢[9-13]。目前,多數研究以短周期或靜態的分析為主,統計分析占據主流,空間分析相對不足。本文從時空的角度,以2001-2005年和2006-2011年兩個時間段來分析江蘇省農民收入的差異,動態的展現出江蘇省農民收入地域格局的演化。
二、研究區域與技術路線
(一)研究區域
江蘇省是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經濟較為發達的省份,共有25個縣級市,24個縣。2011年全省GDP為 49110.27億元,占全國的10.4%,人均GDP 62290億元,是全國人均水平的1.8倍。2011年,江蘇省的農村居民純收入10805元,是全國人均水平的1.5倍。由于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江蘇省內農民純收入存在很大的地域差異。以2011年為例,蘇北地區(徐州、連云港、宿遷、淮安和鹽城)的農民純收入的平均值為9166元;蘇中地區(揚州、泰州和南通)的農民純收入的平均值為11220元;蘇南地區(蘇州、無錫、常州、鎮江和南京)的農民純收入的平均值為15058元,是蘇北地區農民純收入平均值的1.64倍,蘇南和蘇北農民收入差異明顯。
(二)數據來源
縣域經濟是國民經濟的基本單元[6],本文選取江蘇省62個市(縣)作為研究單元。數據來源于2002-2011年的《江蘇省統計年鑒》,以江蘇省縣域農民純收入作為分析數據。由于研究單元的變化,統一將市轄區進行歸并,如南京市玄武區、六合區均劃入南京市轄區;對行政區劃調整以及名稱變更的單元,統一以2011年為基準進行修正。
(三)技術路線
以江蘇省農民純收入的絕對差異和相對差異來研究農民收入的動態特征;以農民收入的水平格局演化和增長格局演化來研究江蘇省農民收入格局演化的,總體特征,并劃分出江蘇省農民收入的類型。
三、江蘇省農民收入變化的總體特征
(一)農民收入持續增長
2001以來,江蘇省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穩步增長,農民純收入的均值由2001年的3879元增至2011年的11468元,增長了近3倍,最大值由2001年的5874元增長至2011年的17460元,最小值由2001年的2412元增長至2011年的7451元,極值差由2001年的3462元增長至2011年的10009元,標準差由2001年的921.76上升至2011年的2896.11,以上指標可以明顯的反映出江蘇省農民收入持續增長,2006年后增長速度加快,且差異逐漸增大。
圖1 2001-2011年江蘇省農民人均純收入變化
(二)地區間絕對差距逐漸增大
2001-2005年,蘇南地區農民純收入從4814元上升到6911元,每年增長524.25元;蘇中地區由3593元上升到4975元,每年增長345.64元;蘇北地區由3230元增加到4241元,每年增長252.75元;蘇南和蘇北兩個區域每年增長的絕對差距為271.5元。2006-2011年,蘇南地區農民純收入每年增長1329.2元,蘇中地區每年增長1059.19元,蘇北地區每年增長894.4元,蘇南和蘇北每年增長的絕對差距為434.8元,說明2001年至2011年,江蘇省地區之間的農民純收入的絕對差距逐漸增大。
(三)地區間相對差距逐漸減小
為排除樣本平均值對標準差指標的影響,進一步采用極熵和變異系數對江蘇省縣域農民人均純收入的相對差異進行分析。從總體趨勢看,極值和變異系數由2001-2011年先增大后減少,極熵自2001年的2.4353增長至2007年的2.5053,而后又降至2011年的2.3433,變異系數由2001年的0.2412增至2006年的0.2788,而后又下降為0.2556,這說明江蘇省農民純收入的相對差異先增大又減少,有逐漸收斂的趨勢。
表2 2001-2011年江蘇省農民純收入統計
年份 極熵 變異系數
2001 2.4353 0.2412
2002 2.4496 0.2415
2003 2.4993 0.2662
2004 2.4925 0.2697
2005 2.5004 0.2775
2006 2.5042 0.2788
2007 2.5053 0.2777
2008 2.4928 0.2755
2009 2.4456 0.2693
2010 2.4033 0.2625
2011 2.3433 0.2556
四、江蘇省農民收入的格局演化
(一)農民收入的格局演化
分別以2001-2005年和2006-2011年江蘇省農民純收入的平均值(S0)為基準,將江蘇省62個市(縣)的農民純收入(S)與之相比較,江蘇省縣域農民純收入水平劃分為以下五種層次:
表3 農民純收入水平類型區
類型 劃分標準
高收入區 150%
較高收入區 125%
中等收入區 100%
較低收入區 75%
低收入區 S/S0<75%
2001-2005年,江蘇省農民純收入的平均值為4505元/人,高收入區有6個(占總數的9.68%),較高收入區有5個(占總數的8.06%),中等收入區有13個(占總數的20.97%),較低收入區有30個(占總數的48.39%),低收入區有8個(占總數的12.90%);2006-2011年,江蘇省農民純收入的平均值為8351元/人,高收入區有7個(占總數的11.29%),較高收入區有4個(占總數的6.45%),中等收入區有14個(占總數的22.58%),較低收入區有24個(占總數的38.71%),低收入區有13個(占總數的20.97%)。
表4 江蘇省農民純收入水平類型區數量
高收入區 較高收入區 中等收入區 較低收入區 低收入區
2001-2005 6 5 13 30 8
2006-2011 7 4 14 24 13
由圖1和圖2可知,高收入區和較高收入區集中分布在蘇南地區,中等收入區和較低收入區主要分布在蘇中和蘇北地區,低收入區則主要分布在蘇北地區。由第一階段至第二階段可知,吳江市由較高收入區變為高收入區,高收入區和較高收入區總數保持不變,說明江蘇省農民收入水平較高的蘇南地區依然保持領先優勢;句容市由較低收入區轉變為中等收入區,新沂市、淮安市、沭陽縣、東海縣和響水縣由較低收入區轉變為低收入區,中等收入區、較低收入區和低收入區的數量總數沒有變化,但是,較低收入區的范圍縮小,低收入區范圍明顯擴大,說明蘇北地區農民純收入在增加的同時,發展速度過于緩慢,與蘇南地區的差距明顯拉大,造成江蘇省內部區域差異擴大。
江蘇省農民純收入可以分為三個梯隊,以蘇州、無錫、常州為代表的蘇南地區為第一層次,這一區域受上海的影響,積極承接上海的產業轉移,鄉鎮企業蓬勃發展,農村經濟發達,農民收入水平較高,以高收入區和較高收入區為主;以南通、揚州、泰州為代表的蘇中地區為第二層次,農民純收入類型區以中等收入區為主;以徐州、連云港、宿遷為主的蘇北地區為第三層次,這些地區以農業為主,第二、三產業不發達,農民純收入類型區以較低收入區和低收入區為主。
(二)農民收入增長的地域演化
分別以2001-2005年和2006-2011年江蘇省農民純收入的平均增長率為基準,將江蘇省62個市(縣)的農民純收入的增長率與之相比較,可以分為高增長地區和低增長地區,兩個階段的分布特征如下:
2001-2005年江蘇省農民純收入增長速度較快的地區主要集中在蘇南和蘇中的蘇州、無錫、常州、南京、南通(啟東市除外)、泰州、揚州、鎮江和蘇北的連云港市(東海縣除外),其余地區則為增長速度較慢的地區,主要分布在蘇中和蘇北地區。2006-2011年江蘇省農民純收入增長速度較快的地區主要集中蘇北和蘇中地區的徐州(豐縣、新沂市除外)、連云港、宿遷、淮安、鹽城(阜寧縣、射陽縣除外)、泰州(興化市除外)和南通的如東縣、如皋市等,增長速度較慢的區域則主要多分布在蘇南地區。
2001-2005年增長速度接近的地區比較集中且連片分布,增長速度較快的地區主要集中在蘇南和部分蘇中地區;2006-2011年分布則較分散不集中,但是增長速度較快的地區明顯分布于蘇北和蘇中地區,蘇南地區增長速度較慢。兩個階段農民純收入增長速度類型區發生了明顯變化,出現了顯著的南北對換,蘇南地區增長速度變慢,蘇北地區增長速度變快,雖然蘇南蘇北地區農民純收入的絕對差異依然很大,但是蘇南與蘇北之間的差距有變小的趨勢。
五、江蘇省農民收入的類型分區
2001-2011年,江蘇省農民純收入的全省平均值為6117元,江蘇省62個市(縣)的農民純收入的平均值高于全省平均值的為高收入地區,其余則為低收入地區;2001-2011年,江蘇省農民純收入的平均增長率為11.41%,江蘇省62個市(縣)的平均增長率高于11.41%的為高增長區,低于11.41%的為低增長區。根據2001-2011年江蘇省農民純收入水平及增長速度可以將江蘇省劃分為以下五種類型:
圖4 江蘇省農民收入的類型分區
六、結論與討論
(一)結論
文章通過定量的分析,對江蘇省農民收入的地域差距及其演化進行了研究,并劃分了地域類型。研究表明:從時間序列來看,江蘇省農民純收入在研究期間呈逐年增加的趨勢,但是,由于蘇南和蘇北地區農民收入增加的幅度不同,導致蘇南和蘇北地區農民收入的絕對差距增大。從空間格局來看,江蘇省農民收入水平呈現出由南向北梯度遞減的空間格局,且各類型區在空間上集聚連片分布,發達區和較發達區集中分布在蘇南地區,欠發達區和次發達區主要分布在蘇中和蘇北地區,貧困地區則主要分布在蘇北地區,南北差異顯著。2001-2005年蘇南地區農民收入的增長率比較高,使蘇南地區農民收入上升到比較高的水平上;而2006-2011年蘇北地區大力發展農業,農民純收入水平也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是與蘇南地區相比還是有一定的差距。綜合江蘇省農民收入的水平和增長速度,江蘇省農民純收入可以劃分為高收入高增長型、高收入低增長型、中收入高增長型、中收入低增長型、低收入高增長型和低收入低增長型六種地域類型。
(二)討論
江蘇省農民收入表現出明顯的南北差異,農民收入水平呈現出由南向北遞減的趨勢,地域分異現象比較明顯。本文認為造成這種空間差異的原因主要有四點:1.區位條件。地理區位是影響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非農就業的一個重要因素,經濟區位、地理鄰近性等因素對農業生產及農戶收入的作用越來越大[14]。蘇南位于我國綜合實力最強的長江三角洲經濟區的中心,受中心城市上海的影響,農民大多從事非農就業,農民收入中工資性收入所占比重較大。蘇中位于長江三角洲經濟區的邊緣,距離中心城市上海的距離較遠,缺乏具有強大輻射作用的中心城市,區位優勢不明顯。蘇北位于我國經濟較為落后的中部地區,距我國經濟發達地區相對較遠,受經濟中心的吸引和輻射作用比較弱,區位優勢較差,農民大多從事農業活動,工資性收入比較少。2.城鎮化水平。20世紀80年代初,江蘇省提出“以城市為中心,小城鎮為紐帶,以農業為基礎”的發展思路,有計劃的發展小城鎮。蘇南以此為契機,大力發展鄉鎮企業,極大地推動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創立了聞名遐邇的蘇南模式,農民收入大幅提升。以2011年為例,蘇南的城鎮化率為71.9%,而蘇中和蘇北的城鎮化率分別為57.5%和53.3%。3.產業結構。以2011年為例,蘇南地區的三次產業比例為:2.3:52.9:44.8,蘇中地區的三次產業比例為:1:54.3:38.6,蘇北地區的三次產業比例為12.9:47.9:39.2。蘇南地區的第二、三產業比例明顯高于蘇中和蘇北地區,非農產業對農村經濟的貢獻較大,這是蘇南農村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4.政策影響。1984年,江蘇省提出“積極提高蘇南,加快發展蘇北”的不均衡發展方針,使蘇南的地方政府與企業擁有更多的優先發展權[15],大力發展鄉鎮企業,蘇南農村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而蘇中和蘇北經濟發展緩慢,導致南北差距擴大。為了縮小南北差距,江蘇省又提出“區域共同發展”、“蘇北大發展”、“建設沿東隴海產業帶”和“加快蘇北振興”等戰略,蘇北農村經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蘇北與蘇南農民收入的差距依然存在。
參考文獻:
[1]門可佩,朱淑丹.基于灰色關聯度的江蘇省農村居民人均純
收入分析[J].安徽農業科學,2011,39(21):13230-13232.
[2]杜華章.江蘇省農村居民收入結構及影響因素實證研究[J].
河南科技學院學報,2011(5):10-16.
[3]孟德友,陸玉麒.基于縣域單元的江蘇省農民收入區域格
局時空演變[J].經濟地理,2012,32(11):105-112.
[4]趙文亮,王春濤,陳文峰,孟德友,范況生.基于縣域單元的
河南農民收入區域分異時空格局[J].地域研究與開發,
2012,8(4):56-60.
[5]杜俊,李裕瑞.安徽省農民收入地域格局變化及其驅動力分
析[J].農業系統科學與綜合研究,2009,25(10):95-99.
[6]杜姍姍,蔡建明.河南省縣域農民純收入增長差異及其演進
格局分析[J].經濟地理,2010,309(12):2091-2096.
[7]劉文軍,吳俐民.云南省縣域農民人均純收入時空格局分
析[J].科學技術與工程,2011,11(21):5128-5132.
[8]劉玉,劉彥隨.環渤海地區農村居民純收入空間分異研究
[J].經濟地理,2010,30(6):992-997.
[9]李春平,劉閣.山東省際鄰邊縣域農民人均純收入時空演變
分析[J].江蘇農業科學,2010(3):480-482.
[10]賀振,賀俊平.農民純收入地域差異時空特征分析[J].經
濟問題,2011(10):92-94.
[11]葉長盛,黃建軍.江西省縣域農村居民純收入空間差異研
究[J].水土保持研究,2011,18(3):153-157.
[12]馬明金,張睿.基于GIS的陜西省農民收入空間分異研究[J].
測繪地理信息,2012,37(6):48-51.
[13]張海軍,蔣國富.河南省縣域農民人均純收入時空演變分
析[J].地理與地理信息科學,2009,25(4):109-112.
[14]樊新生,李小建.欠發達地區農戶收入的地理影響分析[J].
中國農村經濟,2008(3):16-23.
[15]歐向軍,陳修穎.改革開放以來江蘇省區域經濟差異成因
分析[J].經濟地理,2004,24(3):338-342.
(責任編輯:石大立)
(二)討論
江蘇省農民收入表現出明顯的南北差異,農民收入水平呈現出由南向北遞減的趨勢,地域分異現象比較明顯。本文認為造成這種空間差異的原因主要有四點:1.區位條件。地理區位是影響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非農就業的一個重要因素,經濟區位、地理鄰近性等因素對農業生產及農戶收入的作用越來越大[14]。蘇南位于我國綜合實力最強的長江三角洲經濟區的中心,受中心城市上海的影響,農民大多從事非農就業,農民收入中工資性收入所占比重較大。蘇中位于長江三角洲經濟區的邊緣,距離中心城市上海的距離較遠,缺乏具有強大輻射作用的中心城市,區位優勢不明顯。蘇北位于我國經濟較為落后的中部地區,距我國經濟發達地區相對較遠,受經濟中心的吸引和輻射作用比較弱,區位優勢較差,農民大多從事農業活動,工資性收入比較少。2.城鎮化水平。20世紀80年代初,江蘇省提出“以城市為中心,小城鎮為紐帶,以農業為基礎”的發展思路,有計劃的發展小城鎮。蘇南以此為契機,大力發展鄉鎮企業,極大地推動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創立了聞名遐邇的蘇南模式,農民收入大幅提升。以2011年為例,蘇南的城鎮化率為71.9%,而蘇中和蘇北的城鎮化率分別為57.5%和53.3%。3.產業結構。以2011年為例,蘇南地區的三次產業比例為:2.3:52.9:44.8,蘇中地區的三次產業比例為:1:54.3:38.6,蘇北地區的三次產業比例為12.9:47.9:39.2。蘇南地區的第二、三產業比例明顯高于蘇中和蘇北地區,非農產業對農村經濟的貢獻較大,這是蘇南農村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4.政策影響。1984年,江蘇省提出“積極提高蘇南,加快發展蘇北”的不均衡發展方針,使蘇南的地方政府與企業擁有更多的優先發展權[15],大力發展鄉鎮企業,蘇南農村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而蘇中和蘇北經濟發展緩慢,導致南北差距擴大。為了縮小南北差距,江蘇省又提出“區域共同發展”、“蘇北大發展”、“建設沿東隴海產業帶”和“加快蘇北振興”等戰略,蘇北農村經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蘇北與蘇南農民收入的差距依然存在。
參考文獻:
[1]門可佩,朱淑丹.基于灰色關聯度的江蘇省農村居民人均純
收入分析[J].安徽農業科學,2011,39(21):13230-13232.
[2]杜華章.江蘇省農村居民收入結構及影響因素實證研究[J].
河南科技學院學報,2011(5):10-16.
[3]孟德友,陸玉麒.基于縣域單元的江蘇省農民收入區域格
局時空演變[J].經濟地理,2012,32(11):105-112.
[4]趙文亮,王春濤,陳文峰,孟德友,范況生.基于縣域單元的
河南農民收入區域分異時空格局[J].地域研究與開發,
2012,8(4):56-60.
[5]杜俊,李裕瑞.安徽省農民收入地域格局變化及其驅動力分
析[J].農業系統科學與綜合研究,2009,25(10):95-99.
[6]杜姍姍,蔡建明.河南省縣域農民純收入增長差異及其演進
格局分析[J].經濟地理,2010,309(12):2091-2096.
[7]劉文軍,吳俐民.云南省縣域農民人均純收入時空格局分
析[J].科學技術與工程,2011,11(21):5128-5132.
[8]劉玉,劉彥隨.環渤海地區農村居民純收入空間分異研究
[J].經濟地理,2010,30(6):992-997.
[9]李春平,劉閣.山東省際鄰邊縣域農民人均純收入時空演變
分析[J].江蘇農業科學,2010(3):480-482.
[10]賀振,賀俊平.農民純收入地域差異時空特征分析[J].經
濟問題,2011(10):92-94.
[11]葉長盛,黃建軍.江西省縣域農村居民純收入空間差異研
究[J].水土保持研究,2011,18(3):153-157.
[12]馬明金,張睿.基于GIS的陜西省農民收入空間分異研究[J].
測繪地理信息,2012,37(6):48-51.
[13]張海軍,蔣國富.河南省縣域農民人均純收入時空演變分
析[J].地理與地理信息科學,2009,25(4):109-112.
[14]樊新生,李小建.欠發達地區農戶收入的地理影響分析[J].
中國農村經濟,2008(3):16-23.
[15]歐向軍,陳修穎.改革開放以來江蘇省區域經濟差異成因
分析[J].經濟地理,2004,24(3):338-342.
(責任編輯:石大立)
(二)討論
江蘇省農民收入表現出明顯的南北差異,農民收入水平呈現出由南向北遞減的趨勢,地域分異現象比較明顯。本文認為造成這種空間差異的原因主要有四點:1.區位條件。地理區位是影響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非農就業的一個重要因素,經濟區位、地理鄰近性等因素對農業生產及農戶收入的作用越來越大[14]。蘇南位于我國綜合實力最強的長江三角洲經濟區的中心,受中心城市上海的影響,農民大多從事非農就業,農民收入中工資性收入所占比重較大。蘇中位于長江三角洲經濟區的邊緣,距離中心城市上海的距離較遠,缺乏具有強大輻射作用的中心城市,區位優勢不明顯。蘇北位于我國經濟較為落后的中部地區,距我國經濟發達地區相對較遠,受經濟中心的吸引和輻射作用比較弱,區位優勢較差,農民大多從事農業活動,工資性收入比較少。2.城鎮化水平。20世紀80年代初,江蘇省提出“以城市為中心,小城鎮為紐帶,以農業為基礎”的發展思路,有計劃的發展小城鎮。蘇南以此為契機,大力發展鄉鎮企業,極大地推動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創立了聞名遐邇的蘇南模式,農民收入大幅提升。以2011年為例,蘇南的城鎮化率為71.9%,而蘇中和蘇北的城鎮化率分別為57.5%和53.3%。3.產業結構。以2011年為例,蘇南地區的三次產業比例為:2.3:52.9:44.8,蘇中地區的三次產業比例為:1:54.3:38.6,蘇北地區的三次產業比例為12.9:47.9:39.2。蘇南地區的第二、三產業比例明顯高于蘇中和蘇北地區,非農產業對農村經濟的貢獻較大,這是蘇南農村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4.政策影響。1984年,江蘇省提出“積極提高蘇南,加快發展蘇北”的不均衡發展方針,使蘇南的地方政府與企業擁有更多的優先發展權[15],大力發展鄉鎮企業,蘇南農村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而蘇中和蘇北經濟發展緩慢,導致南北差距擴大。為了縮小南北差距,江蘇省又提出“區域共同發展”、“蘇北大發展”、“建設沿東隴海產業帶”和“加快蘇北振興”等戰略,蘇北農村經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蘇北與蘇南農民收入的差距依然存在。
參考文獻:
[1]門可佩,朱淑丹.基于灰色關聯度的江蘇省農村居民人均純
收入分析[J].安徽農業科學,2011,39(21):13230-13232.
[2]杜華章.江蘇省農村居民收入結構及影響因素實證研究[J].
河南科技學院學報,2011(5):10-16.
[3]孟德友,陸玉麒.基于縣域單元的江蘇省農民收入區域格
局時空演變[J].經濟地理,2012,32(11):105-112.
[4]趙文亮,王春濤,陳文峰,孟德友,范況生.基于縣域單元的
河南農民收入區域分異時空格局[J].地域研究與開發,
2012,8(4):56-60.
[5]杜俊,李裕瑞.安徽省農民收入地域格局變化及其驅動力分
析[J].農業系統科學與綜合研究,2009,25(10):95-99.
[6]杜姍姍,蔡建明.河南省縣域農民純收入增長差異及其演進
格局分析[J].經濟地理,2010,309(12):2091-2096.
[7]劉文軍,吳俐民.云南省縣域農民人均純收入時空格局分
析[J].科學技術與工程,2011,11(21):5128-5132.
[8]劉玉,劉彥隨.環渤海地區農村居民純收入空間分異研究
[J].經濟地理,2010,30(6):992-997.
[9]李春平,劉閣.山東省際鄰邊縣域農民人均純收入時空演變
分析[J].江蘇農業科學,2010(3):480-482.
[10]賀振,賀俊平.農民純收入地域差異時空特征分析[J].經
濟問題,2011(10):92-94.
[11]葉長盛,黃建軍.江西省縣域農村居民純收入空間差異研
究[J].水土保持研究,2011,18(3):153-157.
[12]馬明金,張睿.基于GIS的陜西省農民收入空間分異研究[J].
測繪地理信息,2012,37(6):48-51.
[13]張海軍,蔣國富.河南省縣域農民人均純收入時空演變分
析[J].地理與地理信息科學,2009,25(4):109-112.
[14]樊新生,李小建.欠發達地區農戶收入的地理影響分析[J].
中國農村經濟,2008(3):16-23.
[15]歐向軍,陳修穎.改革開放以來江蘇省區域經濟差異成因
分析[J].經濟地理,2004,24(3):338-342.
(責任編輯:石大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