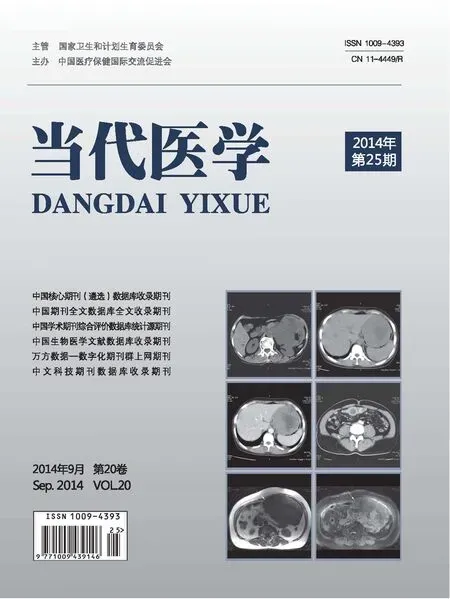副腫瘤性天皰瘡誤診為增殖型天皰瘡1例
宋海禎 陳華全 黃鶯
副腫瘤性天皰瘡誤診為增殖型天皰瘡1例
宋海禎 陳華全 黃鶯
目的 報告1例副腫瘤性天皰瘡。男性患者,22歲。因“口腔反復出現水皰、潰瘍伴疼痛半年,起贅生物半月余”就診。專科檢查:口腔內見多處綠豆至蠶豆大小的淡紅色糜爛面;口腔內右下唇部見數個突出于黏膜表面的贅生物,基底暗紅,頂部色白,質軟。下嘴唇可見糜爛結痂。方法 胸部增強CT檢查示:左側腋窩多個大小不等卵圓形腫塊,考慮系神經類腫瘤可能。外科手術切除一5cm×4cm×3cm大質軟完整包塊,組織病理檢查示:成熟的淋巴細胞增生,間質纖維及血管增生,部分小血管透明變性,不排除巨大淋巴結增殖癥。結合臨床表現,診斷為副腫瘤性天皰瘡。術后應用糖皮質激素治療后皮損好轉。結果 因本病例皮損發于口腔,早期結合病理檢查,僅診斷為增殖型天皰瘡。后患者病情反復,再次行體格檢查后切除腋下腫塊,組織病理切片明確診斷,臨床治愈。結論 反復體格檢查、早期診斷、早期治療才是治療本病的關鍵,值得臨床借鑒。
天皰瘡;副腫瘤性天皰瘡;誤診;增值型天皰瘡
副腫瘤性天皰瘡(paraneoplastic pemphigus,PNP)是一種伴發腫瘤的自身免疫性皮膚粘膜疾病,國內近年對本病的報道已有20余例。現將德陽市人民醫院皮膚科收治的1例報道如下。
1 臨床病例
1.1 一般資料 男性患者,22歲,口腔反復出現水皰、潰瘍伴疼痛半年,起贅生物半月余。患者半年前口腔多處出現綠豆至蠶豆大小水皰,說話及進食時水皰易潰破,潰破后出現淡紅色糜爛面,疼痛明顯。當地診所按“口腔潰瘍”給以中藥及輸液治療(具體不詳),未見好轉。2010年12月患者至四川省華西醫院就診,行病理活檢診斷為“天皰瘡”,給予強的松片(50mg/d×7d)口服,癥狀緩解不明顯。后于本科住院治療,好轉后繼續口服強的松,但口腔癥狀始終未痊愈。半月前上述癥狀再次加重,并于右下唇黏膜部位出現贅生物,質較軟,易破潰。遂于2011年3月8日再次來診,本科室以“增殖型天皰瘡?”收住入院。患者既往有青霉素過敏史。
1.2 體檢 一般情況可,生命體征平穩。詳細查體后發現左側腋窩多個大小不等卵圓形腫塊,質軟,活動度好,無觸痛。專科檢查:口腔內見多處綠豆至蠶豆大小的淡紅色糜爛面;口腔內右下唇部見數個突出于黏膜表面的贅生物,基底暗紅,頂部色白,質軟。下嘴唇可見糜爛結痂(見圖1)。
1.3 實驗室檢查 血常規:NEUT%(中性粒細胞百分比)80.6%(50%~75%),LYMPH% (淋巴細胞百分比)14.0%(20%~42%)。免疫全套示:IGE 223IU/mL(5~165 IU/mL)。生化、大小便常規未見明顯異常,感染性疾病篩查及唇部贅生物脫落細胞檢測皆為陰性。胸部包塊彩超示:左側腋前線皮下肌層深面多發低回聲團塊(部分內伴鈣化);CT平掃及增強報告示:左側腋窩多個大小不等卵圓形腫塊,考慮系神經類腫瘤可能。
1.4 組織病理學檢查 入院前華西醫院口腔黏膜科免疫病理(DIF)示:復層鱗狀細胞間IgG(+),C3(+),IgG(-)。
1.5 診斷 (1)增殖型天皰瘡?(2)炎性肉芽腫?(3)左側腋下包塊性質待定。
1.6 治療:入院后,請口腔科在局麻下行“右下唇贅生物切除術”,活檢報告(見圖2)。本科給予甲強龍(甲潑尼松龍注射液),40mg/d,靜脈滴注,2d后予甲強龍靜脈沖擊療法1次(具體為:第1d80mg,第2天60mg,第3d40mg,第4d恢復至沖擊前劑量)。治療10d病情基本穩定,皮損較前緩解。經相關科室會診后,轉至普外科行“左側腋下包塊切除術”,術中切除一5cm×4cm×3cm大小、質軟、完整包塊,組織病理報告(見圖3)。修正診斷為:(1)副腫瘤性天皰瘡;(2)唇腺囊腫。治療2周后,臨床治愈出院。隨訪1年未復發。

圖1 下嘴唇可見糜爛結痂

圖2 下唇部組織活檢

圖3 左側腋下包塊活檢
2 討論
2.1 副腫瘤性天皰瘡(PNP)是一類自身免疫性的棘層松解性疾病,由Anhalt等[1]在1990年首次報道。該病是一種伴發隱匿的良/惡性腫瘤和反復發作的皮膚黏膜損害為特點的自身免疫性大皰性皮膚病[2],好發于中青年,男女無明顯差異,以粘膜損害最為突出,特別是頑固性的口唇及口腔粘膜的糜爛和潰瘍[3]。而難治的嚴重口腔損害正是PNP的特征性標志,候麥花等[4]回顧性研究7例PNP臨床資料,發現其中有5例均以口腔皮損為最早期主訴,且較尋常型天皰瘡和多形紅斑更為廣泛。
本病誤診率較高,符青梅[5]等統計1999年1月~2008年3月中國生物醫學文獻數據庫中24例PNP,其中22例發生誤診,文獻報道誤診率為91.7%。如不及時治療,20%~30%的患者可累及呼吸道,最終死于呼吸衰竭[6]。
本病雖然預后較差,但手術切除腫瘤后,絕大多數患者在術后6~l8個月皮損改善或痊愈,90%患者循環抗體滴度明顯下降[7]。在治療方面,仍應系統使用糖皮質激素,且應遵循長期以來朱學駿教授提出的“早期應用,足量控制,合理減量,小量維持“的應用原則[8],必要時聯合免疫球蛋白或免疫抑制劑。
本病例早期伴有右下唇部黏膜表面贅生物,被誤診為增殖型天皰瘡。后查體發現左側腋窩卵圓形腫塊,切除腫瘤后,癥狀很快得以控制。符合上述特征。
2.2 結合本次病例,本研究認識到臨床工作中,應嚴格遵守操作規范,對治療療效欠佳、反復發作者,應反復詳細進行體格檢查,尤其對于腋窩、腹股溝等皺褶部位淋巴結不容忽視。對頑固的難治性皮膚黏膜損害時要考慮PNP的可能,以早期發現潛在的腫瘤,早期治療,改善疾病預后[9]。
[1] Anhalt GJ,Kin SC,Stanley JR.et al.Paraneoplastic pemphigu.An autoimmune mucocutaneous disease associated with neoplasia[J].N Engl Med.1990,323(25):1729-1735.
[2] 高春芳,房婕,郭志麗,等.副腫瘤性天皰瘡1例[J].中國中西醫結合皮膚性病學雜志,2004,3(4):242.
[3] 鄭海濤,張振斌,胡金晨,等.一例Castleman病合并副腫瘤性天皰瘡[J].中華內分泌外科雜志,2012,6(3):212-213.
[4] 候麥花,朱豐.7例副腫瘤性天皰瘡臨床分析[J].中國中西醫結合皮膚性病學雜志,2013,12(6):361.
[5] 符青梅,萬學峰,沈大為.國內24例副腫瘤性天皰瘡臨床資料分析[J].臨床誤診誤治,2009,6(6):73.
[6] 傅熙博,付慶才.Castleman病伴副腫瘤性天皰瘡一例[J].中國醫師進修雜志,2009,32(2):73.
[7] 張紅,袁曉英.副腫瘤性天皰瘡1例[J].軍醫進修學院學報,2008,29 (1):62.
[8] 林文生,楊文林.僅累及粘膜的副腫瘤性天皰瘡1例[J].中國皮膚性病學雜志,2010,24(12):1168.
[9] 武劍,陳志偉.Castleman病伴副腫瘤性天皰瘡誤診為白塞病1例分析[J].中國誤診學雜志,2011,11(18):4428.
10.3969/j.issn.1009-4393.2014.25.044
四川 618000 四川省德陽市人民醫院皮膚科 (宋海禎 陳華全) 610072 成都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皮膚科 (黃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