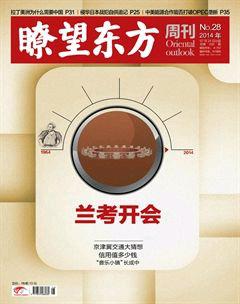“音樂小鎮”長成中
周范才+周小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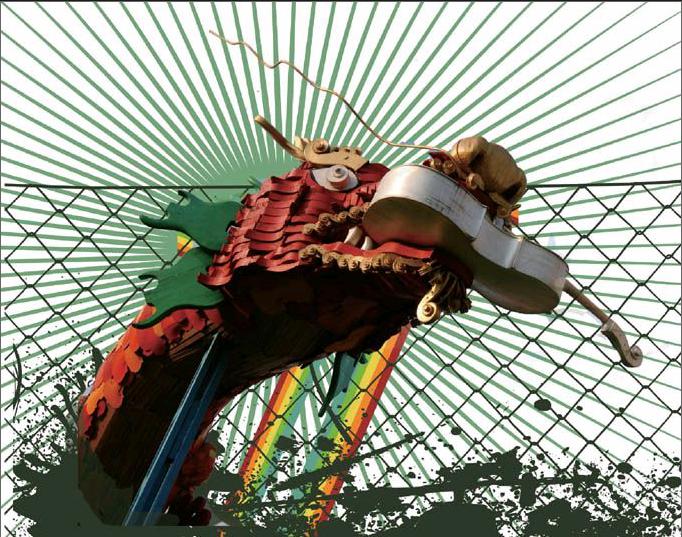
清晨6點,寧靜的周窩村漸漸醒來。一頭銀發的張振峰老人把音響從工作室搬到戶外,擺上樂譜,試了試琴弦,即興用小提琴拉了一曲《春節序曲》。
穿著拖鞋、搖著蒲扇的大爺大媽從家中踱步出門,散步到張振峰的工作室外,在馬路對面的臺階上席地而坐。
這些樸實的村民堪稱張振峰的“知音”,他們中不少人是村里管弦樂隊的成員,或者曾親手在毗鄰的金音樂器集團生產過薩克斯、單簧管。即興用小提琴、薩克斯演奏一曲,對很多農忙時候仍每天扛著鋤頭的周窩村民來說并不陌生。
64歲的張振峰是個文化人。幾年前,他從河北武強縣文化館退休,在周窩村的一個提琴工作室當了一名“提琴體驗師”,每天的工作是為慕名而來的游客演奏、展示提琴,閑暇時,常和村民一起拉琴唱歌。
“當其他村里的人在打麻將、罵大街的時候,我們周窩人在拉小提琴唱歌。”讓張振峰津津樂道的周窩,有一個更為文藝的名字:音樂小鎮。
音樂,是這里唯一的標志
這是位于河北省武強縣的一個普通北方村落。最明顯的特點是,周窩的民居均是40多年前統一規劃建設的,巷陌井然,馬路兩旁是一字排開碗口粗的槐樹,地面均用紅磚鋪砌。經過最近幾年的整修,這里顯得整飭而靜謐。
在2011年之前,周窩和大多數中國北方村莊一樣籍籍無名,甚至一片殘破。如今,這個并不依山傍水的村子在短短幾年內有了北方版“周莊”的味道:沿街墻上點綴著各種前衛涂鴉,歐式路燈一字排開,與音樂、樂器相關的符號被點綴在各個角落,也飄蕩在每一寸空氣里。
音樂是全村最亮眼的符號。村口有用廢吉他和小提琴面板拼接成的椅子;村里沿街的一面面墻壁上都是各種音樂主題壁畫,不時還能看到列儂等國外音樂人的大幅頭像,連路燈、路牌也都設計成了小提琴、吉他等各種樂器的式樣。
周窩乃至整個武強與音樂并無淵源,故事是從一個叫陳學孔的武強人開始的。
1989年,只有小學文化的陳學孔“下海”在天津一家樂器廠當鉗工。之前,他從未接觸過樂器,“根本談不上喜歡,就是為了生存。”如今已是金音樂器集團總經理的陳學孔對《瞭望東方周刊》說,“到現在我也不會玩什么樂器,就是比別人多一點了解而已。”
逐漸摸索到生產樂器的門道后,陳學孔回到老家武強和當時做水管生意的周國芳合伙,開了一家通達樂器廠。廠子只有21名工人,幾乎清一色是附近村民。
最初,通達樂器廠只能生產薩克斯、單簧管等管弦樂器配件。即便如此,這對陳學孔來說也是天大的挑戰。摸了一輩子鋤頭的村民只能依葫蘆畫瓢,自己摸索。陳學孔從外地樂器廠家請來技術人員、找來圖紙,對村民進行培訓。
1995年,陳學孔結識了一位經營樂器生產企業的美籍華人,二人隨后的合作為樂器廠帶來了12萬美元的注資和廣闊的海外市場。
通達樂器更名為“金音樂器”。24年過去,它已經成為中國樂器行業的“老大”,旗下擁有8家子公司,產品涵蓋了木管、銅管、提琴、吉他四大系列100多種規格,成為世界產量第二、中國第一的西管樂器生產企業,年產值達4億元,產品出口到英國、荷蘭、法國、意大利、日本、韓國等30多個國家。
與音樂共生
隨著金音樂器的異軍突起,武強迅速集聚起數量眾多的樂器生產企業。毗鄰縣城的武強經濟技術開發區打出“河北省十大文化產業集聚區”的宣傳標語,正著力打造中國樂器生產基地。
2010年,陳學孔牽頭,將金音曾經的合作伙伴、歐洲樂器行業領軍企業德國蓋瓦公司從天津請到了武強。陳學孔說:“它一過來,供應商、物流、銷售就全得過來,不來就會被淘汰。”
2010年,大量國內外樂器產業人流、物流、資金流的加速聚集,讓美國塞西里歐、德國波蘭斯勒、浙江三弟、武漢艾力卡等國內外知名樂器生產、分銷企業迅速匯集到了占地3平方公里的武強國際樂器產業園,集產品研發、樂器生產和物流倉儲銷售為一體的樂器產業鏈條被打通。
“武強原來主要生產管弦樂器,自從蓋瓦公司入駐以后,鍵盤、鋼琴、打擊樂的生產都起來了。”武強經濟開發區管理委員會副主任于少峰向本刊介紹,如今武強僅樂器制造及相關配套企業已發展到50余家,年增加值2.76億元。
得益于中國經濟改革的推進和世界樂器行業戰略轉移的機遇,過去十年被認為是中國樂器行業的高速發展期。
即便已經成為“中國第一”,陳學孔也承認樂器生產并不突出的產業附加值。“2013年,全國樂器行業的產值138億美元左右,但這大概也就相當于海爾一個車間一年的產值,和人家比,我們的貢獻太小了。”
作為中國樂器協會常務副理事長,這也曾是困擾陳學孔多年的問題。在很多人看來,樂器生產行業屬于制造業、輕工業,與文化產業不沾邊。陳學孔說,中國樂器協會曾向國務院申報文化產業政策項目,商務部、文化部等幾個部委召集他們開會時,與會部委領導也對樂器生產是否應歸入文化產業有分歧。
陳學孔不以為然:“到底什么東西能代表中國文化?是不是得看琴棋書畫?那琴是什么?幾千年都承認的問題,還需要我們開會來討論?”
不過,他也清楚,如果僅是樂器生產離文化產業確實還很遠。
好在隨著金音過去20多年的輻射帶動,武強濃郁的音樂氛圍逐漸興起。不少在金音集團上班的工人,在潛移默化中也學會了吹小號、拉提琴。夏天的傍晚,從工廠下工后,他們還會自發聚在一起練習。據武強縣委宣傳部副部長劉愷兵介紹,武強全縣已有7支農民西洋樂隊,每支樂隊成員多達60余名。
不能只有樂器,沒有音樂
只有樂器、沒有音樂的文化產業是缺少靈魂的。這是周窩音樂小鎮運營方、北京璐德文化公司衡水項目負責人董玉戈的看法。
2009年,國務院發布《文化產業振興規劃》,將文化產業發展提升到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的重要位置。武強縣躍躍欲試。2010年,由于和金音集團的多年合作,陳學孔牽頭請董玉戈供職的北京璐德文化公司為武強做產業規劃。endprint
璐德公司是中國音協吉他學會旗下一家專注于在全國舉辦音樂節和音樂培訓學校的文化公司。2011年,董玉戈到武強開辦璐德國際藝術學校,定位于培養高端音樂人才和師資力量。
董玉戈也是來了武強以后才聽說周窩的。“一開始金音找我們來,只是想助推企業發展。”他說,樂器產業的附加值和品牌價值,必須依靠玩樂器、愛音樂的人來體現。璐德公司建議將周窩村打造成手工樂器批發、零售和旅游體驗集散地,把音樂人和消費者吸引過來。
2011年,武強縣政府和璐德公司達成合作協議,將周窩委托給璐德公司運營,開始對周窩村進行規劃建設和整體開發,打造“音樂家創作創意、愛好者享受參與、旅游者休閑購物,具有國際水準、獨具地域特色的音樂小鎮”。
如今,3年過去,周窩已累計完成投資8000多萬元,在保持既有格局的前提下,硬化路面,整修供排水、供暖等設施,將民居改造成音樂會館、樂器工作坊、音樂家紀念館,以及客棧、茶餐廳、咖啡館等特色院落。
據董玉戈介紹,音樂小鎮的整體包裝和運營完全按市場模式操作,武強縣所在的河北衡水市也給予了強力支持,指令全市每個縣市在小鎮認領改造農家小院。
迄今為止,依托音樂小鎮已成功舉行了武強縣麥田音樂節、中韓國際鄉村藝術節、每年一屆的中國吉他文化節等音樂節會,努力為“周窩音樂小鎮”積聚人氣。
音樂家還未常駐
根據董玉戈的規劃,周窩音樂小鎮應該向畫家村宋莊的模式靠攏:首先搭建起比較完善的配套設施和硬件、平臺,再把音樂人、藝術家和消費者甚至各種商業投資吸引過來。
鋼琴老師韓強也許能算作是第一批被吸引來的人之一。今年40多歲的韓強,本是距離周窩村四五里地的董莊村人,曾學習鋼琴,1995年跟著河北保定的歌舞團一路北上,來到鴨綠江畔的丹東,輾轉于各個夜總會,為演出伴奏。多年后,夜總會不再紅火,酒吧興盛,韓強又和樂隊一起去了天津的酒吧。
2010年,一生都在“走穴”的韓強回到老家武強。他這樣有音樂基礎的本地人正是璐德公司希望物色的人才,雙方簽訂合同,韓強獲得了一間周窩音樂小鎮展銷樂器的門市,負責為前來參觀游玩的顧客演奏、推銷樂器。
游客沒有想象中那么多,韓強招收幾個本地學生,教授鋼琴、吉他等樂器。每個月,他能從璐德領到2000多元工資,趕上附近的紅白喜事,還經常和村里的樂隊應邀演出。
與韓強不同,四川人彭科飛是常駐周窩音樂小鎮的外來戶。20多年前,彭科飛在廣州學做吉他。2006年,他曾應邀來過武強為金音集團研發新產品。在武強開始打造音樂小鎮后,當陳學孔在一次樂器展銷會上遇到彭科飛時,便向他發出了邀約。
2012年,彭科飛來到武強,開辦了一家手工吉他作坊,為吉他愛好者提供個性化吉他定制服務,如今已在圈內小有名氣。他對自己的手藝很有信心,“專業吉他玩家對吉他的手感、材料和聲音都有自己的要求,這都是一般琴行里賣的琴沒法滿足的。”
在周窩音樂小鎮,類似的樂器工作坊、體驗館、創作館很多,但顯然還未形成足夠的影響力。“到現在還沒有形成藝術家、音樂家常駐的態勢。”董玉戈承認,目前周窩音樂小鎮的基礎設施仍很不完善,環境和氛圍的打造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和近年烏鎮因舉辦“烏鎮戲劇節”而迅速成為國內知名的戲劇藝術聚集地不同,周窩遠不具備烏鎮的自然條件。如何吸引國內知名音樂人在周窩落戶,是擺在武強地方政府、陳學孔、董玉戈等人面前的巨大難題。
“麗江、平遙都經歷過了超過20年的培育期,周窩沒有獨特的自然風光,只能靠人來帶動。”據董玉戈介紹,武強已規劃更高接待能力的度假村項目,以及即將揭幕的軍歌博物館等大型工程,希冀通過提供和北京水平相當但使用成本更低的錄音棚、演播廳的方式吸引國內音樂人入駐。
今年8月,已經是連續第四年舉辦的中國吉他音樂節將在周窩音樂小鎮開幕,這個音樂節每年均為周窩帶來數千人流。只是,音樂節閉幕后,更多時間音樂小鎮僅是周窩村民們自娛自樂的天堂。
上午10點,張振峰送走學琴的小男孩,拎著提琴又來到提琴館門口,和朋友合奏了一曲《茉莉花》。悠揚的樂聲在這個尋常的夏日上午縈繞在村頭巷尾,一位騎著三輪車路過的村婦停了下來,和一旁依然坐在臺階上搖著蒲扇的白發老人認真地聽著,一曲終了,沒人散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