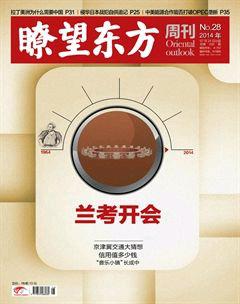楊先讓:不講理的藝術
渠魁+沈杰群

1993年,《黃河十四走》在臺灣出版,作者楊先讓把書送給了老朋友黃永玉。
翻開書后,黃永玉盛贊“黃河十四走”是“對千秋萬載后人有深遠益處影響的東西”。認為該書“點明了研究民間藝術的一個方向,一個方法。是一個鐵打的、無限遠大的可能性”。
黃永玉當年對跑來跑去的楊先讓也不甚理解,曾經對他說:“總在別人地里跑,自己的地都荒了。”黃永玉的關心更像是善意提醒,但是當他看到《黃河十四走》之后,立即表示要為楊先讓寫文章。
這文章便是《天末懷先讓》。后來黃永玉把這篇文章收在了《比我老的老頭》這本書中,以表示他對楊先讓——這個比他年輕幾歲的老頭的敬意。
“刀刀都充滿著感情”
楊先讓的藝術之路似乎充滿了偶然。
他在中央美術學院(當時叫國立北平藝專)讀書時學的是油畫。1952年畢業后分配到人民美術出版社工作,當時鄒雅、力群、古元等優秀的版畫家都在那里,這為楊先讓學習版畫提供了天然的環境,他第一塊用于版畫創作的板子就是鄒雅送的。
楊先讓很快掌握了版畫語言。第一張版畫作品《出圈》就獲得了成功。這幅農村題材的現實主義作品,獲得了1957年的全國青年美術作品獎。
依靠本能的藝術沖動以及敏感于時代的震撼,他創作了許多版畫作品。比如1975年,他感動于石油隊伍會師大慶草原,只用了10天就完成了有數百人物造型,水印套色、恢弘大氣的木刻《會師大慶》。
“我當時多感動啊,刀刀都充滿著感情。”現已耄耋之年的楊先讓聲調突然提到很高,“還有,我為什么要刻焦裕祿?因為我當時感動于這樣一個人物。我最近又刻梁漱溟,為什么?因為他是中國文人的代表,他在特殊的環境下沒有扭曲自己的性格,太可愛了,太難得了!”
2008年,楊先讓曾對西方媒體說:“藝術家受時代約束是難免的,但我無怨無悔。”他又對本刊記者重申了這句話。
轉向民間
選擇版畫創作是一次“偶然”,轉到民間藝術同樣是“偶然”。
黃永玉曾經說近百年來像“張光宇、張正宇、張仃、郁風、廖冰兄這些前輩老大哥為中國民間藝術實踐奮斗、呼號,由于勢單力薄成不了氣候”,而他如此評價楊先讓的《黃河十四走》:“這一走,就好像當年梁思成、林徽因為了傳統建筑的那一走,羅振玉甲骨文的那一走,葉恭綽龍門的那一走。”
楊先讓說自己在“走”之前,對民間藝術并沒有一個清晰的概念,雖然這個時候楊先讓已經在“年畫、連環畫系”(民間美術系前身)呆了有6年。
“年畫、連環畫系”是1980年時任中央美院院長江豐提議建立的,其時已回到母校版畫系任教的楊先讓對年畫、連環畫這兩個專業并不喜歡,但在江豐的勸說下,他同意組建并擔任這個系的教學工作。
楊先讓在這個崗位上工作了三年,常常要為年畫、連環畫系爭取一些利益,油畫家艾中信當時笑稱:你看那個跑來跑去的就是楊先讓。
1983年,楊先讓去美國探親一年。這一年對他的影響很大,他看到美國許多藝術家對民間藝術非常重視,又從畢加索對非洲民間木雕的學習吸收中受到啟發,認識到“每一件中國古老的民間美術作品,稍加變化即是一幅充滿現代觀念的藝術品,既摩登又有歷史內涵。”
但中國的民間藝術太博大深厚,楊先讓感到年畫、連環畫只是民間藝術海洋中的一滴,就有了改年畫、連環畫系為民間美術系的想法。
接下來的日子,常常出現楊先讓游說領導改建民間美術系的情景,楊先讓把這個過程稱之為“如癡如醉”。很多人并不理解他的設想,有領導就認為“美術學院怎么能培養民間藝人?”
終于,民間美術系在改建中起步了。楊先讓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天天喊民間藝術重要,可是熱情代替不了知識,他并不知道民間藝術到底有些什么。他萌生了走向民間采訪與考察的強烈愿望。
黃河十四走
黃河十四走,其實是十五走。
從1986年春節至1989年9月。四年間,楊先讓帶著包括教師、學生、攝影師、錄像隊的考察隊,十五次出入黃河流域考察民間藝術,足跡遍及青海、甘肅、寧夏、陜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八個省區七個民族,100個左右的縣鎮。
楊先讓回憶,當時有個基金會支持,但錢不多。一行人扛著錄像攝影器材,揣著筆記本、介紹信以及各省聯絡人地址,在三輪車、摩托車、公交車等運輸工具轉換中行走。
他們知道,扎根于農耕時代的民間藝術正在經受現代化的強烈沖擊,很多民間藝術都隨著傳人的離去而消失。楊先讓對本刊記者說,他們常常會聽到某地有“寶貝”,撲哧撲哧地去了,尋到地方,找人,被告知,早來幾天就好了,這人前幾天死了。再問逝者的“寶貝”,已當作祭品燒了。
他提到潘京樂,一個年邁的皮影藝術家。1987年,考察隊在陜西華縣,聽說有個演皮影的,一行人便匆匆去了,不過他們事先并不了解何人在演,演什么。當鑼鼓絲弦響起,開唱,楊先讓驚呆了。
接受本刊采訪的時候,楊先讓一直試圖用動作、語言描述潘京樂的“碗碗腔”,他說雖然當時不知道這個老人在唱什么,但當這個老人在拉腔的時候,琴弦在那兒走著,老人不發一音,琴聲完全征服了時間。楊先讓后來想到用“化了”這個詞來形容。
楊先讓給這位老人錄像,回到北京后又介紹他到學校和中國美術館演出。對他來說,能做的只有這些了。而晚年的潘京樂還在為找不到再傳弟子而憂心。
15次行走黃河,考察隊累積了近千張圖片以及20余萬字的記錄文字,剪輯成了一部45分鐘的紀錄片《大河行》,又凝聚成了厚厚的一本書《黃河十四走》。
“雖然考察是蜻蜓點水式的,但是我走完了黃河,也搞通了民間藝術,明白了其中蘊含的哲學。”楊先讓對本刊記者說。
1990年,楊先讓退休了,民間美術系被縮編為民間美術研究室。提到此事楊先讓顯得有些痛心疾首。他說這也是后來移居美國的原因之一。endprint
《瞭望東方周刊》:當年為什么把考察選在黃河流域?
楊先讓:當時幸虧走的是黃河,如果走的是長江,就需要面對太復雜的民族文化樣態,很難系統地進行考察。
黃河流域包涵了中原文化、草原文化、楚漢文化、東夷和苗藏等文化,稱它為華夏民族的搖籃并不是過譽。考察黃河流域的民間藝術,很可能獲得認識和打開中國其他地區民間藝術的一把鑰匙。
《瞭望東方周刊》:你怎么理解民間藝術?
楊先讓:民間藝術的哲學絕不是什么儒、佛、道,民間藝術的哲學思想都是萬物有靈的概念和樸素的陰陽觀。尤其是在偏遠的山鄉,人們更接近天地原始的大自然,所以我們從民間藝術中看到刺繡、布枕、玩具、信物等無不表達對生命繁衍的寓意、對性愛的象征、對祖先的祭祀、對福祿吉祥的期望。
民間藝術都是為生存而進行的創造活動,與生存功利無關的純審美藝術在民間是不存在的。
世界上的民間藝術都是一個體系,造型也是一樣,都是原始的體系。創造非常自由。
《瞭望東方周刊》:中國民間藝術與西方藝術的本質區別是什么?
楊先讓:中國民間藝術是“樂感”文化,西方是“罪感”文化。
比如剪紙藝術家庫淑蘭就是“樂感”文化的代表,她在貧困的壓力下,沒有消失對美的追求與向往,以樸素善良的心地對待世界。她的作品是那樣地富態,那樣地美。直到現在看她的東西都非常感人——藝術上感人,生活上感人。
她的身上表現出一種理想,就是中國民間“樂感”文化。
《瞭望東方周刊》:怎么理解你說的“自由”,我們看到許多民間藝術都非常地相似?
楊先讓:相似是重復,重復說明了一種文化的繼承,民間美術值得重復。
中國民間藝術重要的特點之一就是把表現形式概括為一定程度的程式化,必須在藝術的規范要求之內去發揮其自由。
有一位民間剪紙高手看了美術院校師生的作品后說,“你們是講理的藝術,俺們是不講理的藝術。”這里的“不講理”就是不受固定程式的限制,有較大的主動權。民間藝人所創作的藝術形象,只要他們認為合乎情理就行,是以心靈所見取其神而保其意的。
《瞭望東方周刊》:為什么“不講理”的藝術面臨即將消失的處境?
楊先讓:民間藝術本就是自生自滅的,本就屬于“即逝的藝術”。而且我們的國家正在轉型,民俗要變,民俗一變,附著在民俗上的民間藝術必然要變。現在誰還穿虎頭鞋,誰還穿肚兜兜啊?
保留下來的,都只是旅游產品而已。至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只能盡力而為,畢竟傳統藝術失去了它所存在的空間。
《瞭望東方周刊》:有沒有把民間藝術和現代結合的嘗試?
楊先讓:我畫了幾張畫,不成功,太難了!哪能這么容易啊?1+1就等于2嗎?講一講庫淑蘭的剪紙就能吸收庫淑蘭的藝術精髓嗎?創造本身就是難的,藝術需要發酵。
楊先讓
畫家,1930年生于山東。曾任中國民間美術學會副會長, 1996年被中國版畫家學會授予“魯迅版畫獎”。上世紀90年代赴美國居住,于費城、休士頓等地多次舉辦畫展、講學等文化交流活動。2008年獲得全美文化教育基金會頒發的終身藝術獎。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