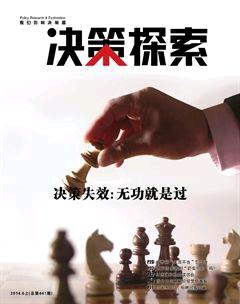“策”前多一事 “決”后少萬事
文/本刊記者++馮春久
6月5日上午7點多鐘,來自漯河市的于果要到鄭州市文化路一家省直機關辦事,車從農業路拐到文化路上,他就開始四處觀察哪里有停車場。
還沒到黃河路,他就看見一指示牌顯示,前面某單位停車場有車位100多個,心里暗自慶幸。到了門口,先是看見有個指示牌橫擋在入口處:車位已滿。后又從門衛跑出來一個保安,告訴他這里不讓外來的車停放,說自己單位的車還放不下。
于果只好繼續往前行,沒走多遠,又看見一指示牌顯示某小區停車場有車位。當他開到門口的時候,同樣吃了閉門羹。一直到了辦事的單位門口,也沒找到停車位。此時正好是上班高峰,車流不息,找個停車位真是難上加難。
于果說,一路上這么多標識顯示有車位,為什么就不讓進去停車呢?既然不讓停車,何必又要設置這種標識呢?
不獨外地人于果有這種想法,就是經常在市區開車辦事的鄭州人也不乏這種想法。從事商貿工作的張海軍說,于果看到的指示牌上還顯示有車位多少個,他則看到一個指示牌上顯示的車位數被人用膠布遮擋起來了。
其實,這是鄭州市為了減少路面停車,減少路面擁堵而采取的措施。鄭州市交通委先后公布了取消停車路段的周邊停車場和新增臨時停車場等示意圖,以方便群眾順利停車,同時還將采取一些新舉措增加停車位,包括治理挪用停車場設施,鄭州市共清理被挪用停車場27處,恢復停車位1473個;錯時開放自有停車場,據不完全統計,鄭州全市單位、社區可錯時開放和拓展停車位近8萬個。
然而,從當前的執行效果來看,并沒有達到當初的設計目標。這項政策當初實行時,為推進各單位開放停車場,河南省委常委、鄭州市委書記吳天君還專門給各單位一把手寫公開信,請各單位騰出車位向社會開放。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多單位又慢慢關閉了本單位的停車場,原來的舉措形同虛設。
從個案上來說,這就是公共治理中的決策失效或者說是決策失靈。公共決策失效是公共行政當中的一種常見現象,它雖然沒有公共決策失誤造成的后果嚴重,但輕者也會給政府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重者會引發社會矛盾。它主要是指決策雖然有效果,但沒有達到預期要求;或者說是雖然達到了預期目標,但成本很大、效益很差,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1958年我國在“大躍進”中的“大煉鋼鐵”。
在公共決策的實際操作過程中,有很多值得汲取的教訓。縱觀這些決策失效的案例,按一般規律性來說,總有一些必然的因素是導致決策失效的主要原因。有專家總結分析如下:第一,立場不夠公正。決策者在制定公共政策時,沒有自覺站在中立、公正的立場對待各種社會利益矛盾,而是自覺不自覺地帶有對矛盾一方或幾方的明顯傾向立場,就很容易導致決策喪失公正性,從而導致政策遭到利益被不公正損害方的強烈抵觸而令決策失效。第二,判斷不夠客觀。決策者在制定公共政策時,對政策執行的客觀環境、執行條件等客觀因素認識不充分,例如對某些政策對象的政策認同感或抵觸情緒認識不足,又如對政策執行所需投入的政策成本估計過低,或者對政策執行者的執行力不能客觀認知,例如過高估計了政策執行部門的基本素質等等,都很可能導致政策決策在局部脫離實際。第三,論證不夠科學。有的決策者在決策論證過程中,缺乏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維方式,不遵循事物的客觀規律,只憑經驗判斷事物、進行推理,主觀片面地進行決策,極易導致決策失效。第四,議程不夠規范。決策者未能按規定程序展開決策過程,或者決策程序本身就過于簡單或不夠科學,都會使決策過于匆忙倉促,容易導致決策失效。
如果說上述幾點屬于一般性的客觀因素,那么決策者在決策時的不夠充分民主則是決策者的主觀性因素。主要表現為決策者在決策的過程中,未能廣泛充分地聽取同該項政策相關的各方面的意見,包括直接和間接的政策對象的意見、主要執行和協同執行的有關部門的意見、雖不是該政策對象但可能會極其關注該項政策執行過程和執行結果的有關方面的意見等,僅有個別人或少數人進行主觀決策,都可能導致出臺的政策本身有誤,或者可能在政策出臺后和政策執行時遭到某一方的嚴重抵觸或反對,最終令政策執行變異甚至夭折。
無獨有偶,李亞等人也曾經在《學習時報》發文稱,現實中經常出現公共決策的制定過程及其實施效果遠未達到預期目標的情況,公共決策失效屢見不鮮,其中最常見甚至最重要的原因則是,專家參與和公共參與方面存在缺陷。
事實上,這正是如果“策”前多了專家和公眾參與這一事,就會減少“決”后很多扯皮的矛盾和問題。
文章指出,各地區、各部門的決策中,問計于專家已很常見。通常的做法有,舉辦專家座談會、論證會,成立專家咨詢委員會或針對特定問題的研究課題組等。決策者對專家參與越來越熟悉,顧忌也相對較少。但專家參與的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仍然不少,主要有以下三種。
一是專家參與的不平衡。最常見的是,決策論證時缺乏某些相關領域的專家或持與決策組織者明顯不同意見的專家。公共決策的復雜性經常超出決策者的想象,如果對此缺乏認識,決策組織者無意忽略了或故意拒絕某些方面專家的參與,決策中的疏漏就在所難免。專家參與過程中要容納持不同立場、甚至意見針鋒相對的專家,即所謂兼聽則明,看似常識,實際上能夠做到的卻不多。這不僅需要決策者的智慧和開明,還需要相應的制度來保障。
二是對專家參與缺乏有效制約和監督。近年來媒體和公眾表達了對專家的種種負面看法,貶之為“磚家”,實際上并非空穴來風。詬病最多的是專家被某一利益群體所收買,失去了公信力。其實,科學決策自然需要客觀中立的專家,但也不排除專家可以是利益群體的代言人,如是這種情況,則必須有為其他利益群體代言的專家來相互制約。專家的中立性并非核心,最關鍵的是不能有專家打著中立的幌子為某一群體代言。這就需要對專家參與予以監督,而公開性是不二法寶。決策論證中專家正式的發言和論證意見需要公開,專家座談會和論證會也應當有非專家組成員的人員列席監督,而這些舉措在現實中都明顯缺位。
三是專家越位屢見不鮮。專家的優勢在于,他們能夠在所擅長的領域利用其專業知識作出科學或技術分析。所謂專家越位,是指專家超出其專業特長,對公共決策的方案或后果進行價值判斷。例如,某地要引入大型化工項目,專家的職能是對化工排放物的危害性作出科學分析,對泄露風險的概率進行研判,但不可越俎代庖地作出能否興建化工廠的結論。是否接受建化工廠的風險,對項目的利弊權衡,完全屬于價值判斷,這只能由直接的利益相關者——當地民眾和政府來定奪。
文章還說,每一決策都要求必須有公眾參與確實不足取也不現實,但那些密切關系百姓生活、直接影響相關群體切身利益的公共決策一定要吸納利益相關者的意見。一旦決定引入公眾參與,決策者就必須有誠意,廣泛聽取并尊重所有利益相關者的意見。公眾并不“傻”,那種走過場式的“參與”、花瓶式的“參與”,不僅對民主決策毫無益處,更會出力不討好,嚴重損害政府的公信力。
而在生活中,我們也不難發現,和各級領導干部打交道,特別是涉及公眾參與的時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非常普遍的看法。出亂子,惹麻煩,是很多決策者最為顧慮的。謹慎些并沒有錯,但如果因此而過于消極,回避公眾參與并奉之為行事準則,其實并不明智。決策前少一事,往往導致決策執行中問題頻繁發生。政策出臺后,媒體的質疑和冷嘲熱諷,公眾或利益群體或明或暗的抵制、甚至對抗,往往導致政策失靈。為改變這種局面,進一步提高決策者組織駕馭公眾參與與專家參與的能力,促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一體化發展,改革公共決策體制和通過立法來保障專家與公眾有效參與,都是不可或缺的。
由此可見,決策前多一點麻煩,多一些程序,決策后定會少很多矛盾和困難,決策的效果也才能更接近于或達到決策時的良好愿望和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