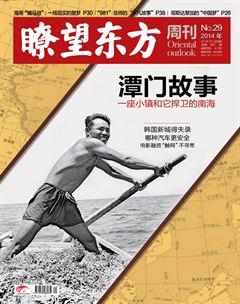韓國新城得失錄
鄭明媚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韓國中央政府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經濟發展計劃,促進許多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大量人口由此涌入城市。
為了緩解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發展導致的人口集聚膨脹,特別是人口向韓國首都首爾高度集聚的問題,韓國中央政府啟動了新城發展計劃,開始在首爾周圍建設新城。新城數量從當初的5個,發展到如今的近30個。
特別注重城市功能的選定
新城啟動的最初動機是為了解決市民的住房問題,但僅僅解決居住,也導致新城的功能不健全。新城與母城之間在上下班高峰時期的交通壓力,導致韓國的新城在后期又演變成舊城有機更新、城市邊界擴張和衛星城的建設模式。
韓國政府部門把新城建設分成兩個階段:1989年前,韓國啟動了24個新城的建設;1989年以后,啟動了11個新城的建設。
如果按照新城的功能來區分,1989年前啟動的新城主要是圍繞疏解首都首爾的城市壓力和功能;1989年以后的新城,更多的是為了實現均衡發展,以及為了戰備的考慮,疏解首爾過度集聚政治、文化、經濟中心的功能。
韓國的新城建設過程中,特別注重城市功能的選定。比如60年代,除了啟動為了解決住房問題的新城建設目標以外,結合韓國第一次制定的國土綜合開發計劃,新城與大規模產業基地共同推進。
另外,針對不同新城的地方特點,韓國的新城還推動了構建區域新的增長中心的新城發展計劃。比如,躍漢江開發的江南新城,成為對接江北老區的新的經濟中心;承接中央國家機關政府職能的世宗市;把制造業作為發展重點的昌原市;以及把旅游業當做主導產業的濟州島等。
韓國的新城建設之所以能成功,在于其有效解決了三個難題,一是往新城集聚人口;二是解決新城發展的空間;三是解決新城建設的資金難題。在這三個方面,韓國積累了一些經驗。
主城人口愿意遷往新城
為了解決首都住宅供需矛盾的激增,韓國確定了包括“盆唐、一山、坪村、中洞和山本”等5個新城的開發,都是在首爾市中心25~30公里以內,建設具有商業功能、休閑功能、便利的出行、舒適的居住功能于一體的新城。
比如90年代推動的東灘新城一期項目,是一座建造在一片農地上的嶄新城市,現在已經形成了接近20萬人的成熟市區。這里的大多數人都是從首爾搬過來的。
吸引人口到新城來的主要原因是本地物價便宜,生態環境好,社區實現了智能化的管理方式。住在這里的居民有的在本地就業,有的在首爾就業。因為在新城的建設過程中,產業集聚區的建設與開發、招商引資的工作是同步進行的。
另外,新城比較注重人性空間與生態環境的構建。比如,安養市市中心河流水系與城市景觀的結合,就充分利用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保持河流兩岸自然地形、喜水植物與有機質交換本底。住在新城的人既能享受城市的各種便利,還能享受到自然風光。
由此可見,新城具備自足性,是許多首爾市區人口往新城遷移的主要原因。
土地征收與供給計劃按照相關法律進行
韓國自上個世紀50年代起,陸續制定了關于土地開發和保護的各項法律。特別是70年代,為支持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后續的新城發展計劃,出臺了比較完善的法律體系。為了抑制投機和房產泡沫,韓國還制定了一些調控措施,比如《關于宅地所有上限的法律》、《關于開發利益回收的法律》和《土地超過得利稅法》、《關于房地產實際權利者名義登記的法律》等。
完善的法律體系作保障,使得韓國的新城開發并不是投機者而是許多剛需人口在推動,所以房地產價格相對合理。新城的發展與愿意搬遷的人口的目標基本一致,并沒有導致大量的鬼城出現。
為了完成韓國的“200萬套”住宅的計劃,韓國專門設立了以政府主導的土地住宅公社,90年代、特別是進入21世紀后,社會資金參與新城開發的比例才逐漸增多。
韓國土地公社在新城開發過程中,政府主導的開發方式主要是站在公共立場上促進規劃和開發,負責土地的一級開發和出讓,包括從所有者手中買入、開發、儲備和供給。
這種政府主導的開發模式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買賣投機行為。比如,新城開發之初,韓國中央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義征收了大量土地,為第一期的新城開發開拓了有效的空間。
多元化融資解決新城建設資金難題
關于新城發展計劃,韓國是舉全國之力來推動。初期的新城建設,中央政府提供了一些資金支持,特別是針對低收入人群的土地與住房建設,政府提供關于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持資金,以及相應的減免稅收等支持措施。
但除了少部分的中央支持以外,韓國土地住宅公社通過市場行為,采取了多元化的市場化融資手段,解決資金的難題。
比如,一級開發過程中通過預售來集資;韓國土地住宅公社通過成立土地銀行,對土地進行儲備、開發、供應和發行土地債券等形式籌集資金;二級開發過程熟地和住宅的預售籌集資金等。
從上世紀60年代起,韓國土地住宅公社開始參與新城建設,迄今為止,共參與韓國16個城市的新城開發,項目單位多達26個新城區,建成243萬戶住宅。
為了穩定住宅市場,韓國土地住宅公社還推行了國家鼓勵租賃住房的措施,儲備148萬戶住宅專門用于租賃市場。
發展之憂
韓國的新城計劃,成為韓國城市化過程中區別于歐美的典型發展模式,推動了韓國實現均衡發展的目標。但是就其新城發展而言,也有一些問題值得思考。
比如,城市發展戰略受中央政府執政理念的影響較大。中央政府對全國城市發展目標的確定,對各城市本身選擇發展定位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以慶尚南道為例,在李明博執政時期這里是全國的制造業中心,而到了樸槿惠時期,制造業中心又轉移到了其他地區,新城的發展計劃與戰略重點不得不跟著調整。
同時,規劃理念的變化也影響新城的持續發展。韓國的新城發展與城市綠帶計劃幾乎是相伴實施的,但是綠帶發展受到幾次民眾或反對派的沖擊,最終停止。規劃理念的變化,也導致城市發展計劃并不能按照預想的方案進行。
韓國許多新城,都是在建設和后期運營過程中不斷修正。比如安養市,河流水系的生態治理,從規劃時人工干預過多到回歸自然,也是在人們對理念認識提升過程中完成的。河流水系已經作了修正,但是傳統文化在建筑、街區中的體現,卻不能很好地修正。韓國許多新城的城市風貌、建筑風格基本雷同,體現不出民居的特色。
此外,就業與居住地的匹配度仍然是新城發展的一大難題。雖然規劃新城都按照理想的方式設定了產業集聚區,但在實際發展過程中,產業的進駐與新城的開發仍然步調不一致,城在前,產業在后,對于一些就業比較困難的人來說,住在新城的就業機會更少。
(作者系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發展改革試點處副處長)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