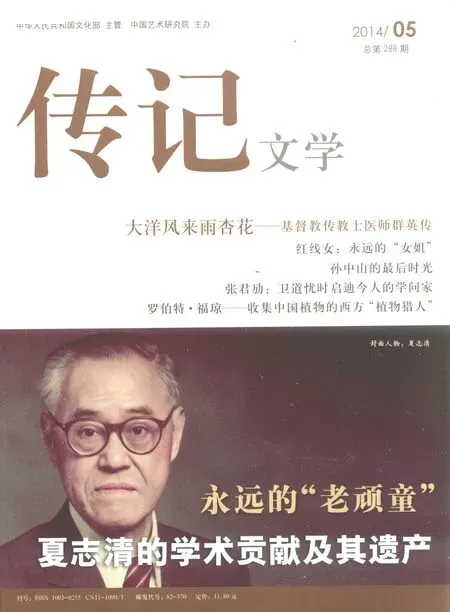衛道憂時啟迪今人的學問家
張家康
衛道憂時啟迪今人的學問家
張家康

張君勱,一位學者政治家。他的政治活動和學術生涯竟長達62年,其造詣和影響都是深遠的。可是,長期以來,他的政治主張和哲學思想,一直不為人們所理解,甚至受到譴責和批判。今天,當我們以寧靜而又客觀的心境,重新審視和觀照他時,不由地發現,他的使中國成為現代化國家的種種設想,仍有著歷史和現實的意義,他所不遺余力地“復興儒學”的倡導,更使他成為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何以又斷念政治
清貧之家的出身,使張君勱自幼便好學上進,且聰慧過人,憑著如此條件,本可以在科舉取仕的路途上博取功名,無奈家道中落,只得奉母命考入上海廣方言館。這是一所洋學堂,屬科舉時代的另類學堂,備受讀書人的鄙視,所以,它招收學生時附加“優惠”條件,即每位學生每月可領到一兩紋銀的津貼。誰曾想到,廣方言館對他的一生會造成那么大的影響,這里的英文訓練,使他后來留學日本時,能順利熟練地閱讀英文版圖書,并為以后的學術研究和國際交往奠定了語言基礎。
戊戌變法失敗后,康有為、梁啟超成為清廷通緝的要犯,可是,在廣方言館門口卻高懸著他們的照片,這一年,張君勱才12歲,看著康、梁的畫像,躁動的血脈受到莫名的激涌,從而對那個陌生的詞匯——政治,有著一種從未有過的探究、投入的熱情。1904年,他考入南京高等學校時,正值考選留日學生之際,他選派的機遇極大,可是,由于難以籌措留學經費,不得不收回自己躍躍欲試的心情。第三年,他為愛國心所驅使,參加學生拒俄義勇隊,卻被校方強令退學。正當他彷徨迷茫之際,友人將他介紹到長沙明德學校教授英文,他由此獲得生平的第一個職業。轉瞬間,任教已經兩年,所積薪銀已有十余錠,留學之資已經足矣,他的東渡日本留學的愿望,又重新萌發。
1908年,張君勱等得寶山縣政府的全年留學費,赴日本留學。寶山縣之所以如此慷慨,是指望他們學習理工,好日后以實業振興家鄉。可是,他卻偏偏棄理擇文,考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科預科,這使寶山縣很失望,立即停止供給公費。他又開始度那清貧的生活,可是,他的心境卻十分愉悅,而更為榮幸的是,他在日本與自己心儀已久的梁啟超相見,并與其一起成為政聞社的發起者,且擔任評議員。正是在日本,他與現代學術開始正式的接觸,而更為有趣的是,他所學并非日本的學術,而是英、美、德等西方國家的學術。日本給他最深的感觸則是,日本的政體對其國民的適宜性,日本發展的經驗,可以為中國所借鑒。
1910年,張君勱完成早稻田大學的學業,獲政治學學士。次年,在清廷殿試中,得授翰林院庶吉士,即所謂的洋翰林。武昌起義后,他回到家鄉,擔任寶山縣議院議長,接著便出任農商部秘書。1912年,他作為民主黨人的代表,來到日本迎接梁啟超回國。早期的他不僅在政治上追隨梁啟超,就是在學術研究上也是亦步亦趨,緊追不舍。梁啟超的西方文化未必優越,東方文化未必落后的思想,便為他所贊賞,以至在后來的“科玄論戰”中,被他引申而發揮。他的政治立場與梁啟超也基本一致,在由封建制向現代社會轉型時,他們都反對采取革命和暴力,鼓吹漸進式的和平改良。如果說他們之間還有什么差異的話,那就是梁啟超主張君主立憲,張君勱主張民主立憲。
1913年1月,張君勱以《憲法新聞社》通訊員的身份赴德國采訪考察。3月,他入柏林大學專攻政治學。在德國親身體驗的一件事,給他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當時,他在租住的房間內懸掛一幅地圖,并在上面標示日德雙方攻防進退的情形,并且預言德國無勝算的把握。這些細節為房東老太太所懷疑,遂向警察舉報他是日本間諜。警察立即前來偵查,他暫時失卻自由,但是,警察并沒擅入私房,只是緊緊守住大門。后來,還是他請求搜查時,這才有兩名偵探入室搜查。多少年后,他在談論中華民國憲法時,還以此事來證明尊重人權,是民主憲法制度的基礎。
1915年秋,張君勱來到英國,仔細考察久已向往的英國議會。次年,他回國擔任《時事新報》總編輯。期間,他力主中國對德宣戰,并和梁啟超一起斡旋于各國公使之間,呼吁撤消德國的領事裁判權,取消德國的租借地和租界。1917年6月,張勛擁廢帝溥儀復辟,張君勱又頻頻出入各國使館,申辯萬萬不可承認溥儀為帝的理由。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時,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得以參加巴黎和會。他隨梁啟超以非正式代表身份赴歐洲,觀察巴黎和會。這是他的第二次游歷歐洲,二度歐游鑄成他一生中的兩件大事,一是接受國家社會主義思想,二是接受德法唯心主義哲學。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社會主義思潮已在中國成為時尚,誠如國民黨元老馮自由所說:“社會主義的潮流,真有萬馬奔騰之勢,睡在鼓里的中國人便也忽然醒覺,睡眼惺忪的不能不跟著一路走。”不過,社會主義有品牌之分,張君勱所選擇的國家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是迥然不同的,反對階級斗爭,主張勞資攜手,反對直接行動,主張議會路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主張民主政治,反對國際主義,主張國家主義。這些不和諧的內容,注定了他與中國共產黨人的分道揚鑣,也就注定了他往后的政治命運。
巴黎和會強權政治的事實,使張君勱對所謂國際公法、公理失望之極,甚至想把“所藏國際法書籍付諸一炬”。他越來越覺得所研究的政治、經濟現象是那么的隱隱綽綽,模模糊糊,如同霧里看花。于是,他放棄了政治經濟的研究,用他的話說,是從“政治國”跳入“學問國”,即由社會科學的研究轉入哲學的研究。
去了一政治國,又來了一學問國;每日為此學問國之建設作種種打算。……數年來以政治為飲食水火之君勱,已斷念政治矣。吾同志誠有出死入生之舉,以急國家之難,則弟之赴湯蹈火,決不人后。若夫現實之政談,則敬謝不敏。
張君勱信奉起德法唯心主義哲學,并由此而上溯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頭,從而開啟中國文化保守主義的思潮。原先,他和許多激進的知識分子一樣,對東西方文化的態度是,“中國一無是處,西方一切都值得仿效”。現在則起了根本的變化,更多的是批評西方文明的“不是處”,張揚東方文明的“是處”。
科學受道德限制
1923年2月,張君勱應吳文藻的邀請來到清華大學,對一批赴美留學生發表《人生觀》演講。他說,人生觀與科學不同,其表現內容為:“第一,科學為客觀的,人生觀為主觀的”;“第二,科學為論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觀則起于直覺”;“第三,科學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觀則為綜合的”;“第四,科學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觀則為自由意志的”;“第五,科學起于對象之相同現象,而人生觀起于人格之單一性”。由此,他得出結論:“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而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為力,惟賴人類之自身而已。”
此論一出,立即在知識界激起軒然大波。首先,丁文江當面提出責難:“科學而不能支配人生,則科學復有何用?”兩人辯論了兩個多小時,誰也沒有說服誰。素“以擁護科學為職志”的丁文江,豈肯善罷甘休,又在《努力周報》上發表《玄學與科學》的論文,指出,在歐洲鬼混了2000多年的玄學,經過重新裝點,“大搖大擺的跑到中國來招搖撞騙”,“玄學的鬼附在張君勱身上”,“若是我們相信了張君勱,我們的人生觀脫離了論理學的公例、定義、方法,還成一個甚么東西?”張君勱當然不會沉默不語,也在《北京晨報》上發表《再論人生觀與科學并答丁在君》,對丁文江的批評作出答辯。于是,一場“科玄論戰”就這樣拉開帷幕。
戊戌變法以來的中國知識界,正如胡適所說:“這三十年以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這樣幾乎全國一致的崇信,究竟有無價值,那是另一問題。我們至少可以說,自從中國講變法維新以來,沒有一個自命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毀謗‘科學’的。”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人類社會造成的慘劇,使梁啟超、張君勱對科學萬能提出懷疑,梁啟超在其著名的《歐游心影錄》中說:“我絕不承認科學破產,不過也不承認科學萬能。”張君勱緊隨其后,發表《人生觀》論文,就是要把人生觀從唯科學主義中剔除出來,區分開來。
此時,西方的知識界精英們已給西方文明敲響了警鐘。1920年,英國著名思想家羅素在中國巡回演講中,盛贊中國文明,檢討西方文明。他們在反思,西方文明如此下去,與預期的美好目標,是否會南轅北轍,滑入泥淖。張君勱正是由此切入問題的實質,試圖回答物質與精神的關系。他說:“人生者,介于精神與物質之間者也”,“古往今來之大思想家,每于物質精神之不調和,不勝其悲憫,于是,靜思默索,求得一說焉”。人類在解決精神與物質之間的沖突中,通過探索和努力,形成了人類自身的文明。
在將東西方文明對照比較后,他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學家,側重內心生活之修養,其結果為精神文明。三百年來之歐洲,側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其結果為物質文明”。他認為,西方文明和國人的西化趨向,都是唯科學主義和功利主義在作祟,而恰恰輕視了人類自由意志的精神作用。科學只是外力,人類如無自由意志的精神作用,那么“朝作夕輟,人生如機械然”,“今日歐美之迷信科學者,已不如十九世紀初年之甚。”由此,我們難道不應該從中汲取些什么嗎?
這里必需指出的是,張君勱并非一概地排斥西方的工業文明,而是在提醒國人向西方學習時,切記和警惕西方文明的偏失,以免重蹈覆轍。同樣的道理,他之批評科學,也不是籠統地反對科學,而是主張“科學能力有一定界限之說”。他歷來提倡,“科學的發展要受道德的限制”,“科學結晶之使用,應有倫理或道德上的標準”。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國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投擲原子彈,人們只是在此時才感受到問題的嚴峻,人類文明將面臨著被自己所創造的科學摧毀的危險,所以,人類必須正視問題的實質,那就是站在倫理學的高度,對科學予以審視。他稱,處在這樣一個“原子能時代”,只能以德智主義哲學予以評判,他在《原子能時代之道德論》中說:
原子彈發明后,它已不若千里鏡當作千里鏡用,蒸汽機當作蒸汽機用,因為原子彈之使用可以消滅敵國的人民,擴大言之,可以消滅人類,這使原子彈的使用發生一個大問題,是不是要了武器,不要人類?還是要人類,不要武器?假定自然科學研究的目的是所以增益于人類的,而不是害人類的,又假定到了有武器而沒有人類之境地,是人類自身所決不做的,那么,我們必須在這方面有一個大大的覺悟。現今科學發展碰到了一個新的界限,換句話說,知識的發展與人類的生存不能并立時,知識應受道德的限制。
20世紀20年代初期的“科玄論戰”,早已落下沉重的帷幕,科學派大獲全勝,玄學派遭人唾罵。然而,在經歷半個世紀的風雨歷程后,學界在評述這場論爭時,其心氣平和了許多,言詞客觀了許多,結論也自然公允的多了。唐君毅先生評價說:“君勱先生的哲學思想,對一個學哲學的人,包括我在內來說,其細微之處,當然有些尚待商榷,因為學哲學之人間總有許多異同;然在大體上說,其在人生觀論戰所表現的哲學思想方面,可說是一種正路。……科學以外之哲學、文學、藝術、宗教之學問應在學術世界中占相當的地位。然五四時代之淺薄思想,于非科學者,即稱之為玄學,加以貶斥,卻使后來之國家學術研究,限在極小之范圍中,不能用以樹立中華民族之學術文化生命,這是很可惋惜的。”
我穿了件濕衣服
1923年夏秋之交,面對軍閥割據的局勢,國人提出種種解決國是的主張,概括起來不外乎:舉曹錕為非常大總統及立孫中山為總統、曹錕為副總統等方案。張君勱在梳理這些方案后,認為這些都“不足以解決時局”,獨自提出一個“合南北要人于一爐”的國是主張:設立以張謇、汪精衛、孫中山、黎元洪、吳佩孚等七人組成的國民委員會,作為國家最高行政機構,議決國是。他夸耀自己的國是主張具有四點長處:一是使正在爭雄之各要人地位平等,免去地位高下之爭;二是遇事公決,無人大權獨攬;三是各人可相互牽制彼此制衡;四是委員會立于公允立場上,不偏向于任何一派軍閥,有利于辦好裁兵和公開財政二事,此二事成,則中國可望實現法治之局。
此時,他的從政建功的欲望十分強烈,然而,在現實政治的渦流之中,他充其量是個“政治教育家”和“政治評論家”而已。他辦過政治大學,有意把政治大學辦成“民主政治的實驗所”,可是,不幾年,他因涉嫌“進步黨”,政治大學便為國民黨所接收;他還與人辦過《新路雜志》,發表過《一黨專政與吾國》《現時政潮中國民之努力方向》《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之解剖》和《當代政治學之趨勢》等,闡述唯心史觀,批評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批評蘇俄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革命。他的這些所言所行,已為他往后的政治活動奠定了基本的路徑:既不與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為伍,又與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不相為謀,企圖以所謂“第三條道路”,超然于黨派之外。
1932年4月,張君勱、張東蓀、湯住心、胡石青等人發起的“中國國家社會黨”在北平創立。“國社黨”偏偏“生不逢時”,因為,自1927年以來,國民黨為建構“黨外無黨”、“黨外無政,政外無黨”的一黨專政的統治格局,不僅對共產黨進行圍剿,其他政黨也都處于非法地位,時時提心吊膽,惟恐遭到取締。“國社黨”也命途多舛,只能在縫隙中求生。“國社黨”成立之初,其機關刊物《再生》便被視為反動刊物,后經張君勱的出面交涉,此事稍稍平息。1934年7月,“國社黨”在天津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政綱、黨章。張君勱被選舉為中央總務委員,兼任總秘書,總攬黨務。大會發表了宣言,提出“國社黨”的主張,除舉國一致對外之方針、國家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主張和民族主義的立場外,強調中國應該建立政黨政治:“中國今后當采酌英美現制之精神,由各黨派之合作,予政府以大權。”
1937年7月15日,國民黨在廬山召開國是談話會,發動各黨派共赴國難,抵御日寇。張君勱受到邀請,會上,他在蔣介石、汪精衛演說后,第一個發言說:“目前國難嚴重,在此時期,民族生存之重要,超過一切,必先有民族,方可談到其他,在精誠團結聲浪中,在野人士,對政府應表示信任,發揮善意,本人尤鄭重表示此意。”會后,張君勱成為國防參政會參議員。次年4月,他代表“國社黨”發表《致蔣介石汪精衛信》,表示:“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意旨”,“對于國民政府一致擁護而外,別無起死回生之途。”蔣介石、汪精衛很快便作出反應,發表《覆張君勱》,對國社黨的態度表示歡迎,指出:“全國賢智之士,或加入本黨,共同負荷,或秉持共信,一致努力,俾捍御外侮,復興民族之使命,得以早日完成。”從此,“國社黨”得到承認,由秘密轉為公開。
同年12月,張君勱又發表《致毛澤東先生一封公開信》,對中國共產黨提出規勸:“以八路軍之訓練任命與指揮,完全托之蔣先生手中”;取消陜甘寧“特區之制”;“將馬克斯主義暫擱一邊”。迄今為止,沒有發現毛澤東的復信,但是,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即已表達了中共一貫的思想。毛澤東說:“國外的資產階級政黨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領一部分軍隊。中國則不同,由于封建的割劇,地主或資產階級的集團或政黨,誰有槍誰就有勢,誰槍多誰就勢大。處在這樣環境中的無產階級政黨,應該看清問題的中心。”“歷史不長的幾個小黨,如青年黨等,沒有軍隊,因此就鬧不出什么名堂來。”“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他也知道這封信不會得到回應,那么,他為什么要知其不可而為之呢?我們不妨再回到《致蔣介石汪精衛信》中,從那里我們似乎可以找出答案。他說:
吾國圣賢之宇宙觀曰:“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惟其心目中注意之方面多,故不好為一偏與排他之論。反之,最近歐洲各國政局,常有有我無他之象。立足于無產階級者,不容資本家之存在;立足于個人自由者,不顧及全社會之幸福,頗有為我東方人所不克了解者矣。
張君勱不獨要求中國共產黨放棄武裝,也要求蔣介石廢棄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他所鑄就的政治模式,多少有些天真幼稚,一廂情愿。國民黨至退守臺灣島都沒有舍棄一黨專政,而中國共產黨則結合中國國情,實行中共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他脫離實際政治遠矣,臺灣的梁敬錞先生分析說,張君勱“總想以學風納政潮,以筆桿代槍桿,以法治代人治;大概因此之故,他畢竟辦了黨。為了黨,他貼錢,他惹禍,費了力氣,糟蹋了時間,窮困了生活,既不曾因黨而增加了他半點學術聲光,又不曾因黨而掌握了一天政治權勢”。

1946年11月17日,“民盟”代表去南京中共辦事處梅園新村送周恩來。左起:周恩來、鄧穎超、羅隆基、李維漢、張申府、章伯鈞、沈鈞儒、董必武、黃炎培、張君勱、王炳南
1941年3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簡稱“民盟”)成立。張君勱為發起者和領導者之一。從1944年開始,他便積極投身于國統區的民主運動,希望中國“將來的政治,必須以各黨派共謀的民主政治”。在國共兩黨談判期間,他力促兩黨化干戈為玉帛,并提出一個折中的方案,希望國共兩黨予以接受,這個方案是:第一,國家“主權在民”;第二,國民黨放棄“特殊地位”,“各政黨咸立于國家之下”;第三,“統一軍令”,全國軍隊“立于同種號令之下,不許兩種軍隊相對峙”。他想以公允的姿態,做著一件姥姥不親舅舅不疼的事情,那就是硬拉著國共兩黨入他的政黨政治的框架之中,結局是可想而知的,吃力不討好,碰了一鼻子灰。
1946年8月,張君勱、張東蓀領導的國家社會黨與伍憲子、徐傅霖領導的民主憲政黨,合并為民主社會黨。10月,蔣介石違背政治協商會議決議,不顧中共和“民盟”的反對,片面決定召開制定憲法的國民大會。正是在這種情形下,張君勱召集民社黨會議,提出只要能通過憲法草案,實行法治,逐漸實現民主政治,民社黨就應參加國民大會。他為鄭重起見,特意致函蔣介石,提出參加國民大會的兩大前提條件:一是“徹底實行停戰命令”,二是“徹底實現政協決議”。他本人雖然沒有參加制憲國大,但是,這件事已經造成難以挽回的負面影響,“民盟”宣布:“民社黨之參加‘國大’,系違背民盟中規定條例,實應請其退盟。”至于他本人,1949年1月28日,毛澤東在圈定的43名戰犯中,將他列于最后一名。
一介書生關心政治,熱衷國是,但卻總是泛泛空論,無的放失。他所設計的種種方案,每每以失敗而告終,這種“理論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常常使他感到“政治上的煩惱”,所以,他生前常常自嘲說,對于參加政治活動,“我也是沒有辦法呀,就好象穿了一件濕衣服,現在脫也脫不下,只好這樣穿下去”。
儒學傳播在海外
人民解放戰爭已成摧枯拉朽之勢,國民黨政權已是氣息奄奄。張君勱所追求一生的民主憲政的理想終成泡影,檢討一生的行跡,不免黯然神傷,心灰意懶。1949年3月,李宗仁與何應欽先后來上海,請他派人參加行政院,均被拒絕。此時,印度德里大學及泰戈爾大學發來邀請,他欣然答應前往講學,主講“中國孔孟哲學”。他先飛香港轉澳門,在這里集中精力備課。可是,李宗仁還是不死心,又派居正勸請他出山,許諾可任行政院長,再次被他婉拒。到了印度,他巡回演講于11所大學,所涉選題為:儒家受佛教影響后之復活;中國現代文藝復興;孔子哲學,孟子哲學,老子哲學;中國政黨之發展。
新中國建立后,面對新制度、新秩序,很多著名的知識分子都有一種無所適從的感覺,馮友蘭懷著同樣的心態,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自己以前講授的是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感到很悔疚,從今往后要學好馬克思主義,以五年的時間,重寫一部中國哲學史。張君勱知道后,頓時感到“身發冷汗,真有所謂不知所云”,他認為馮友蘭丟失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最為珍貴的氣節。為此,他寫下《一封不寄之信——責馮芝生》,批評馮友蘭輕易改變理想,未能將中國哲學與自己的生命融而為一,“心口不一,口言而身不行”。他還由此專門引申出《中華民族精神——氣節》,文章說:“不作人云亦云之文,不作言之無物之文,不作隨俗浮沉之文,不作敷衍塞責之文。執筆而書之,必胸中真有所見,而有益于世道人心者。良以世亂若此,我幸茍全性命,其能不苦心焦思,嘔心瀝血,以冀挽救吾族于萬一乎?”
中國共產黨并沒有忘記張君勱,通過陳叔通向他發出友好的信息,邀請他回到祖國。周恩來還讓張經武赴印度約見他,可是,他卻拒絕見張經武。顯然,他看重的還是自己所堅守的中立的政治立場,不是嗎?政權變更的關鍵時刻,他既不去臺灣,也不來大陸,獨獨選擇的是海外飄泊的游子生涯,所表明的不正是自己的政治態度嗎?即在國共兩黨之間走一條獨立不偏的路線。如此,他已不與任何政治利益集團發生關系,可以平心靜氣地看待任何問題,隨心所欲地發表言論,撰寫文章,這正是他所崇尚的知識分子的氣節和尊嚴。
1951年12月,張君勱就要離開印度前往美國。他在印度生活了兩年,講學期間,給印度學界傳播了中國哲學,備受學界崇愛,印度朋友稱他是“玄奘后第一人”。他在印度完成了多篇學術文章,如:《讀存齋先生“往自由與民主之路”文》《學術思想自主論小引》《英文版〈新儒家思想史〉漢文自序》《義凈與鄭和》等。赴美前,他還特意往東南亞國家考察,與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等會晤,旋即考察澳大利亞、馬來西亞等國,這些都表明沉寂講學,是他的無奈和痛苦,自言超然于政治的他,與政治還是“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次年4月,張君勱來到美國華盛頓,住在一位朋友的家中,這里離美國國會圖書館很近,只有兩三條街道的路程。美國國會圖書館的藏書,堪稱世界之首,難得的是,在這里可以很方便地查閱中國絕版書籍。他每日都在這里讀書、寫作,《新儒家思想史》就是在這里完成的。除此之外,他還對王陽明學說進行研究和寫作,后經牟宗三整理成《比較中國陽明學》。1955年5月,斯坦福大學聘請他擔任研究員,給予相應的工資,自此,他才從晦暗的生活陰影中走出來,再也不用過那種吃上頓愁下頓的日子了。可是,好景不長,他在斯坦福只待了七個月又“失業”了,不過,《世界日報》很快便聘請他主撰社論,于是,有了相當穩定的經濟收入,過著一段衣食無憂的日子。
1958年1月,他與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聯名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書》(又名《中國文化宣言》)。《中國文化宣言》洋洋灑灑四萬余言,一經發表,頓時在海外華人中激起反響。它的基本內容反映出現代新儒家的共同認識,如,肯定中國文化的精神生命;中國文化有一脈相傳的道統;中國文化既注重倫理道德,又不乏宗教精神;心性之學為中國學術思想的核心;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得益于它的博大精深;中國文化既有民主思想的種子,又有科學精神。6月,他得友人資助,作環球講學,所經漢堡、倫敦、西貢、香港、東京等地。轉了一圈再回舊金山,繼續為《世界日報》撰寫社論,度那鬻文為生的日子。
1961年5月,陳誠赴美曾與之會晤,再次希望張君勱回到臺灣,他回答:如無三黨(國民黨、青年黨、民社黨)合作,是不會回臺灣的。他還是大夢未醒,仍在回首1946年“三黨合作”的前塵往事。已逾古稀之年的老人所樂此不疲的事情,便是向世界介紹、傳播中國儒家思想。晚年耗時最長、精力最多的心血之作《新儒家思想史》(英文)下冊,終于完稿,這樣,繼1957年出版的《新儒家思想史》上冊,這部著作全部付梓印刷。由于他對中英文都嫻熟自如,對中西哲學又融會貫通,因此,他的《新儒家思想史》在英語世界發行后,便備受關注,格外受重視。
張君勱已入耄耋之年,老而多病,命運無常的緊迫感,使他較著勁要與歲月的年輪賽跑。從1965年至1967年,他的學術活動安排得滿滿的,應韓國大學李相殷教授的邀請,由美國飛漢城,出席“亞洲現代化問題國際學術大會”;在《自由鐘》發表《三通性質今解》《文化核心問題——學問之獨立王國論》;應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的邀請,又由美國飛星洲講學。1968年12月,他因胃癌入舊金山柏克萊醫院治療。次年2月23日,他帶著抽搐的病容,懷著未竟事業的遺憾溘然長逝,享年83歲。這位現代新儒家創始人之一的他,一生都諍言剛直,其理想性的主張,往往與現實悖異,甚至令當政者誤解和難堪。然而,他對現代中國政治及文化啟蒙的貢獻,卻是怎么也抹煞不了的,十多年前,朋友們所出《張君勱先生七十壽慶紀念論文集》中所言,可為他一生的蓋棺之論:
先生種學與身,著書立言,倡導民主,履危犯難,組黨參政,抉摘蔽惑,齊一眾議,卒能完成憲法,政制以立,民權以張,蓋非先生博大精深之知,高瞻遠矚之見,亢直不阿之操,無以促其成也。……夫以先生之介無我,使建國功成,民治樹立,自無吝于個人之權位。蓋先生之志,為國本絕續之大計,人類文化之趨向,與夫宇宙真理之所在。衛道憂時,任重道遠,其所以啟迪今世之功,誠不可沒也。
責任編輯/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