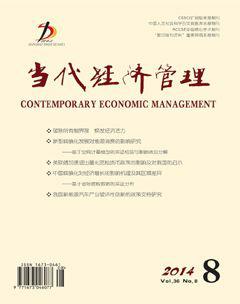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破壞性創新的政策支持研究
黃++棟+祁++寧
[摘要]提高新能源汽車產業創新水平、將新能源汽車產業置于國民經濟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地位予以支持已成為世界大國博弈的重要命題。文章將破壞性創新理論用于指導我國的新能源汽車產業政策,在公共科技政策分析的基本政策工具框架下,采用內容分析法分析了2009年至今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創新的政策支持體系;對特斯拉汽車成功進行破壞性創新的案例及對我國的啟示作了實證研究,進而提出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破壞性創新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破壞性創新;新能源汽車;創新政策
[中圖分類號]F062.9[文獻標識碼] [文章編號]1673-0461(2014)08-0079-08
一、緒 論
1. 技術和需求之間的相互作用:破壞性創新的動力
根據Christensen(2004)的觀點,破壞性創新產生的原因正是由于技術進步的滯后與消費者需要的產品性能之間的矛盾,即技術進步的軌跡與消費者所能利用的產品性能的軌跡之間的不一致。同樣,破壞性創新作為創新的一種,其發展的動力也離不開技術和需求之間的互動。“破壞”描述的是創新成果對市場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必須通過產品性能的改進作為中介,其背后是產品性能能夠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對于消費者而言,對產品和服務的購買并非是購買了技術本身,而是購買了技術所能給消費者帶來的改變。因此,消費者付出的成本與產品能給消費者帶來的改變之間的關系就是產品的性價比。
2. 支持創新的政策工具
直接研究政策促進破壞性創新的文獻目前較為少見,而促進產業創新水平提高的政策支持的有關研究層出不窮。Rothwell和Zegvold(1985)從政策工具的角度,將創新政策分為供給型政策工具、環境型政策工具和需求型政策工具。張雅嫻、蘇竣(2001)采用Rothwell的分析方法,對我國政府激勵軟件和微電子產業發展的政策進行了政策工具的適用性分析,并指出由于政策工具的使用不合理,抑制了政策的總體實效。在其基礎上,趙筱媛、蘇竣(2005)從政策工具的視角,結合科技活動特點和科技政策作用領域等因素,構建了公共科技政策分析的三維立體框架,其中X維度是其基本政策工具維度。施麗萍(2011)對這一基本政策工具維度進行了修正(見表1)。
二、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破壞性創新的條件與障礙
1. 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政策概況
回顧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政策,根據政策密度,可明顯地劃分為兩個階段。2009年以前,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以政府主導、科研院所完成研究任務為主要特征,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未能確立。2009年后,產業政策密集出臺,產業發展思路日益明確,政策支持力度迅速加大。
1999年全國“清潔汽車行動”以降低汽車排放污染、凈化空氣為目標,標志著我國從政策層面開始重視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發展。“十五”期間,我國提出新能源汽車“三縱三橫”的開發格局:“三縱”指混合動力汽車、純電動汽車、燃料電池汽車三種不同的技術路線;“三橫”指多能源動力總成控制系統、電機及其控制系統和電池及其管理系統的關鍵技術。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對新能源汽車產業的政策支持力度迅速增大,新能源汽車的產業地位被提高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和2009年以前相比,這一時期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支持政策具有幾個顯著的特點。一是政策密度大,對產業構成重大影響的規劃、補貼、市場培育等政策在短時間內連續出臺;二是思路日益清晰,從混合動力汽車、純電動汽車、燃料電池汽車三種不同技術路線共同發展到將純電驅動作為主要戰略取向,政策指向更加聚焦;三是演進過程加速,對原有政策調整補充的反應時間縮短。本文根據公開資料對2009年至2014年4月關涉新能源汽車產業的所有全國性政策文本進行了搜集整理,按時間順序排列如下(見表2)。
2. 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開展破壞性創新的有利條件
(1)巨大的潛在市場需求與技術潛力之間的互動。中國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的統計,2013年,我國汽車產銷2 211.68萬輛和2 198.41萬輛,已連續五年蟬聯世界第一。由于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這一產銷數據有較大可能被不斷刷新提高。汽車產業的巨大市場背后是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巨大潛在需求。另外,經過數十年的積累,我國汽車制造業已積淀了一定的技術基礎,加上新能源汽車領域近二十年的探索,目前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具有較大的技術潛力,在動力電池和電機領域技術水平已有較大的發展。這種巨大的潛在市場需求與技術潛力之間的互動構成了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開展破壞性創新的最關鍵有利因素。
(2)相對完整的產業鏈為產業價值鏈重新整合提供的便利。新能源汽車產業關聯產業多、產業鏈條較為復雜。我國有較為齊全的工業體系,具體到新能源汽車領域,上游原材料、關鍵零部件、整車制造、售后及增值服務企業等產業鏈環節均有布局,這為產業價值鏈的重新整合提供了較大可能。產業價值鏈的重整能為企業價值鏈的重構帶來便利,而這恰是商業模式破壞性創新的重要獲得途徑。
(3)政府的積極態度及其對產業發展的深刻影響。在我國,政府行為對產業發展有著較為深刻的影響,通常情況下,政府的積極態度與產業發展的速度呈明顯的正相關關系。我國各級政府對于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發展具有較高的積極性,出臺了多項支持政策。特別是國發[2010]32號文《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將新能源汽車產業列為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使新能源汽車產業破壞性創新成果的產生有了更好的政策土壤。
3. 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開展破壞性創新的主要障礙
(1)在位企業依然是市場競爭主體,特別是整車制造領域新進者極少。目前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主要競爭主體依然是傳統燃油汽車產業巨頭,以傳統燃油汽車產業巨頭企業投資新能源汽車業務為主要表現,整車制造領域新進者極少,新進者幾乎沒有市場地位,而這些大企業在開展破壞性創新方面有更多的困難。像特斯拉汽車公司一樣“為新能源汽車而生”的知名企業缺失。另外,由于中國市場仍然存在廣闊的傳統燃油汽車市場空間,因此企業在發展新能源汽車業務時常常將其置于依附地位,形成了較強的路徑依賴,使企業依然將更多的精力和資源集中于傳統燃油汽車的研發與銷售上,制約新能源汽車領域破壞性創新的發展。
(2)技術積累不足的同時,研發投入仍然落后于國外先進企業。我國在新能源汽車產業鏈的技術積累仍然不夠,但與此同時,我國新能源汽車企業的研發投入仍然落后于國外先進企業。以通用汽車為例,在2001~2004年期間通用投入10億美元用于新能源汽車的研發,該公司2009~2012年新能源汽車研發領域的預算為30億美元;2009年道氏化學、LG等四家電池生產企業在美國密歇根州投資17億美元用于新一代新能源汽車電池的研發。而一汽“十一五”期間在新能源汽車領域的研發投入總計才3億元人民幣;東風汽車“十二五”期間計劃投入的研發經費為30億元人民幣;截止到2013年上汽集團在新能源汽車領域的研發總投入為40億元人民幣。
三、支持新能源汽車產業創新的基本政策工具視角分析
采用2009年以來,四年間出臺的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密切相關的全部政策文本20個(見表2),根據公共科技政策分析的基本政策工具維度(見表1),本研究將20份政策文本的有關具體條款作為分析單元,進行抽取和編碼。按照已經界定的類目體系,將分析單元(編碼號)歸屬到對應的類目中。
endprint
1. 總體狀況
根據對文本的梳理,2009年以來我國支持新能源汽車產業創新的政策總體上可以劃分為幾條主線。一是以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示范推廣試點工作(編號A、E、H、I)、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工作(編號Q、R、S、T)為主線,通過支持城市或區域先行先試、獲得政策支持,意圖達到“以點帶面”的效果。二是以產業技術創新工程(編號O)及建立和支持專門實驗室(B、J、P)為代表的政府對技術創新的直接介入。三是以準入門檻、目錄管理(C、K)為代表的管制政策。四是針對消費者的直接補貼(F、L)。在這四條主線之上,是總體規劃和目標設定(D、G、M、N)。
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創新,是一項關涉到科技、財稅、產業發展等多方面的綜合性任務,50%的政策文本由兩個或兩個以上部門聯合發布。財政部牽頭發布的政策占總數的50%,國務院在《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2012-2020)》中明確的應當作為部際協調牽頭單位的工業和信息化部牽頭發布的政策數量最少,僅1個(如圖1)。這一情況意味著財政政策在新能源汽車產業有關政策工具的運用中處于強勢地位,下文其他數據也佐證了這一觀點。
政策類型與政策力度密切相關。層級較高的政策類型僅《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1項,行政法規、條例、部令缺失。50%的政策以通知的形式發布,內容權威程度不夠。新能源汽車安全性是產業發展中的焦點問題,而以上政策中僅有的關于加強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示范推廣安全管理工作的一項是以各政策類型中權威程度最低的函的形式發布。
根據統計,20項政策涉及到40個政策工具的使用,其中供給型政策工具6個(占15%),環境型政策工具26個(占65%),需求型政策工具8個(占20%)。三種不同維度的政策工具盡管都有運用,但從數量上看相對失衡。尤其顯著的是,環境型政策工具中補貼與金融支持、稅收優惠兩項便高達12個(占總數的30%),這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財政手段在新能源汽車產業有關政策工具的運用中處于強勢地位的觀點。
2. 供給型政策工具情況
政府通過提供科技創新的相關要素直接推動和引導創新主體進行技術創新和產品研發,是重要的政策手段。目前我國尚未出臺新能源汽車產業領域人力資源培養與吸引的專項政策。《關于進一步做好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示范推廣試點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強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示范運行期間的監控和評價,但沒有涉及有關數據共享機制。科技基礎設施建設和科技資金投入上都有著力,已成立兩個重要的國家地方聯合工程實驗室,并對有關技術創新活動進行了直接的科技資金投入。保障科技活動順利進行的配套服務通常體現在日常的行政管理工作內,目前沒有出臺專門政策。供給型政策工具維度下的五種具體政策工具,目前的6個分析單元對應了除公共服務外的四種,這當中67%(共4個)集中在科技基礎設施建設和科技資金投入上,人力資源培養、科技信息支持及公共服務相對薄弱。
3. 環境型政策工具情況
環境型政策工具是政府通過提供有利的政策環境對產業界施加影響,間接引導企業走創新發展之路的方式,是我國現有新能源汽車產業創新的政策支持中最重要的部分,在數量上占比達65%。26個環境型政策工具中,涉及到財政稅收的(補貼與金融支持9個、稅收優惠3個)12個,幾乎占環境型政策工具的一半;法規管制9個,目標規劃5個,知識產權保護無。環境型政策工具維度內數量失衡。
目標規劃政策工具方面,我國已形成總綱(《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產業專門規劃(《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2012-2020)》)、產業科技發展專項規劃(《電動汽車科技發展“十二五”專項規劃》)三位一體的相對完備的體系,對總體目標、市場空間、技術發展都作出了明確規劃。
補貼與金融支持,包括貸款、補貼、擔保、出口信貸、風險投資等方面。而在現有9個政策工具中,8個是補貼方案,僅有的1個籠統地提出了強化金融支持方面的要求,沒有實施細則和具體方案。央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也沒有出臺專門支持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的政策。由此可見,現有政策對補貼與金融支持的運用過于倚重直接財政補貼。
法規管制所涉及的內容可以分為三個方面。一是對行業準入、標準體系等強制要求;二是對技術路線的統一規定;三是為營造公平競爭環境作出的努力。法規管制政策工具在全部40個政策工具中占比也達到了22.5%,對管制政策的偏好程度也較高。另外,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政策完全空白。
4. 需求型政策工具情況
需求型政策工具指政府通過優先采購自主創新產品、貿易管制等措施減少技術創新過程中的不確定性,穩定新技術和新產品市場,以保證科技成果產業化的順利進行。我國現有的8個需求型政策工具中,公共技術采購占5個。既包括政府直接采購,也包括政府協調其他采購主體進行的采購。另外,關于充電設施的歸類,由于其建設目的是為了減少科技成果產業化中的障礙,由政府出資或政府協調資金進行建設,因此被歸類到公共技術采購中。
產業技術創新工程明確將企業作為新能源汽車的創新主體,將科技研發任務外包給非政府組織(主要是企業組織)進行。鼓勵引進國外先進的新能源汽車產業技術,支持國內企業進軍國際市場等,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各個方面均有涉及,但仍以公共技術采購為主要手段。
5. 分析結論
通過對政策文本進行內容分析,本文認為,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支持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創新的政策體系,組合運用了供給型、環境型、需求型政策工具,但現行政策體系還不夠完善,突出表現在各層面政策工具應用存在過濫或缺失。
(1)政策類型層次不夠完整,權威政策類型相對缺乏。從政策文本類型看,除國家權力機關制定的法律、國家行政機關制定的條例外,根據《國家行政機關公文處理辦法》規定,還包括命令(令)、議案、決定、公告、通告、通知、批復、函、會議紀要等類型,這些不同層次的政策類型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政策體系。不同的政策類型之間存在效力差別,法律處在各政策類型的頂端。我國目前沒有新能源汽車領域相關的法律和行政條例,《可再生能源法》和《節約能源法》對有關內容有所涉及,但針對性不強。大部分政策類型為國務院部委發布的通知,部令數量都為零。整體上看,支持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創新的政策層次較低,權威政策類型相對缺乏。
(2)環境型政策工具、尤其是財政補貼政策應用占比過大。前文研究已經表明,三種政策工具維度中環境型政策工具的數量獨占近2/3;在全部14種政策工具中僅財政補貼一種就占比22.5%。一方面體現了國家財政預算角度對新能源汽車產業的重視和支持;另一方面也提示了非金融財稅政策濫用的風險。在公共科技政策分析的基本政策工具維度理論中,補貼與金融支持政策工具是應當包括財政補貼和金融支持兩個方面內容的政策手段,貸款、擔保、出口信貸、風險投資的作用不能片面地被直接補貼取代。
(3)部分政策工具的應用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現有政策中,涉及加強公共服務和知識產權保護的內容完全空白;關于人力資源培養內容較為籠統;科技信息支持的內容不夠完善。加強公共服務、人力資源培養和科技信息支持三項政策工具是產業創新的基礎性政策,沒有良好的公共服務環境、高素質的人力資源隊伍和有效的科技信息支持就很難有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而知識產權保護直接關乎科技創新的積極性,同時也是我國各個高新技術產業在國際貿易競爭中面臨的共性壓力。這部分政策工具直接針對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基礎性或焦點問題,但在現有政策體系中卻相對缺失。
endprint
四、案例分析:特斯拉汽車成功的啟示
1. 僅僅技術突破或商業變革都不能有說服力地解釋特斯拉汽車成功的原因
特斯拉汽車的成功是其在技術和商業模式兩個層面進行破壞性創新的結果。特斯拉汽車真正解決了其他純電動汽車產品和傳統燃油汽車競爭時在續航里程、百公里加速、操控性等方面的短板;商業模式的破壞性創新則保障了其產品能迅速打開銷路,并實現公司財務的健康。僅僅從產品的角度,性能水平能與特斯拉現有車型正面競爭的純電動車并不是沒有,但從市場的角度,像特斯拉這樣能嚴苛地控制成本并準確地找到目標客戶的產品暫時還沒有出現。
2. 特斯拉汽車十分典型地符合破壞性創新的特征
特斯拉汽車公司產品的切入路徑,恰恰是回避傳統燃油汽車市場數目龐大的中端利基客戶,開拓的是注重身份、環保和高性能的新的客戶群體;而特斯拉汽車以操作簡便、設計人性化著稱,沒有在從傳統燃油汽車向純電動汽車轉換的過程中添加任何使用上的不便,反而優化了用戶體驗;企業也將最終對主流市場現有傳統燃油汽車的徹底替代作為遠景。特斯拉汽車技術層面破壞性創新,是針對目前客戶需求不能被滿足的部分,是技術與需求互動的結果;而商業模式破壞性創新的形成,也是特斯拉通過顧客價值創新尋找新的利潤來源;對企業價值鏈進行整合或拆分,使成本結構發生變動的結果。
3. 非財稅的金融政策支持在特斯拉汽車的成功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非財稅的金融支持在特斯拉汽車公司發展中起到關鍵作用。2009年,美國政府決定向特斯拉汽車公司提供一筆低息貸款,用于擔負特斯拉S電動車的工程和研發成本。特斯拉汽車公司首席執行官Musk曾在多個場合表示,獲得這筆貸款的時機正是公司深受金融危機的不良影響、財務上陷入艱難的時段,美國能源部的這筆貸款對于特斯拉汽車公司的成功脫險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這筆款項已開始被償還,且計劃償還完畢的時間比原定提早五年。
4.“需求拉動”成為特斯拉汽車誕生的最根本因素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需求拉動”的作用比“供給推動”來得更直接、更有效,被普遍認為是影響技術創新方向和速度的重要工具,破壞性創新的動力恰恰是技術和需求之間的相互作用。一方面,美國通過補貼和碳交易擴大市場需求,對市場需求進行正向的強烈刺激;另一方面,通過強制政策實現傳統燃油汽車被替代,對市場需求進行逆向的強烈刺激。早在2009年,加州空氣資源管理局就通過了一項較為激進的計劃,要求到2050年,全州銷售的所有汽車都必須是零排放汽車;同時,加州政府據此對汽車廠商下達了州內傳統燃油汽車和新能源汽車銷售的配比任務;另外,加州已經開始對部分行業征收碳排放稅,汽車也將在不久后被納入課稅范圍,特斯拉汽車公司成為了這一系列舉措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加州是全美國環境政策最為嚴苛的州,油價高企、管制嚴格,減排目標十分明確,使用傳統燃油汽車受到政策的擠壓,這極大地刺激了新能源汽車的需求,從而激發了市場的創新活力。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前文已在公共科技政策分析的基本政策工具視角下對我國現有新能源汽車產業的有關政策進行了分析,并得出了分析結論。在這一分析結論的啟發下,針對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破壞性創新的環境,通過與破壞性創新成功典例特斯拉汽車的經驗的比較研究,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建議。
1. 建立面向破壞性創新的多層次政策支持體系
根據我國新能源汽車領域有關法律和行政法規缺位的現狀,結合美國在以法律為統領的政策體系構建上的經驗,應當加強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有關專門法律法規的制定工作,將新能源汽車產業創新活動納入法制化軌道,用更高層次、更具約束力的專門法律法規統領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創新的政策支持體系,使其他層次政策的制定有法可依。建立面向破壞性創新的多層次政策支持體系,著眼于為破壞性創新提供良好的法治環境,使政策支持更加規范,減少在位企業形成利益集團干擾政策制定、妨礙新進企業開展破壞性創新的情況發生。同時,專門法律的制訂也將增強新能源汽車產業在國民經濟體系中的地位,促進形成良好的產業生態,從而使破壞性創新的產生有健康的土壤與環境。
2. 調整妨礙破壞性創新的財政補貼政策
前文研究表明,財政補貼在我國現所運用的政策工具中占據過高的比例。財政補貼通過降低新能源汽車產品的購買成本,擴大新能源汽車廠商的市場空間,對于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創新具有積極的作用。但片面強調財政補貼將反而帶來諸多負面影響:一是造成不公平競爭,現有新能源汽車廠商(多也是傳統燃油汽車廠商)能夠通過依據產品發放補貼的政策獲取更多的資金支持,擠壓了新進入者的生存空間;二是鼓勵“投機取巧”,整車銷售越多、獲得的補貼越多的補貼政策,可能導致新能源汽車廠商將更多的精力用于進口零部件組裝整車以加速銷量增長套取補貼,反而抑制了創新;三是在國際貿易中可能面臨更多的爭端。現有政策工具中財政補貼政策運用過濫的局面必須盡快改變。
3. 注重非財稅的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在破壞性創新中的作用
非財稅的金融支持政策在特斯拉汽車公司的成長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種市場化的手段能有效降低政府在選擇財政補貼對象時信息不對稱的可能,同時也更有利于引入先進的管理方式、產業鏈合作伙伴等其他資源增強產業創新能力,也避免了貿易爭端的風險。根據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非財稅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匱乏的情況,應盡快建立起針對不同創新階段的金融政策工具箱,形成多元化的投融資渠道,以應對企業不同發展階段的資金需求,特別是促進融資相對困難、但又是破壞性創新主體的新興企業的發展。
4. 盡快完成向“需求拉動型”政策思路的轉變
“需求拉動”是破壞性創新形成的根本動力,也是美國之所以產生特斯拉的重要經驗。應當進一步加強對政府采購政策工具的運用,發揮政府采購對企業技術創新的拉動效應。選擇政府采購激勵效率最高的環節——產業和產品發展周期的早期階段進行重點支持,并根據其市場成熟度及時調整支持力度。需求拉動不能僅僅依賴財政補貼和稅收減免,也應根據實際情況,下決心破除GDP至上和利益集團的桎梏,增加傳統燃油汽車的使用成本,倒逼新能源汽車市場空間的擴大,從而刺激破壞性創新的產生。
5. 其他建議
以上四條建議是立足于本研究所做的工作之上,根據前文推演得出的結論。新能源汽車產業破壞性創新的政策支持是一個系統的解決方案,本文研究過程中發現、但囿于篇幅未能展開進行深入探討的內容還包括如下三點。
(1)加強新能源汽車領域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我國目前尚未出臺任何與新能源汽車領域知識產權保護有關的政策。知識產權保護力度關系到創新者的積極性,對于破壞性創新而言尤為重要。通常,破壞性創新的主體是市場的新進入者,和在位企業相比,他們沒有雄厚的資金、人力、經驗耗費在知識產權爭端中,但相關創新成果是其賴以生存發展的核心競爭力。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關系到企業破壞性創新的積極性,較低的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反而是縱容和鼓勵模仿性創新、維持性創新,對破壞性創新而言具有負面效果。
(2)研究促進新能源汽車產業開拓海外市場的政策支持方案。我國目前在促進新能源汽車產業開拓海外市場的政策支持方面力度不夠。既往經驗表明,在手機、汽車等領域,我國企業均有通過先海外再國內、從低端向上延升從而做大做強的破壞性創新的例子,海外市場對于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的重要意義不容忽視。同時,海外市場的新能源汽車領域很多仍處于空白或低競爭水平上,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力量的及早介入有助于取得先機。
endprint
(3)加強對民眾節能環保意識的宣傳教育。前文多次論述到需求是破壞性創新的根本動力,而新能源汽車產業需求的擴大,民眾節能環保意識是重要影響因素。總體看我國民眾節能環保意識較為薄弱,低碳減排在消費者購買行為當中的影響因素占比較低。通過宣傳教育政策促進全社會節能環保意識的覺醒和提高,有助于刺激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市場需求與技術潛力之間的進一步互動,有利于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破壞性創新成果的出現。
[參考文獻][1] Alan Pilkington and Romano Dyerson. Innovation in disruptive regulatory environments A patent study of electric vehicle techn-ology development[J]. European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06(1).
[2] Birgitta Sandberg. Creating the Market for Disruptive Innovation: Market Reactiveness at the Launch Stage[J]. Journal of Targeting,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for Marketing, 2002(2).
[3] Brian Leavy. A system for innovating business model for breakaway growth[J]. Strategy & Leadership, 2010(6).
[4] Clark Gilbert and Joseph L Bower. Disruptive change: when trying harder is part of the problem[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02(5).
[5] Constantinos D Charitou and Constantinos C Markides. Response to Disruptive Strategic Innovation[J]. 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2003(4).
[6] Marnix Assink. Inhibitors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 capability a con-ceptual model[J]. European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06(2).
[7] Min Lin,Yi Wang and Guisheng WU. Regional strategies for devel-oping emerging industrie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in China[J]. Journ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3(1).
[8] Pete Thomond, Torsten Herzberg and Fiona Lettice, Disruptive Innovation: Removing the Innovators'Dilemma[A]. British Academy of Management, 2003 Conference Proceedings.
[9] Steven T Walsh, Bruce A Kirchhoff and Scott Newbert. Differenti-ating Market Strategies for Disruptive Technologies[J]. IEEE Tran-sc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2002(11).
[10] T. J. Foxon, R. Gross, A. Chase, J. Howes, A. Arnall, D. Anderson. UK innovation systems for new and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ies: driver, barriers and systems failures[J]. Energy Policy, 2005(33).
[11] Yong Zhang, Yifeng Yu and Bai Zou. Analyzing public awareness and acceptance of alternative fuel vehicles in China: The case of EV[J]. Energy Policy, 2011(39).
[12] William Eggers,Laura Baker,Ruben Gonzalez and Audrey Vaughn. Disruptive innovation: a new model for public sector services[J]. Strategy & Leadership, 2012(3).
[13] 白勝.Christensen破壞性創新理論的邏輯演進[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2(13).
[14] 陳勁,王飛絨.創新政策:多國比較和發展框架[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
[15] 陳向東,胡萍.技術創新政策特點和效應的國際比較[J].中國科技論壇,2003.
[16] 陳衍泰,王露嘉,汪沁,歐忠輝.基于二階段的新能源汽車產業支持政策評價[J].科研管理,2013(12).
[17] 陳振明.政府工具研究與政府管理方式改進[J].中國行政管理,2004(6).
[18] 丁常文.破壞性技術創新研究[D].南京:東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19] 傅家驥.技術創新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
[20] 高銘澤.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研究[D].長春: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21] 顧瑞蘭.促進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的財稅政策研究[D].北京: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2013.
[22] 韓懷玉.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的國際比較研究[D].西安:陜西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23] 克萊頓·克里斯滕森.創新者的窘境[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24] 克萊頓·克里斯滕森,邁克爾·雷納.困境與出路[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25] 柳卸林.技術創新經濟學[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3.
[26] 繆小明,王海嘯.基于破壞性創新視角的新能源汽車發展研究[J].情報雜志,2013(2).
[27] 施麗萍.基于內容分析法的中國科技創新政策研究[D].杭州:浙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28] 宋建元.成熟型大企業開展破壞性創新的機理與途徑研究[D]. 杭州: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
[29] 蘇啟林.破壞性創新、技術跨越與中國產業成長[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
[30] 蘇英.創新政策理論基礎的演變及啟示[J].科技創新導報,2010(33).
[31] 田紅云.破壞性創新與我國制造業國際競爭優勢的構建[D].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
[32] 邢懷斌,蘇竣.均衡與演化框架下的技術政策比較[J].科學學研究,2004(22).
[33] 王春法.技術創新政策:理論基礎與工具選擇[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
[34] 聞媛.技術創I型政策分析與工具選擇[J].科技管理研究,2009(8).
[35] 襲希.知識密集型產業技術創新演化機理及相關政策研究[D]. 哈爾濱:哈爾濱工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
[36] 楊雅南,鐘書華.政策評價邏輯模型范式變遷[J].科學學研究,2013(5).
[37] 葉楠,周梅華.新能源汽車采用的影響因素分析及推進策略[J].統計與決策,2012(18).
[38] 袁健紅,張亮.基于破壞性創新視角的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路徑研究[J].中國科技論壇,2010(8).
[39] 張長令,王麗萍.低速電動汽車是破壞性創新嗎[J].中國科技論壇,2013(3).
[40] 張雅嫻,蘇竣.技術創新政策工具及其在我國軟件產業中的應用[J].科研管理,2007(25).
[41] 趙筱媛,蘇竣.基于政策工具視角的公共科技政策分析框架研究[J].科學學研究,2007(1).
[42] 鄭代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高新技術產業政策研究——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D].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
[43] 仲為國,彭紀生,孫文祥.科技政策定量研究探討[J].戰略研究,2008(7).
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