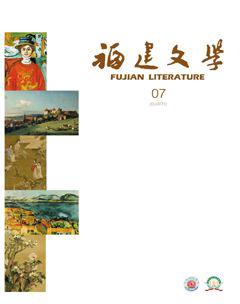普魯斯特的世界
陳朵拉
讀完《追憶似水年華》竟然有種長吁一氣的感覺,就像經過一場長途跋涉,沿途風景固然醉人,卻還是希望早日到達終點。從15年前擁有這套書,到如今讀完它,這么漫長的時光過去了。為著“追憶似水年華”這樣富有詩意的書名所蠱惑,這部書一直在內心占據著極其重要的位置。閨蜜為此笑我是個長情的人。中間的閱讀過程卻是幾經廢止,據說普魯斯特的弟弟曾笑言:閱讀《追憶似水年華》要么得摔斷了腿,要么得生病在家,否則哪來的那么多時間去閱讀這部世界上迄今為止最長的小說呢?此話固然是玩笑,但是《追憶似水年華》自是需要不同一般的閱讀條件。這兩年,于我,似乎是恰當的閱讀時機了,許是我亦開始無可救藥地眷戀起那些逝去的歲月,許是當年的浮躁漸漸地為內心的沉靜所取代。
進入普魯斯特的世界是件費神的事,仿佛要經過一個曲折昏暗的狹長狹長的通道,為此,你要有足夠的耐力忍受這個敏感到幾近神經質的人的喋喋不休和反復無常。在《追憶似水年華》中,普魯斯特極盡他回環往復、細致入微、委婉曲折的描寫特點,開卷回憶童年時期睡前索要媽媽的一個吻,竟可長篇累牘幾十頁,以至于有出版商看得昏昏欲睡而與這部驚世之作失之交臂。怠惰如我,我常想如若我不預先知道《追憶似水年華》久負的盛名,只怕亦是沒有足夠的眼力和勇氣去進行這樣一場心靈的深度游。
你只有緊緊跟隨著普魯斯特的筆觸,沉溺于自身,才能最終步入這個用回憶和文字構筑起來的無與倫比的圣殿。在這里,你將看到普魯斯特宛如一個魔法師,突破了與生俱來的肉體的缺憾,用他穿透一切的目光慢慢地使潛藏在生活表層下的另外一個世界完美地浮現出來,這是帕慕克所言的比第一世界更加真實的第二世界。在甜蜜與感傷的回憶中,普魯斯特看到平淡無奇的生活表象下暗流洶涌的生存真相,并用他精美絕倫的文字將之呈現在讀者的面前。普魯斯特說:“真正的藝術,其偉大便在于重新找到、重新把握現實,在于使我們認識這個離我們的所見所聞遠遠的現實。”
普魯斯特擁有濃重的時間感。無處不在的時間意識開啟了普魯斯特的世界,當然,這個世界最后亦由他關閉。因為有太多的事情沒有做,有太多的遺憾沒有彌補,所以總以為自己還很年輕,所以總不想老去。可是,當初充滿青春活力的女子轉眼就“白發蒼蒼、拱肩縮背成了個兇狠相的小老太婆”。時間在人的軀體上刻下深深的灰色軌跡,普魯斯特不忍正視生命衰老的速度,他自以為參加了一個化妝舞會,每個人只是將自己化成老人登臺演出而已。他終究還是從別人的時光流逝中看到了自己的似水年華,因而大驚失色。個人的年華逝如流水,但是宇宙的時間卻是綿綿渺渺,永不隔絕。人有多強烈的超時間的愿望,他遭遇不堪一擊的個人時間時就有多慘痛。
普魯斯特說他的書只是為讀者提供閱讀自己的方法,他只想知道讀者在他們自己身上讀到的是不是就是他寫下的那些話。怎么不是?我們有多少次在午夜夢回的時候被來自心靈深處的不安所籠罩,在迷茫中所有世事幻如云煙,唯有永不停歇向前流淌的時間之流猶如一道強光橫亙在黑暗的世界里。這種恐懼不正是源自于悄然消逝的時間永遠無法挽回?
個體時間的有限性被死亡以極端的形式展示出來。隨著死亡的來臨,“此在”不復存在,由此帶給人類的是輕浮到難以承受的虛無感。小說中,馬塞爾先后經歷外祖母、女友阿爾貝蒂娜、好友德·圣盧等人的死亡,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至親的死亡曾經帶來的錐心之痛逐漸淡化,最后只成了幾個被偶然憶及的瞬間。一輩子的光陰竟至于不留痕跡,“輕輕地我走了,正如我輕輕地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云彩”的詩人式的離愁在生存論意義上是有更沉重的意味。
人類因為害怕死亡之后的虛無,將希望可以不朽的靈魂安頓在了彼岸世界。然而,在現代社會,彼岸世界土崩瓦解,殘留的些許宗教余溫不足以慰藉人世的缺憾。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講述了一個古老的傳說:“昔日米達斯王曾很久在林中尋找酒神的伴侶,聰明的西列諾斯,但沒有找到。當西列諾斯終于落到他手上時,王就問他:對于人絕好絕妙的是什么呢?這位神靈呆若木雞,一言不發,等到王強逼他,他終于在洪亮的笑聲中說出這樣的話:朝生暮死的可憐蟲,無常與憂患的兒子,你為什么強逼我說出你最好是不要聽的話呢?世間絕好的東西是你永遠得不到的,——那就是不要降生,不要存在,成為烏有。但是,對于你次好的是——早死。”
世間絕好的東西是不要降生,不要存在!存在只是烏有。失去了宗教神性光輝庇佑的現代人除了墮入無休無止的虛無與荒誕之中,是否真的別無出路?追尋意義是抵抗虛無的唯一途徑。存在主義認為人雖然是被拋到世上的,但是人有選擇自己本質的自由。不要神靈,拯救人類的責任重新回歸人類自身。海德格爾說要“向死而在”,唯有“向死而在”才能從沉淪的在世中返歸本真的存在。
誠然,常人生而在世,并不總能意識到死亡的切近,死亡永遠是他者的經驗。但是,對于普魯斯特而言,如影隨形的疾病時刻提醒他死亡隨時來臨,他被困足其中的斗室關閉了他年輕時無窮向往的社交界,卻向他開啟了一個澄明的心靈之境。可以假設,如若不是他的疾病,他可能會成為另一個花花公子斯萬沉淪于平庸的常人的世界。但是,他禁足在暗室之中,思考時間、生命、死亡這些永恒的哲學命題,最終選擇文學作為拯救靈魂、超越死亡的途徑。他相信,天才是通過他們的作品來顯示的。
企圖以藝術對抗人世的虛無、拯救殘缺的人生,紛繁復雜的現代主義流派展現了這樣一個共同的形而上傾向。藝術的意義正在于帶領人們越過人生的繁瑣與平庸,從中發現存在的詩意美,這亦是人生的意義所在。如若沒有藝術,我們將用什么來彌補現世的種種缺憾;如若沒有藝術,生命于普魯斯特將果真如他自己所言:“如果命運讓我多活一百年,而且不帶殘疾,它也只是在一個縱向的生命里增添連續延長的部分,而人們甚至看不出再延長這種生命有何意義。”
逝如流水的現世時間遵循的是直線向前的法則,但是,普魯斯特的文學世界,在對似水年華的追憶之中,時光之流實現逆轉,生命在回環往復的輪回中到達永恒。或許對許多人而言,回憶總隱喻著衰老,人們更愿意對回憶掉轉頭以看似更加樂觀的心態面向著未來,從來沒有人像普魯斯特那樣以如此虔誠的心追憶似水年華,這個偉大的世界注定首先屬于普魯斯特。
回憶是要再一次印證我們生命的足跡,讓我們在永恒回歸的目光中收獲關于存在的至高無上的幸福。普魯斯特編織著密密麻麻的回憶之網,他沿著逆轉的時光之流固執地回去尋找停留在原地的那些人和事,為它們拂去歷史的塵埃,重新賦予它們鮮活的生命。有時,在夢境中,過往的那些人和事聽到他心靈的召喚越過萬水千山齊聚當下,逝去的時光死而復活。當然,更多的時候是,“它們佇留在自己的位置上,佇留在一系列被遺忘的日子中,等待著,一次突如其來的巧合不容置辯地使它們脫穎而出。”瑪德萊娜點心之于貢布雷,一高一低的臺階之于威尼斯,刀叉碰撞的聲音、漿洗的餐布之于巴爾貝克,就是這樣一次次突如其來的巧合。在這突如其來的瞬間,回憶之門緩緩打開,往昔的世界在迷蒙不清的霧氣中慢慢升騰而起。普魯斯特將這樣的時刻稱為至福。
其實,我們的一生也有無數的機會碰到這樣的巧合。還記得,曾經,在夏日的午后,看著遠山郁郁蔥蔥的樹林,一陣微風拂過耳際,我的內心總會有一種莫名的悸動。我亦曾如普魯斯特追隨瑪德萊娜點心引起的內心的震動那樣,試圖仔細探究這種悸動緣何而起,我依稀辨認出微風中的遠山樹林里隱藏著我童年時期在外婆家度過的美好時光,待至我想進一步看清,這個似乎將要顯形的世界卻頓然隨風消散。這種感覺稍縱即逝,如今,我已久不能有這種悸動的感覺了,我想我將永遠不能像普魯斯特那樣緊緊抓住這個瞬間細細回味,找回我那逝去的歲月,從而將其幻化成一個精彩紛呈的世界。
在普魯斯特往回看的眼光中,決然沒有張愛玲“隔著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帶點凄涼”的荒蕪心境。他的回憶,雖然略帶感傷,卻是隔離一切世俗紛紛擾擾的純凈的詩的世界。
普魯斯特的回憶關注的不是事實本身,而是注視事實的方式,而是找到一種達成生活本質的東西。他認為現實主義自稱忠實于真實,實際上卻因此而離真實最遠。相較于被理性與意愿梳理過的記憶之河,普魯斯特更愿意從非理性、非意愿的遺忘之川中尋回往昔,他希冀“返回隱藏著確實存在過卻又為我們所不知的事物的深處”。理性與意愿終究因為太多的目的性不免有韋伯所言之“理性的牢籠”的意味,唯有非理性與非意愿摒棄了目的性從而更契合審美的無目的的目的性,因此也更接近生命的本真的存在。
對于才智與心靈,普魯斯特總是更青睞后者。經過才智條分縷析的生活,固然更有智慧,可是總顯得太干澀而不圓潤。用心靈把握的生活,是豐滿的,是囊括一切彼此關聯的人和事的嚴密的網,人世間所有的紛繁復雜盡在其中。
普魯斯特記下了他的愛,他的傷感,他的痛苦,他的嫉妒,他的追求,他的失落,他的幸與不幸,是要有多么細膩委婉和洞察一切的心靈才能如此纖毫畢現地呈現出這樣真實的世界。或許才智和心靈從來沒有被分開,就像梅塞格利絲那邊和蓋爾芒特那邊最后被發現由一條小路連接成一個世界。這,就是普魯斯特的世界,一個圓滿的世界,一個用小說的形式、散文化的語言建構的詩的世界。
責任編輯賈秀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