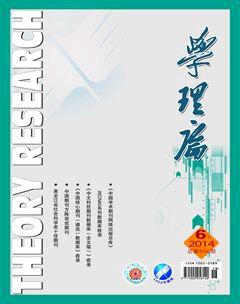全球變暖背景下的中國氣候外交
沈玲玲
摘 要:全球氣候變暖已經成為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重大問題,它不但影響自然生態系統和人類的生產生活,而且引發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在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下,以氣候為主題的外交活動也隨之展開。在全球變暖這一背景下,分析了目前中國氣候外交的行動,存在的問題,并對進一步推動中國氣候外交提出了一些思考與對策。
關鍵詞:全球變暖;氣候外交;氣候合作;中國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18-0017-02
全球變暖已是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氣候變化對人類的威脅已經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全球氣候變化治理是涉及多個領域的復雜問題,它的實質是能源環境競爭和全球治理失效的雙重聚焦[1]125。近年來,圍繞全球氣候問題的國際交鋒愈演愈烈,氣候問題政治化趨勢也日趨明顯。氣候外交開始走上前臺,成為各國外交的重要內容之一。
一、中國氣候外交行動
氣候外交是外交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狹義的氣候外交是指“主權國家通過外交部門或環境部門等代表國家的機關和個人,采用交涉、談判以及其他和平方式來解決涉及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外交活動”。廣義的氣候外交則是指“一切出于全球氣候‘良治的目的而進行的國際氣候博弈與合作活動”[2],其行為主體既包括國家外交部門和環境部門,也包括一些政府間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社會團體、公司等。氣候外交主要有公共性、多層次性、主體多元性等特點。隨著國際社會對全球變暖問題的日益重視,國際氣候制度的逐步完善,中國的氣候外交也日益頻繁和活躍起來。2007年6月,國務院成立了由溫家寶任組長的國家應對氣候變化領導小組,隨后外交部成立了楊潔篪任組長的應對氣候變化對外工作領導小組。自1989年以來,中國已經加入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等50多項國際環境條約,已經與周邊國家和發達國家展開了諸多的氣候治理項目[3]。總體看來,中國目前的氣候外交主要包括以下兩部分:
(一)積極參與國際氣候談判
參與國際氣候談判是全球氣候外交的一個重要表現形式。在1972年的聯合國人類環境大會上,氣候變化問題首次成為國際談判的議題。1990年,第45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成立了由聯合國全體成員國參加的“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政府間談判委員會”,國際氣候變化談判的進程從此正式啟動。中國從一開始就積極參與國際氣候談判,包括《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的談判以及其他涉及氣候變化領域的談判。具體表現在,中國成立了由來自能源部、外交部、國家環保局等部門的成員組成的氣候談判代表團,積極參加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的歷次籌委會。從里約熱內盧到京都,從哥本哈根到德班,再到最近一次的華沙世界氣候大會,中國代表團都廣泛參與各個級別和層次的磋商與談判。近年來,中國在推動減緩氣候變化的國際進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作用,日益成為國際氣候判的核心成員。在參加的歷次氣候談判大會上,中國談判代表團都竭力維護本國的國家利益和國際形象,并聯合發展中國家維護其整體利益。例如,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指出發達國家的歷史責任;強調人均碳排放量,注重公平與責任。后金融危機時代,隨著總體實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升,中國在國際氣候談判上表現得更加主動與開放。2013年11月,世界氣候大會在波蘭首都華沙召開,中國、印度、巴西和南非組成的“基礎四國”提出了促成大會成功的四點建議。其中包括要加大落實以往承諾的力度,盡快開啟德班平臺的談判,要在減排、適應、資金、技術和透明度等關鍵問題上取得平衡結果,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新協議應有約束力等,并表示“基礎四國”將為此共同做出努力[4]。在華沙氣候大會上,中國代表團為本次會議的成功,在多邊機制的有效性、靈活性方面做出了最大努力。
(二)開展多層次性的氣候外交
首先,中國開展全球層次的多邊氣候外交,積極參與國際氣候機制的構建。主要包括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的締約與“巴厘島路線圖”的達成;研究探討基于各種不同公平原則的碳排放權;參加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活動并參與制定關于氣候變化的國際性規則;與世界自然基金會、綠色和平組織、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和機構建立并發展了在資金、技術與信息等方面的氣候合作。此外,中國還參加“主要經濟體能源安全與氣候變化會議”與“碳收集領導人論壇”,“八國集團峰會”等全球性會議,利用這些會議和場合闡明自身立場,討論氣候變化的應對措施,構建國際氣候治理機制。
其次,中國開展區域層次的氣候外交和雙邊國家間的氣候外交,積極參與國家間的氣候治理與合作。首先,中國開展APEC峰會和東亞峰會框架下的氣候外交。在2007年APEC峰會上,胡錦濤提出了包括“合作應對,可持續發展,堅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主導地位,堅持科技創新”[5]的中國參與氣候變化談判四項原則。2010年3月,“東亞峰會氣候變化適應能力建設專家研討會”在北京召開,中國作為東道主提出東亞峰會成員國應重視和加強氣候變化適應能力建設,要堅持依靠科學技術提高適應能力,有效加強東亞區域內氣候合作。其次,中國還積極開展雙邊氣候外交活動。一方面,中國與美國、日本、歐盟等發達國家與地區開展氣候技術領域內的合作,積極引入減排技術、污染治理技術。另一方面,中國與巴西、馬來西亞、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氣候制度談判中合作協商,互相協調各自氣候政策,共同站在發展中國家的角度與發達國家加強氣候治理領域內的技術合作。
二、當前中國氣候外交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第一,中國的氣候外交面臨著保障發展空間和履行減排義務的挑戰。作為一個經濟高速增長的新興大國,高需求的能源消耗必然造成溫室氣體排放的居高不下,再加上以第二產業為主體,資源密集型的轉型經濟結構,中國的碳排放量屢增不減。一方面,在國際舞臺上,中國一直以負責任的大國自居,恪守減排承諾、嚴格執行規定的碳排放量是應有之義;但另一方面,中國也要保障自身的發展權。倘若只是單純地為了履行與自身不符的減排義務而壓縮國內的工業發展,那必將對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嚴重的沖擊。可以說,中國在現階段正面臨著保障國內發展空間和履行國際減排義務的矛盾困境,如何在保障國家發展的基礎上推動世界氣候新體制的建立是中國氣候外交需要完成的艱巨任務。
第二,后京都時代氣候談判壓力越來越大,中國在國際氣候談判上的形象有待改善。隨著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量的不斷增加,西方國家總是力圖將發展中國家納入強制性的減排框架。而中國一直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站在發展中國家的角度強調“有區別”,這一系列舉動直接導致某些西方國家誤讀了中國的氣候政策,甚至把中國看成國際氣候談判的強硬者和阻撓者。英國學者巴里·布贊指出,西方國家對中國在哥本哈根氣候談判的總體印象是負面的[6]。再加上國際媒體以及公眾溝通能力和經驗的不足,中國在氣候治理上所采取的一些重大行動往往被國際社會忽視。
第三,國際舞臺上出現了“中國氣候威脅論”的論調。由于目前中國大部分污染排放居高不下,各類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占全球份額較大,西方國家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對全球氣候與環境構成了嚴重的威脅。他們把控制氣候變化、發展清潔能源與國家安全直接掛鉤,并且大肆渲染“中國氣候威脅論”、“中國責任論”,更有甚者直接宣稱全球氣候變暖是中國這樣的新興大國所造成的。
三、推動中國氣候外交的建議與對策
第一,積極參與國際氣候談判大會,嚴格履行國際氣候公約。高度重視并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氣候談判大會,在氣候談判議程設定、議題提出、氣候博弈等方面全面積極進取;提出中國的碳減排方案,占據制高點。尤其要積極參與氣候變化方面國際合作規則的制定[7]。對于目前已經簽訂的國際氣候公約,中國應樹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控制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嚴格履行國際氣候公約。為了加強履行公約的能力建設,必要時還要加大國外先進環保技術和資金的引進。
第二,加強氣候外交宣傳,建立中國應對氣候變化進程的宣傳機制。定期發布中國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的政策措施及其取得的成效,向國內外宣傳中國的氣候政策,溫室氣體減緩排放情況,人均排放和人均累積排放等,使世界正確認識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1]268,從而客觀評價中國為氣候治理采取的一系列行動。與此同時,還應動員社會力量,積極發揮民間社會團體和非政府組織的作用,加強社會公民團體之間的國際交流,促成更多的群體參與緩解全球變暖的行動。
第三,全面貫徹科學發展理念,落實節能減排和轉變發展方式。中國應對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不僅是出于氣候外交上國際社會輿論的壓力,更是國內科學、可持續發展的需要,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首先,要在戰略層面上改變過分重視能源安全、忽略氣候變化和環境問題的政策取向,將氣候安全和生態安全納入到國家安全與長期發展戰略之中。同時要毫不猶豫地加大對氣候環保領域的資金投入,通過法律法規,稅收政策等一系列手段實現節能減排。低碳經濟和綠色發展是世界也是中國未來發展的方向和出路,只有轉變發展方式,并且堅持不懈地貫徹落實,才能在高新技術和低碳經濟領域占據制高點,才能在氣候外交的舞臺上擁有更多的籌碼,變被動為主動。
參考文獻:
[1]楊潔篪.世界氣候外交和中國的應對[M].北京:時事出版社,2009.
[2]馬建英.全球氣候外交的興起[J].外交評論,2009(6).
[3]張海濱.環境與國際關系:全球環境問題的理性思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華沙氣候大會達成協議后閉幕[EB/OL].新華網,[2013-11-24].
[5]胡錦濤在悉尼APEC會議上對氣候變化提出建設性意見[EB/OL].新華社中文新聞,[2007-07-28].
[6]甘鈞先,余瀟楓.全球氣候外交論析[J].當代亞太,2010(5).
[7]胡宗山.政治學視角下的國際氣候合作與中國氣候外交新政策[J].社會主義研究,2010(5).
[8]魯毅.外交學概論[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
[9]張磊.國際氣候政治的中國困境:一種微觀層次的梳理[J].教學與研究,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