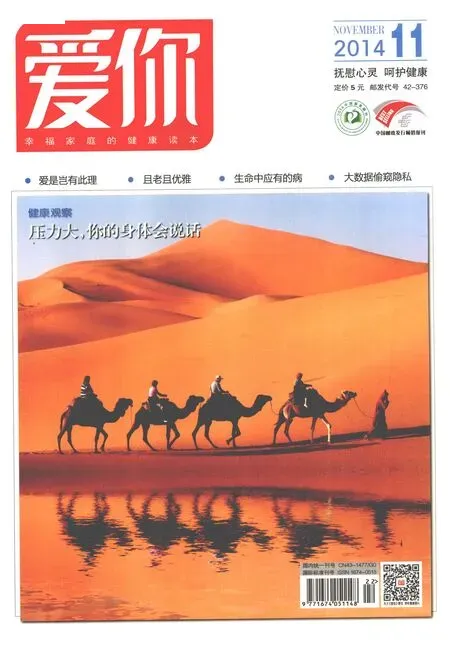曾與她琴瑟和鳴
◎ 季羨林
曾與她琴瑟和鳴
◎ 季羨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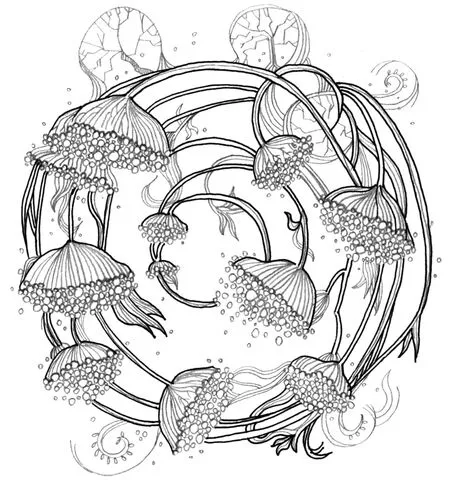
我是季家的獨根獨苗,身上負有傳宗接代的重大任務(wù),所以十八歲就結(jié)了婚。妻子德華長我四歲,對我們家來說,她一輩子勤勤懇懇,有時候還含辛茹苦。上有公婆,下有稚子幼女,丈夫十幾年不在家,公公極難侍候,家里又窮。這些年,她究竟受了多少苦,她只是偶爾對我流露一點,我實在說不清楚。
德華天資不是太高,只念過小學,大概能認千八百字。她沒有給我寫過一封信,因為她根本拿不起筆來。到了晚年,連早年能認的千八百字也大都還給了老師,剩下的不太多了。因此,她對我一輩子搞的這套玩意兒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東西,有什么意義。她也似乎從來沒想過要知道。在這方面,我們倆毫無共同的語言。
雖然在文化上她不能和我琴瑟和鳴,但在道德和賢淑方面,她卻是超一流的,也讓我極為欣賞。上對公婆,她真正盡到了孝道;下對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應(yīng)做的一切;中對丈夫,她絕對忠誠,絕對愛護。
她是一個極為難得的孝順媳婦、賢妻良母。她對待任何人都忠厚誠懇,從來沒有說過半句閑話,她也不會撒謊,一輩子沒有說過半句謊話。
1962 年,嬸母同德華從濟南搬到北京來。過單身生活數(shù)十年的我,當時總算是有了一個家。
這是德華一生的黃金時期,也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時候。我們在家里和睦相處,你尊我讓,從來沒有吵過嘴。有時候家人朋友團聚,烹飪往往由她們二人主廚,食前方丈,杯盤滿桌。飯菜上桌,眾人狼吞虎咽,她們倆卻往往是坐在一旁,笑瞇瞇地看著我們吃,臉上流露出愉悅的神情。對這樣的家庭,一切贊譽之詞都是無用的,都會黯然失色。
我活到了八十多,參透了人生真諦。人生無常,無法抗御,在極端的快樂中,我的心頭往往會閃過一絲暗影: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我們家這一出十分美滿的戲,早晚會有散場的時候。果然,嬸母先走了,去年德華又走了。然而她也已活過米壽(88歲),與我相濡以沫,夫妻相諧,相信可以瞑目了。
我和她的“重逢之日”,想來也不會太遠。
(摘自《當時只道是尋常》重慶出版社 圖/樂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