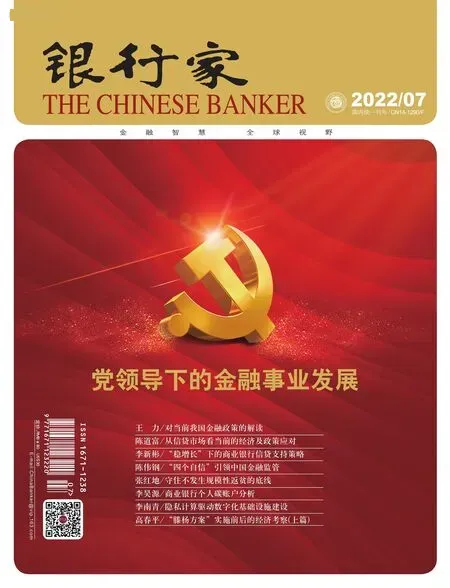“微文化”沖擊波
高續(xù)增
我從最近召開(kāi)的“全國(guó)深度報(bào)道研討會(huì)”發(fā)布的有關(guān)文件得知,傳統(tǒng)媒體的從業(yè)者們感受到了嚴(yán)重的危機(jī)。其中最讓我吃驚的消息是上海解放日?qǐng)?bào)報(bào)業(yè)集團(tuán)所屬的《新聞晚報(bào)》已于今年年初停刊。有人分析它的倒臺(tái)是由于競(jìng)爭(zhēng)不過(guò)另一個(gè)報(bào)業(yè)巨頭——上海文匯新民報(bào)業(yè)集團(tuán)下屬的《新民晚報(bào)》才自我消失的,而我卻認(rèn)為還有比上述原因更重要的其他原因造成了這一結(jié)果,那就是遇上了不止一座“冰山”,其中最大的一座就是近年來(lái)與文化迅速結(jié)合成一體的IT新科技,它的泛濫和蔓延就催生出了“微文化”。
一個(gè)有兩千多萬(wàn)人口的超級(jí)大城市里,相當(dāng)于歐洲一個(gè)中等國(guó)家的人口,不會(huì)連兩家晚報(bào)都容不下。前幾年(大約是2008年前后),每到臨近年底,我都會(huì)注意到有報(bào)刊打著“完成黨報(bào)的征訂任務(wù)”的旗號(hào)絞盡腦汁四處活動(dòng),結(jié)果怎樣,局外人不怎么關(guān)心。反正那個(gè)時(shí)候有大量國(guó)企和事業(yè)單位會(huì)響應(yīng)號(hào)召撥出專(zhuān)款訂閱黨報(bào),這是那些以宣傳為能事的報(bào)刊的殺手锏和看家本領(lǐng)。今天看來(lái)不太靈了。如果說(shuō)那時(shí)是因?yàn)辄h刊受到了市場(chǎng)化運(yùn)作的新興媒體的沖擊,那么現(xiàn)在出現(xiàn)這樣慘烈的局面,則是由于受到了微文化的重創(chuàng)。
我思考這個(gè)問(wèn)題時(shí),頭腦中產(chǎn)生“微文化”這個(gè)詞的,沒(méi)想到上網(wǎng)一查,原來(lái)早有人搶了先。更讓我想不到的是,創(chuàng)造出這個(gè)新詞的人不是學(xué)者、大師之類(lèi)的文化人,而是一個(gè)搖滾樂(lè)的主唱,那是1997年的事情,不過(guò)那位主唱所謂的“微文化”,與我所說(shuō)的微文化的內(nèi)涵不一樣,畢竟17年前世界上根本沒(méi)有如今發(fā)達(dá)的網(wǎng)絡(luò)文化,更沒(méi)有今天我所謂的微文化的實(shí)體和內(nèi)涵。他的“微文化”所指的僅僅是“草根文化”的文藝版而已。
我所謂的微文化應(yīng)當(dāng)這樣被定義:相對(duì)于舊的正統(tǒng)文化形式(它們便于與自上而下貫徹執(zhí)行的宣傳工作和體制內(nèi)機(jī)構(gòu)下達(dá)的行政任務(wù)相配合),那些借助于QQ、微博、微信等高科技的手段和設(shè)施,能把近半數(shù)的識(shí)字人調(diào)動(dòng)起來(lái),并參加進(jìn)去的文化形式,這是我下面所議論的“微文化。”
微文化有幾個(gè)特點(diǎn),其中一個(gè)是“自由散漫”,一旦傳布開(kāi)來(lái),就跟野火一樣沒(méi)邊沒(méi)沿,沒(méi)時(shí)沒(méi)點(diǎn),甚至不用經(jīng)營(yíng)場(chǎng)合、隨便一個(gè)人、幾個(gè)人就能玩起來(lái)。因此,弄好了,這個(gè)微文化幾乎不用政府撥款就能將文化輕易地普及到大眾群體中,讓大眾在享受中受到文化生活的熏染,傳布“正能量”;弄得不好,由于缺乏有效監(jiān)管,就會(huì)被階級(jí)敵人所利用,成為薛蠻子、“立二拆四”那樣的野心家陰謀家邀買(mǎi)人心蠱惑大眾的宣傳工具,或者為傳銷(xiāo)組織騙錢(qián)提供方便。
QQ、微博的時(shí)髦,我都趕上了,卻很快就厭煩了,原因是必須占用當(dāng)時(shí)還屬于寶貴的在線資源,但是隨著無(wú)線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的普及和發(fā)展,微信已經(jīng)不需要太多的投入就能讓你成為這個(gè)新天地的一員,開(kāi)始享受前所未有的樂(lè)趣、收獲難以預(yù)測(cè)的交流成果。四個(gè)多月來(lái),我用這個(gè)溝通工具聯(lián)絡(luò)了許多久未聯(lián)系的老朋友,交上了本地的外地的新朋友,不用有人召集、不用費(fèi)力地事先商量約定、不用花費(fèi)太多的時(shí)間就交流思想,相互間傳遞最有價(jià)值的信息和思想,互相推薦好書(shū)好文章,想得到真正有深度的學(xué)術(shù)文章和時(shí)政報(bào)告也不用到圖書(shū)館去了,對(duì)我的日常工作來(lái)說(shuō),微信真是個(gè)好幫手。
微文化的“快餐式”這一特點(diǎn),是尤其應(yīng)當(dāng)引起注意的。交流手段的極速升級(jí)換代,讓文化傳布變得很輕松,交流工具也不再稀缺,不用說(shuō)畢昇時(shí)期,六十年前長(zhǎng)輩還有對(duì)后生“敬惜字紙”的告誡語(yǔ),那時(shí)連煙盒背面那樣大小的廢紙都要利用起來(lái),訂成小本本,練習(xí)寫(xiě)字或記事。傳布文化的困難,把社會(huì)人分成界線分明的兩大塊,于是社會(huì)因此而不可能協(xié)調(diào)融洽。而現(xiàn)在,想學(xué)文化,不用拜師,不用上學(xué)校,把上網(wǎng)的技能掌握了,就齊活了。當(dāng)然,現(xiàn)在學(xué)文化更大程度上是謀生或是將來(lái)向上攀爬,需要擠進(jìn)優(yōu)質(zhì)教育資源,其最優(yōu)先的考慮是索取文憑。這樣,微文化的最主要作用就成為有閑者的心靈雞湯,真正繁忙的公務(wù)員和“白骨精”們很少有迷戀此道的。
微文化帶給我們的是一種全新的交流方式,它必然會(huì)對(duì)人類(lèi)的社會(huì)生活產(chǎn)生廣泛的影響。
造紙術(shù)和印刷術(shù)是中國(guó)人發(fā)明的,因此能讓中國(guó)人在很長(zhǎng)的歷史時(shí)期保有文化自信,也因?yàn)閾碛惺澜缟献钬S富的紙媒歷史文獻(xiàn)而讓所有敬畏精神文明的民族和國(guó)家歆羨不已。但是,在世界進(jìn)入工業(yè)化時(shí)代以來(lái),中國(guó)的印刷科技一直落后于西方世界,最近30年雖然我們趕上不少,但是從總體上看,還是落后的。好在這最后一波的信息傳輸革命我們還是跟上了世界的腳步,這要感謝鄧小平在他最后能發(fā)揮作用的時(shí)候,果斷地截?cái)嗔烁鞣N歷史的和文化的糾葛,為中國(guó)的現(xiàn)代社會(huì)的建設(shè)打下了基礎(chǔ),才使得今天我們得以擁有世界上數(shù)量最多的電腦和最龐大的網(wǎng)絡(luò)受眾,在微文化一瞬間成為人類(lèi)最新的文化成果的時(shí)候,中國(guó)人沒(méi)有成為圈外的圍觀觀眾。
微文化帶給我們的是一種全新的信息交流方式,現(xiàn)在,借助于微文化的各種媒介,人們可以相隔萬(wàn)里實(shí)現(xiàn)瞬間的互動(dòng)交流,讓孟德?tīng)栠z憾終生的那種悲劇,再也不會(huì)發(fā)生在當(dāng)代了。
但是微文化的負(fù)面作用和影響同樣也不能忽視。
微文化會(huì)讓人們變得心浮氣躁,弄得不好,則難以被利用來(lái)提升民族整體的文化修養(yǎng)。社會(huì)上多如牛毛的各種各樣的文化速成班,充其量只能對(duì)文化普及起一個(gè)點(diǎn)到為止的作用,這些文化快餐很容易讓人們遠(yuǎn)離經(jīng)典,真正面壁苦讀的人大大地減少了。
于是就有真學(xué)者發(fā)出了擔(dān)憂:微文化這一“人與技術(shù)的共謀”會(huì)造成社會(huì)性的“群體孤獨(dú)癥”(語(yǔ)義出于美國(guó)女學(xué)者雪莉·特科爾的新著——《群體性孤獨(dú)》)。
她指出,由于科技的發(fā)展,尤其是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的普及,對(duì)人類(lèi)的影響已經(jīng)深入到人的個(gè)體感情和欲望的塑造,人與技術(shù)的關(guān)系正發(fā)生著驚人的變化,同時(shí)人際關(guān)系也發(fā)生了顯著的變化。
不是么,一家人在一起,不是交心,而是各自看電腦和手機(jī);朋友聚會(huì),不是敘舊,而是拼命刷新微博微信;課堂上,老師在講,學(xué)生在網(wǎng)上聊天;會(huì)議上領(lǐng)導(dǎo)在作報(bào)告,聽(tīng)眾在收發(fā)信息,這些僅僅是曾靖皓先生隨手拈來(lái)的微文化對(duì)傳統(tǒng)文化的小規(guī)模的“偷襲”的例證(《新京報(bào)》2014-6-7)。
電子書(shū)是微文化沖擊書(shū)刊市場(chǎng)的重要的方面軍。2013年亞馬遜kindle登陸中國(guó),帶動(dòng)各種形式的電子書(shū)鋪天蓋地般涌來(lái)。百道網(wǎng)CEO程三國(guó)最近接受采訪時(shí)表達(dá)出這樣一個(gè)觀點(diǎn),值得所有讀書(shū)人深思:在當(dāng)前蓬勃而喧囂的環(huán)境中,“選書(shū)”是讀者學(xué)習(xí)過(guò)程中最重要的一個(gè)環(huán)節(jié),有了電子書(shū),就成為讀者解決這個(gè)問(wèn)題的好幫手。
我深以為然。因?yàn)樵谥R(shí)爆炸的年代,書(shū)刊的數(shù)量泛濫,而人們讀書(shū)的時(shí)間反而在減少,這樣,精選精讀必然成為趨勢(shì)。現(xiàn)在,讀書(shū)的成本越來(lái)越從購(gòu)書(shū)款轉(zhuǎn)移到讀書(shū)所占用的時(shí)間了。
微文化方興未艾,不過(guò)人們千萬(wàn)不要駐足,以免在此文化工具迅速“變臉”的關(guān)鍵時(shí)刻,成為新品種的“文盲”。
微文化與紙媒之間的沖突不可避免地延伸到社會(huì)的方方面面,首當(dāng)其沖的是文化成果的所屬權(quán)問(wèn)題。
北京市字節(jié)跳動(dòng)科技有限公司CEO張一鳴在做足了融資方面的文章以后,卻陷入了版權(quán)泥淖,先后有《新京報(bào)》等5家紙媒大腕指控張一鳴開(kāi)發(fā)的“今日頭條”涉嫌侵犯了它們的權(quán)益。而張一鳴辯解說(shuō)“我們只做新聞的搬運(yùn)工”,把你們采訪來(lái)的新聞搬運(yùn)給想知道它們的受眾,這不能算作侵權(quán)。而現(xiàn)行的法律條文和以往的判例都不能成為這場(chǎng)爭(zhēng)吵的判別依據(jù),在這個(gè)全新的訴爭(zhēng)中以往那些“對(duì)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的保護(hù)”和“知識(shí)的再加工和傳布”之間的界限變得異常模糊。看來(lái),版權(quán)法領(lǐng)域也要在這股大潮的沖擊下好好地清醒清醒了。
在本文的寫(xiě)作過(guò)程中,我的朋友余效誠(chéng)先生的新著出版了,粗粗拜讀之后我驚嘆于這位默默無(wú)聞的耕耘者,是在做著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情”,他以自己豐富的教學(xué)經(jīng)歷和廣泛的社會(huì)科技實(shí)踐寫(xiě)成了《數(shù)字讀物論》,這是一部橫趟許多學(xué)科和領(lǐng)域的嚴(yán)謹(jǐn)而且體系完整的作品,本應(yīng)當(dāng)由一個(gè)不小的團(tuán)隊(duì)來(lái)共同完成的工程,卻由他一個(gè)人完成了。讓人扼腕的是,多家出版社根本認(rèn)識(shí)不到這本書(shū)的價(jià)值,向他提出的條件都是自費(fèi)出版。現(xiàn)在書(shū)已經(jīng)出來(lái)了,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méi)有書(shū)中所涉及到的哪個(gè)權(quán)威部門(mén)認(rèn)識(shí)到書(shū)中所建構(gòu)的內(nèi)容,近而規(guī)劃了他們那個(gè)部門(mén)今后的發(fā)展方向,或者是今后的工作要點(diǎn)。以我一個(gè)只擅長(zhǎng)于發(fā)議論的“隱士”的角度看,對(duì)我上述所說(shuō)的所有被微文化沖擊的領(lǐng)域,他幾乎都為它們做了“標(biāo)準(zhǔn)化式”規(guī)范,我無(wú)法精確地預(yù)測(cè)微文化將來(lái)的前程和勢(shì)頭,但是微文化一定會(huì)像余效誠(chéng)所預(yù)見(jiàn)的那樣,開(kāi)拓出一片新的文化天地,成為文化成果與科技成就相互融合的、內(nèi)部結(jié)構(gòu)和諧的系統(tǒng)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