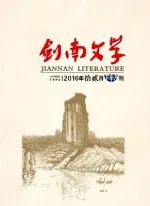獻給故鄉的頌詞(組詩)
故鄉一夜
風 吹來寂寞
五月的手指將夜色聚攏
將我包圍
靜 帶來疼痛
疼痛就寂寞
竹林變瘦了
庭院深深
喇叭花次第開放
無人來嗅
莫名其妙的惶惑
來自一處陰暗的角落
母親老了
咳嗽聲不再清脆
于是懷疑
時間的作梗
風在吹攏烏云
故鄉干旱了好久
天空就是一種誘惑
夜鳥 叫著孤單
童年越走越遠
于是懷疑
什么叫故鄉
在故鄉的懷抱睡覺
一驚一炸
已不甚安穩
聽院中的狗叫 聲聲喚黎明
明兒
去看看荒蕪的田塊
去看看清廋的包谷林
看看又能怎樣
故鄉 老母親們在堅守
她們的兒子和媳婦
在幾千公里之外
建設著別人的故鄉
太陽升起
太陽升起
霧霾散盡
大山高不出我的眼睛
一片青杠林
連著一片榿木樹林
就是無邊春色
那個時候
喜歡早起看太陽
看太陽就感知故鄉的溫暖
若干年后
太陽爬上山梁子
母親在父親墳前上香
我跟在母親之后
女兒跟在我之后
看太陽將整個村莊照耀
母親白發飄飄
臉頰清廋
但精神還好
太陽升起
總要落下
總有一天
我要成為故鄉的泥土和石頭
盼望太陽
永久照耀著我
讓我的靈魂還有溫度
雨一直下
那天丘陵 皺了一天的眉頭
雨一直下
我困在思念里
母親在忙
棉花地緊挨著父親的墳頭
她戴著斗笠
給棉花上廂
勞動一天也沒有休止
我在城市一角
電話里 盡是故鄉的雨聲
電話是女兒買給她婆婆的
母親隨時都沒有離身
母親在她的棉花地里勞作
我在電話這頭淚眼婆娑
雨一直下
雨聲敲打著我不安的靈魂
但沒有什么能扯斷
我和母親的聯系
大塊的棉花地
在70多歲的母親面前
也像她的孩子
我還有什么可說
水稻揚花
這是鄉間 樸素的稻子
在履歷一次生命的分娩
它高高地揚起頭
和季節作一次
深刻的對視
然后 開始上路
噴香的稻花閃爍水晶的語言
這是八月 鄉村的稻子
在用揚花的方式
和人類作年年歲歲的交流
周而復始地注釋季節的風雨
鄉村的稻子
在用揚花的語言
喂養人們日漸貧乏的思維
也飽滿
好多遠離鄉村之人的夜晚
其實 看水稻揚花
不如 聽水稻揚花
我知道 聽水稻揚花時
伴隨稻子拔節的聲音最動人
親近農諺
農諺長在土地和人類深處
四季的風穿透它豐富的內涵
農人的腳步踏踩它
成平平仄仄的句子
高高矮矮的莊稼把它演繹成
與人類息息相關的日月晨昏
農諺是祖先在千年流光歲月中
遺落的一支歌
被父輩們拾起
整理成好聽的音韻
被風一吹一送
四處溢蕩 落地生根
生命在飽滿的期待中吟詠
農諺 因了種子對土地的承諾
季節深處絡繹而來的歌子
才會燦燦爛爛
親近農諺
親近生我養我的土地
聽那被風吹來吹去的鄉村跫音
農諺 在時空中
令我好生感動
打著補丁的河流
坍塌了 童年的柳堤
河流一截一截打著補丁
象傷口
迎面痛苦地舔著我的靈魂
水到哪兒去了
蘆葦到哪兒去了
水鳥到哪兒去了
傍水而居的夢到哪兒去了
無語 一截截補丁
沉重的河床
長長的 嘆息
我聽見是祖先的怨聲
夜晚 我無論如何還是
做了一個夢
把自己變成了一條魚
潛回到了透明的河水中
初夏
一不小心
鳥的叫聲清脆了許多
陽光躍上高枝
向萬物拋著媚眼
白天長了 夜晚短了
鄉村肥了
時間廋了
父親徹底走了
在心底許下來生
呼吸
今夜 我呼吸不暢
頭頂的云越積越多
鳥 劃不開一片屬于自己的天空
雨點沒有 雷聲很大
風把思緒逼近墻角
吶喊中的苦
期待故鄉蘇醒
池塘
空曠過后是寂寞
蟬聲過后是午夜
游蕩過后是疲憊
思念過后是回望
沒有什么能改變池塘的風水
池塘四周是院落
池塘是風景
也是陪伴
也是夢
誰會在乎一方淺淺的池塘
誰就擁有一方淺淺的鄉愁
誰會在乎一方溫柔的池塘
誰就有資格懷想故鄉
永遠
永遠有多遠
老家有多老
夜色蒼茫
走過每一個游子
天地玄黃
過客的腳步匆匆
捧一把泥土
在腥味中舔舐山高水長
喚一聲乳名
感知鄉村俚語的永遠芳香
永遠的母親永遠的鄉親
永遠的疼痛
永遠的臍帶
永遠的鄉愁
永遠的村口
細水長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