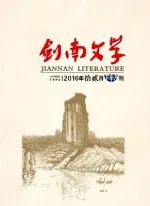文化傳統語境中的現代性研究
隨著西方社會形態整體上由現代向后現代轉型,西方學人開啟了對現代性、后現代性的反思。就中國而言,經濟的發展、全球化參與的深度化、中西文化及古今文化對話的深度推進,對中國現代性問題的拷問反思成為時下各學術領域關注的焦點。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歷史學、文學諸領域對中國現代性問題的探討成果斐然。
一、文化傳統與現代性
文化的定義可以說是最為豐富的。據不完全統計,大約有二百余種說法。愛德華·伯內特·泰勒認為:“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是包括了全部的知識、信仰、藝術、法律、風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掌握和接受任何其他的才能和習慣的復合體。”泰勒所謂的“知識”,主要是指建立在人類理性認知基礎上的數學、天文學、醫學、農學、工程學、生物學、航海學等普遍性經驗型知識范疇;其所謂“信仰、藝術、法律、風俗”等,放眼世界各民族文化而言,是共性與個性、普遍性與特殊性、人類性與民族性的統一。所以,泰勒關于文化的這一界說,揭示了世界各民族文化既有共性又有差異性這一本質特征,因此顯得尤其深刻。如此,文化則在更深層次上體現出使族群富于凝聚力、向心力的某種“內在力量”。這一“內在力量”顯然是在文化表現形態的知識、信仰、藝術、風俗、法律等演進史中形成的傳統,即文化傳統。
文化傳統是民族身份認同的一個重要標識。當外來民族征服一個土著民族時,其首要策略在于對該民族進行文化殖民的改造工程,從而消蝕其先有的民族身份認同感。可以說,世界任何民族基本都曾遭受過外族入侵甚至外族統治,因此每個民族的文化傳統事實上都處于被動的歷史變異狀態;并且,民族的活力源于其文化傳統對時尚文化及外族異質文化的主動吸納、革故鼎新。因此,每個現存民族的文化傳統同時也處于主動的歷史革新狀態。故而,人類文化傳統的穩定性是相對的,革新性是絕對的,沿革性才是文化傳統的深層特性。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尤其是在清末以來外力驅迫下被動奔赴現代性道路時,更體現出穩定與革新兩股勢能的交匯沖突。在這兩股勢能的較量中,“今且置古事不道,別求新聲于異邦”以求對文化傳統的改良卻是時代的絕對主題。因此,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客觀存在著一條嬗變的軌跡,而這條軌跡譜繪出了特定歷史階段民族文化傳統的命運。
“現代性”(Modernity)一詞的內涵是與“現代”(modern)、“現代化”(modernization) 相關聯。“現代”(modern)一詞最早書寫形式是晚期拉丁語的“modernus”,指“最近”、“現在”、“此刻”等。因此,“現代”就時限性來說,大約指中世紀末期,此時期系西方文化的轉型期,于此西方踏上了近現代文明之路——“1500年前后發生的三件大事,即新大陸的發現、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則構成了現代與中世紀之間的時代分水嶺。”西方近現代文明的實質是在構筑他們的現代化之路——如哈貝馬斯所言,“現代化概念涉及一系列的過程,諸如資本的積累和資源的利用;生產力的發展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政治權力的集中和民族認同的塑造;政治參與權、城市生活方式、正規學校教育的普及;價值和規范的世俗化等等。”“現代性”的定義雖然學術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均揭示出了其豐富而深刻的內涵。趙一凡先生認為,現代性有三個層面,即文藝現代性、哲學現代性、社會現代性。本文主要從以社會學角度探討文化傳統與現代性的關系,吉登斯的現代性界定也許更為確切:“現代性是一種社會生活或社會組織模式,它最初出現在大約17世紀歐洲,后來其影響或多或少地遍及世界范圍。”后來他又指出:現代性是“在后封建的歐洲所建立而在20世紀日益成為具有世界歷史性影響的行為制度與模式”,特征是 “工業主義”、“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等。
顯然,從上述關于現代性之概述來看,一個民族社會文化的現代性是就標志著該民族社會文化向現代化的轉型,在轉型中舊傳統得到革新,新傳統得到確立,即民族文化的傳統在現代性轉變會產生嬗變,從而折射出該民族在探求現代化過程中的心中歷程。
二、中國現代性特征
“現代性”只能是社會文化進入“現代”時才能產生。據社會文化向現代化轉型標志現代性問題產生這一觀點來打量中國的“現代”時限,則應當指鴉片戰爭之后的歷史時間。據此,中國的現代性內涵就是指 “中國社會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在古典性文化衰敗而自身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急需重建的情勢下,參照西方現代性指標而建立的一整套行為制度與模式。”從福柯關于現代性主要指涉到與現實相聯系的思想態度與行為方式,并與哲學認識論、方法論和道德、宗教、政治密切相關這一觀點來看,中國現代性內涵的當具化到清末以來中華民族對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制度與理想模式的羨慕與追求并訴諸到如政治模式、經濟制度、社會法治、婚姻觀念,以及風俗禮儀、宗教信仰、民族藝術等社會文化具體表現層的現代性實踐探求尋。
由于現代性發生的具體文化傳統與歷史境遇不同,中華民族的現代性與西方現代性相比較,有著明顯的特殊性。王一川先生認為中國的現代性特征在于,與西方現代性的原生型、合規律性的時空演進擴張、趨強型特征相比較,中國的現代性屬于后發型、時空裂變型、衰敗中轉型。這一分析有相當的深刻性。但我個人認為,我們還可以從其他角度來考察中國現代性的復雜與獨特性:第一,宗法血緣制、原始農業文明心態與思維方式、封閉的大陸環境,既是中華文化向本文化族群傳遞族群凝聚力的臍帶,也是使得文化傳統與現代性呈現出復雜的糾合關系,并使得現代性在中國的播撒顯得步履蹣跚的重要原因,同時也使得中國的現代性并不是對西方現代性的純粹拿來,而是集體無意識地混雜了由文化傳統所烙下的古典性;第二,由于中華民族在追求現代性之際,正值家國破敗、民族危亡,所以,追求民族自立、自強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是作為現代性的核心內涵來理解,因而,中華民族的現代性更多體現在政治、經濟、軍事層面,而這些目標追求的現實并不依靠個體的力量,而要依賴群體力量如政黨、集團、社會、種族、民族,等等,因而中國的現代性往往是集體主義的追求,沒有個體主義的追求——如對個人自由、個人信仰、個體存在的價值拷問——或者說,這方面的現代性追求在彼時中國歷史中并非占據著主導地位;也沒有對現代性在更為深刻、更為根本的文化層面、法制層面、哲學層面進行相應的推進與反思探究等,因而我們的現代性又是殘缺單一的現代性。同時體現出中國現代性深刻的民族主義特征——或者說,民族主義思想往往成為中國現代性發生、發展的最大驅動力;第三,據部分西方學者看來,西方社會已然進入后現代社會,故“后現代性”成為目前西方學者們檢討反思的熱點。當然,后現代性與現代性究竟有何瓜葛牽連,中西學界一時也無定論。如果從西方當前后現代性語境來看,中國現代性另一重要特征又呈現為:一方面,中國啟蒙現代性在歷史這一軸上顯然是沒有完結的,尚處于過程之中,因為現代性的重要內涵之一——作為主體的個人之自由、個人信仰、個人存在的價值等問題,在當下中國政治語境中并沒有得到解決,是發育不全的、甚或是腰斬了的現代性;另一方面,由于地域發展程度差異因素,廣大農村尤其是中西部農村,人在現代性社會中的主體地位更沒有得到張揚,因而在空間場域這一概念上,中國的現代性更體現出不平衡性;三是中國這一未盡的現代性工程又似乎搭乘著經濟與文化的全球化、現代互聯網技術等高速行駛的列車,同樣地,局部地、不平衡地、殘缺單一地跨入后現代性這一領域——在流行文化、民間價值立場等方面,可作如是觀。
有意思的是,正是混雜了文化傳統傳遞下來的集體無意識的古典性,決定了當中華民族在奔赴現代性、且傖促遭遇后現代性過程中遇到困難、挫折與困惑時,人們往往以回歸到傳統為對現代性的反思方法;而當被烙下民族主義特征的現代性遭受挫折時,由于缺乏對現代性全面打量的品質,因而這種現代性又表現出盲目與盲動,顯現出其先天畸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