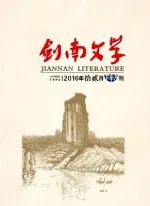《金瓶梅》讖語探析
《說文解字》曰:“讖,驗也。有徵驗之書。河洛所出之書曰讖。”讖語作為迷信的產物,是體現統治者意志并具有語言性質的文字或圖記。讖語作為我國術數文化中的一種奇特現象,在《金瓶梅》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值得我們來細細分析。
《金瓶梅》全書中,多處用到讖語。如潘金蓮摸李瓶兒熏被用的銀香球兒,道:“李大姐生了蛋了。”(第二十一回)張竹坡批:“又為生子作影。”回前評也提到:“閑閑一語,遂成生子之讖。”病中的李瓶兒對西門慶道:“誰信你那虛嘴掠舌的。我倒明日死了,你也舍不得我罷。”(第六十一回)張竹坡批:“說死者,自分未必死也。不知出口成讖矣。”等等。
一、讖語對《金瓶梅》結構的影響
以出現在第二十九回,揭示全篇人物命運的“吳神仙冰鑒定終身”為例。吳神仙為西門慶及其妻妾們算命,吳神仙說西門慶“形如擺柳,必主傷妻;若無刑克,必損其身。”李瓶兒“觀臥蠶明潤而紫色,必產貴兒;體白肩圓,必受夫之寵愛。”等,作者將預言人物命運歸宿的讖語設置在整體情節的三分之一處,符合《金瓶梅》“先是吳神仙總覽其盛,后是黃真人少扶其衰,末是普凈師一洗其業”的敘事脈絡。張竹坡第二十九回回評中道:“此回乃一部大關鍵也。上文二十八回一一寫出來之人,至此回方一一為之遙斷結果。蓋作者恐后文順手寫去,或致錯亂,故一一定其規模,下文皆照此結果此數人也。此數人之結果完,而書亦完矣。直謂此書至此結亦可。”自第二十九回、三十回以后,西門慶一家便顯現出不可逆轉的下降趨勢,也正符合了張竹坡所謂的“《金瓶梅》是兩半截書,上半截熱,下半截冷,上半熱中有冷,下半冷中有熱”的論斷。此讖語的出現在體現全文上半部分“熱中有冷”的敘事風格、承上啟下的同時,也充分顯現了作者在全文結構安排時的良苦用心。
二、讖語對《金瓶梅》主旨的影響
《金瓶梅》開啟了文人直接取材于現實社會而獨立創作長篇小說的先河,全文中無不洋溢著現實主義的風格,反映在讖語出現的具體語境中,也是如此。讖語出自吳神仙本人之口,授予西門慶、吳月娘等眼前的人物。在吳神仙對西門慶及妻妾等人物命運看似直言不諱的道白的同時,在某些程度上,也保留了不確定性,這與作者本身所持有的宗教觀有著必然的聯系。由于金瓶梅的作者不僅在創作思想上受佛教、道教影響很深,對佛教、道教的歷史作用自有看法和見解,而且具有淵博的佛教、道教知識。作者以寫實的筆法將讖語引入“在佛道教影響下而形成的世態習俗中”,整個相面過程中充斥著濃厚的現世宗教氣息,在這一背景下,讖語與小說的主旨融為一體,營造出一種極具現實感的宗教氛圍。
三、讖語對《金瓶梅》藝術風格的影響
“綜觀小說史上的眾多讖言,其中的下品使小說流于程式化的荒誕神道,中品多使小說增色不少,上品則羚羊掛角,無跡可求,達到藝術上的高度完美境界。”其關鍵在于讖語能否與小說的藝術風格融為一體。
張竹坡在《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中講到:“讀《金瓶梅》當看其白描處。”這要求我們在鑒賞《金瓶梅》讖語的時候,也不應忽視作者對白描的運用。白描這種作為文學創作中最常見的表現手法,賜予了《金瓶梅》中讖語獨特的藝術美感。為達到“摹神肖形,追魄取魂”的效果,結合白描和傳神筆法,勾勒與人物性格相符的神韻,《金瓶梅》中讖語在這方面做了較為成功的探索。用白描加修辭的方法寫吳月娘“女人端正好容儀,緩步輕如出水龜”;分別用“眼如流水”、“舉止輕浮”寫孫雪娥與潘金蓮,寥寥數字盡現其丑態;寫李瓶兒的“華月儀容惜羽翰”以及龐春梅的“天庭端正五官平,口若涂朱行步輕”,又不能不說是以簡約的言辭展現人物形象,突出個人特點的詩句。白描手法在體現《金瓶梅》讖語藝術價值的同時也賦予全文頗具世俗氣息的市民階層的審美風格。
經過綜合的分析,我們發現《金瓶梅》的讖語在適應小說主旨、結構以及藝術風格的同時,也服務于小說整體的需求。因此,讖語作為一種獨特的敘事意識形式,不僅具有其獨立的藝術價值,更是構成小說整體藝術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
(西南科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