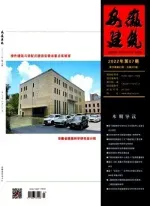從“霍華德”的田園城市走向科學發展的人居環境
馬皖強 (安徽省建筑設計研究院有限責任公司,安徽 合肥 230022)
1 概 述
霍華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現代城市規劃的先驅者,面對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以及帶來的新形勢,順應著工業革命后全新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為了解決日益突出的工業化城市相關問題,思索著“對環境進行全面的設計,進行某種探索”。由此,順應著城市生活個體、順應時代的物質需求,以及城市生活全體為了解決個體生活的需求,霍華德提倡“社會城市(Social City),開創了區域規劃、城鄉結構體系、城市體系的探索。
作為近代城市規劃的啟蒙者,霍華德所追求的,實際上是解決在新城市的影響下,全新時代中各類生活個體與客體的矛盾與沖突。在當時的思維體系中,模糊的科學發展的人居環境的概念,已經由此開始體現。只不過,當時的體現,在思維維度的限定下,所關注的個體還僅僅是“人”而已。霍華德,是基于一種“社會精神”全面推動人居環境的發展。
2 科學發展的人居環境科學
科學發展的人居環境科學(The Sciences of Human Settlements),是以人類聚居為研究對象,著重探討人與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科學。在這個體系中,主體不單單是人,環境也成為了所依托的重要一員。
霍華德在自己開拓性的研究中,其“田園城市”概念的建立與推廣,宏觀上說,已經隸屬于科學發展的人居環境科學了,但在當時思維維度以及宏觀地球環境科學認知的客觀局限性限制下,人居環境的改善主體,出發點還是局限于以人作為服務及被服務主體對象的。在同期“兩股并行的溪流”中,P·蓋迪斯(Patrick Geddes,1854~1932),現代城市規劃的奠定人之一,“從生物學研究走向人類生態學,研究人與環境的關系,系統研究現代城市成長和變化的動力以及人類、居住地與地區的關系”,從這方面來說,他研究的主體對象,已經要略進一步了。
P·蓋迪斯倡導了綜合規劃的概念,在這個概念中,“他把看做人類文明的主要器官”,并推演了主客體活動對客體環境演化的持續影響。基本框架在這個體系中,開始突破城市的常規范圍,囊括進自然地區。“有機規劃”概念的推行,是P·蓋迪斯不同于霍華德的地方。但沒有更大范圍環境系統理論研究體系的依托,P·蓋迪斯的所有概念,思想的局限性依然存在。
科學發展的人居環境科學,重點突出在“科學發展”。在每一個時間軸上,人們的認知都在不斷的突破,大環境體系所依托的空間維度也不斷拓展。在這種情況下,人居環境科學需要不斷依從維度的變化而變化,科學系統研究的著眼點作為系統的重要維度之一,也在不斷的變化著。作為一個多維度并存影響與發展的學科系統,時間維度、思想維度、空間維度、生態維度等多重維度的發展與變化,都讓人居環境科學走向更為客觀的研究體系。從根本上說,科學發展的人居環境科學,即使服務于人類,也是服務于人類所生存的環境,這兩個被服務的主體,是并行存在的。
人類所生存的環境:微觀上的體現,是現有的人類聚集點,從建筑單體(如會所、影院、體育場……)到建筑群體(社區、城市綜合體……),從鄉村到城市,從小城鎮到大都市,從都市到都市圈;宏觀上的體現,從都市圈到國家、區域,直至地球,甚至今后可能會發展的星際空間,都是環境主體。
隨著各種維度的不斷延展,區域化的研究開始建立發展。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一個既向往新技術又注重人文的博學者,被稱為上個時代最深入、最有影響的思想家之一。他強調以人為中心,提出影響深遠的區域觀和自然觀。在芒福德所推動的規劃思想體系中,以人為本和區域觀作為重點被正式提出、研究已經實施。在這個體系中,人居環境科學的科學發展,已經開始被淋漓盡致的得以體現。在隨后的時間軸上,科學發展的人居環境科學,便依附著所有現行的相關科學體系,隱性的發展起來,但在這個時候,科學發展的依據,還少了一個重要的體系的支持,即環境監測體系。
1975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下屬的全球和地區環境監測的協調中心(GEMS),根據1972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的建議正式成立,地址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它系統的收集、分析和評價各種環境狀況變化因素的數據和環境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變化情況。監測系統支持的活動主要有5個方面:氣候的觀測;污染物遠程遷移的監測;人體健康的檢驗;陸地可更新資源的監測;海洋污染狀況的監測。列舉的國際監測項目包括4大類:生態監測;污染物監測;自然災害監測;環境監測研究。我國從1978年起先后參加了大氣污染監測、水質監測、食品污染監測、人體接觸環境污染物評價點監測等活動。
3 人類聚居科學
道薩迪亞斯(C.A.Doxiadis,1913~1975),希臘城市規劃大師,將聚居(Settlement)的概念提取出來,加以系統研究,稱之為Science of human settlements,吳良鏞先生將之翻譯為“人類聚居科學”。人類聚居學的研究,在吳良鏞先生看來,是一項建設性的、創造性的工作。從古至今,建筑學者們一直強調的是建筑的特性、藝術性以及規劃的“為人性”(For-Human),但總體還是依托于建筑為研討基礎。人類聚居科學系統的正式建立,讓科學發展的人居環境科學開始有了自己的骨架與血肉,不再依存于其它學科與體系。而且,1975年建立的GEMS,也開始源源不斷為“科學發展”輸送強有力的支撐體系。
人類聚居科學,因道薩迪亞斯的創建,可以稱之為道氏學說,在吳良鏞先生看來,其系統的理論特點主要表達于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時代及其所面臨的任務的認識”。在這一點,從1963年《臺勞斯宣言》開宗明義:“縱觀歷史,城市是人類文明和進步的搖籃。今天,就像其他所有的人類機構一樣,城市杯極度地卷入了一場襲擊整個人類的迄今為止最為深廣的革命之中。”這場革命是什么?就是城市化。城市的發展與進化,隨著人類文明的需求,在霍華德、蓋迪斯、芒福德等人的系統映像下,用自己被動的發展方式,席卷、映像了整個人類聚居環境,在現代社會,這種映像,即使對于為加入人類聚居區的非聚居自然環境,也造成了深刻的影響。1967年《臺勞斯宣言》指出:“從整理看來,直至最近,政府、學者、經濟學家、專家們都已忽略了城市化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城市化是發展的結果,也常常是發展的負擔。但是,它還應該成為良性發展的手段。”道薩迪亞斯,通過城市化引發的各種影響以及環境的影響與被影響等各類城市發展維度上的拓展,開始”人類聚居學“的建立與研究。
第二,“考慮問題的整體觀、系統觀”。在現代,城市發展的問題錯綜復雜,除了之前各種發展學說、體系的依托,面對的問題卻沒有直接的線性關系和解決方法。“人們總是試圖把某些部分孤立起來單獨考慮,而從未想到從整體入手來考慮我們的生活系統”。人類聚落的發展,始終以一種非線性的螺旋纏繞的方式往前行。道薩迪亞斯開始用人類聚落環境的整體性、系統性為研究建立起系統模型架構。
第三,交叉學科觀點的應用,多學科并行的理論研究方法,也拓寬了道氏學說的維度。這種研究方法意義非常。人類聚居學不單單是建筑學、城市規劃學、地理學、社會學等學科某一體系的研究方向,而是眾多學科都需要面對與解決的。人類聚居,實際上是一個眾多學科的主體。所有學科的“起承轉合”,都與人類聚居學相依共存,同時,學科上的共生體系,也為科學發展的人居環境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這一點,從1975年建立的GEMS,可以得到強有力的證明。
理論框架的初步建立,是道氏學說為科學發展人居環境研究系統提供最有效的研究模型。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作為該系統模型的有效支撐,讓人居環境的科學發展性有了更具有客觀性的特性。道薩迪亞斯1975年完成的《人類聚居學與生態學》(Ekisticsand Eclolgy),作為道氏學術思想有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成為了今后人居環境科學發展研究的強有力支持體系。
4 結 語
從霍華德的田園城市,到道薩迪亞斯的人類聚居學,對于人居環境科學發展與研究來說,這些體系都是人居環境科學的歷史依托。宏觀上說,無論是哪種學科,都是在研究、探索人與環境的關系及發展,以人類生存環境為框架,人與生存環境為共生體系,既解決人類的生存環境問題,又解決環境被人類生存所擾動的問題。由此,科學發展性,作為人居環境體系的重要影響維度,逐步深化影響到我們今后的人居環境發展體系中來。
[1]伊利爾·沙里寧.城市——它的發展衰敗和未來[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86.
[2]吳良鏞.人居環境科學導論[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