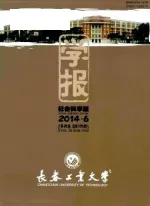被建構的“人”——關于福柯的主體論的解讀
金 輝
(廣西中共欽州市委黨校,廣西 欽州535000)
一、從“人”到“主體”
(一)沒有起源的“人”
從研究“神”的問題到研究“人”的問題古希臘哲學完成了它的第一次范式轉變。我們今天之所以稱蘇格拉底為“第一個把哲學從天上請回人間的哲學家”正是因為他把早期古希臘哲學的研究重點從自然界轉向了人的問題,從此人的問題作為哲學的中心問題成為了任何一個哲學家或哲學著作都不可回避的問題。在蘇格拉底之后,從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到薩特的“存在主義”,從尼采的“上帝之死”到福柯的“人之死”都是以人的問題為中心展開論述的,我們甚至可以說自蘇格拉底之后對人的問題幾乎等于了哲學的元問題。①哲學觀問題有廣義與俠義之分,廣義的哲學觀問題是元哲學問題,俠義的哲學觀問題是哲學的元問題。元哲學問題不同于哲學的元問題,哲學的元問題只有一個,即“哲學究竟是什么”。引自《哲學通論》郭慶堂、王昭風、丁祖豪、唐明貴合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2008,10,第1頁。然而,要從哲學的角度探究人的問題就不得不首先回答“人”從哪里來。當一個孩子問他的母親他是從哪里來到世界的,母親的回答往往都是一樣的,她會告訴孩子他從母親的體內孕育而出,這是最簡單也是最本能的回答,若是把這個問題放到現代可能母親并不害怕孩子繼續追問她是從哪里來的(這種追問甚至可以一直到他的曾祖母是從哪里來的),可是若放到古代社會,不論是西方的古代社會還是東方的古代社會,孩子若是繼續追問母親可能母親會無言以對,或是用非科學的解釋將孩子打發掉。原因很簡單,現代社會自然科學不僅發達而且普及,因此孩子的不斷追問終究會得到一個科學的解釋。這里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即是不是在自然科學出現之前的時代里人們就無法回答孩子的追問了,顯然也不是,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母親很可能會用一種非科學的解釋回答孩子的追問,并且這種非科學的解釋在當時看來可能被人們視為非常合理的——人是由神創造的,在西方神可能指上帝,而在其他的國度可能會有自己的神,例如中國的“女媧”。當自然科學足以用科學的方法揭示人的起源時,人類的自我認識無疑邁了一大進步——我們對人的起源問題不再糾結于神了,特別是在現代社會,一個略微有點知識的人都知道人是從猿進化而來的,這一切都看似十分合理,可在哲學層面上卻存在著很大的缺陷。哲學上人的意義不同于自然科學,在自然科學上我們說人起源于猿是把前者和后者當做同一物種的不同進化階段看待的,兩者具有同一性,而同樣的話在哲學上是矛盾的。哲學上所講的人是一個人類自我認知的概念,“人”這一概念是在猿之后形成的,是人成為“人”之后對自我的建構,正如卡西爾所說:“物理事物可以根據它們的客觀屬性來描述,但是人卻只能根據他的意識來描述和定義。”[1](P8)因此,在哲學層面上人就不可能起源于猿,因為“人”這一概念是形成于人類自我意識中,它是人根據以往自身在自我頭腦中的表象形成的抽象概念,而這一表象一定不是人進化為人之前的那個生物形態所具有的表象,不管那個形態是猿還是別的。既然是這樣我們不免要問,那哲學層面上“人”的概念形成于什么時候呢?是不是找到這個時間點就可以說找到“人”真正的起源了呢?問題就在這,盡管我們知道“人”的概念是來源于人的意識,可人這一形象的開端卻是在我們得出抽象概念之前(在那之前的我們已經成為人了),即便我們能考證概念的“人”形成的時間點(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可我們發現,現實的人早就站在概念的“人”之前了,因此我們無法窮盡“人”的起源時間點,就像福柯所說:“來源并不宣告其誕生的時間,也不宣稱其經驗最古老的核心:來源使人與并不具有與人相同時間的一切聯系起來了;來源不停地并且在始終更新的擴散中表明事物已開始在人之前,并且由于這個原因,由于人的經驗完全是由這些事物構建的和受其限制,所以沒有人能歸于人一個起源。”[2](P432)汪民安也認為:“在現代思想中,人并沒有一個確切的起源,人是一個毫無起源的存在,與其說存在著這樣一個起源,不如說存在著一個散布的來源,一個沒有固定明確的誕生地的來源、沒有同一性的來源、沒有瞬間性時刻的來源。”[3](P80)
(二)成為主體的“人”
哲學上普遍認為:“主體指的是一種有著主觀體驗或與其他實體(或客體)有關系的存在。就此而言,主體就是感知者、觀察者,而客體則是被感知、被觀察的東西。由于主體指的是實施行為并為之負責的個人或實體,而不是實施與其上的客體,因此這一術語常常被當做‘人’的同義詞,或指涉人的意識。”[4](P500)所以在很多哲學家看來,主體等于“人”,主客二元對立的確立就是源于從“猿”到“人”的建構,盡管人是先成為“人”才建構了主客二元的世界觀,可主體的含義卻使得主體和“人”在時間上處于了同一個開端,從這個角度來說,一次生物學上的轉變(從猿到人)讓人同時完成了對自我認知的兩次建構,即“人”的概念的建構和主體概念的建構,然而在福柯看來,這種主流的哲學觀點是站不住腳的,他認為人和主體不可能同時建構,因為作為主體的人是人類進入現代社會的產物,是19世紀才存在的。正如他自己所說:“只要仔細觀察一下16、17、18世紀的文化,我們就會發現,在此期間人根本沒有任何位置。”[5](P79)他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他看來只有人將自己視為一個研究對象加以認識才能稱自己為主體,而這一切都是伴隨19世紀后人文科學的建立發生的,在這之前人對自身的認識是缺乏社會深度的,因為主體應該被視為一個關系范疇,是一個人與他人和自身的互動中體現出的概念,因此他認為:“主體這個詞有兩種意義:控制和依賴使之隸屬于他人;良知或自我認識使之束縛于自身的個性。兩種意義都表明了一種使之隸屬、從屬的權力形式。”①“福柯的附語”,主體與權力,附于美L·德賴弗斯、保羅·拉比諾《超越結構主義與解釋學》,張建超,張靜譯,光明日報出版社,1992年版,第276頁。可見福柯關于主體的論述是建立在這樣一個主體概念之上的,所以他的主體不同于其他哲學家眼中的主體概念,他的主體只存在于現代社會。在福柯看來,現代社會中的人就是他所說的主體,而且這個主體概念充滿了悲觀的情調,正如有的學者這樣說道:“在福柯看來,現代人不是本真意義上的人,而是被改造成為主體,都是把人變成主體的產物。反過來可以說,福柯筆下的‘主體’在倫理學意義上指的就是按照一整套現代社會標準來思想、行動和生活的現代人,這個現代人之所以遵循同樣的、齊一的倫理規范,是因為他們/她們都按照同樣的、齊一的主體觀念改造過,這種改造不僅是身體上的規訓而且也包括思想上的清洗。”[6](P48)可見,一方面福柯本人對現代社會中作為主體的人深表同情,另一方面對現代社會給予了強烈的抨擊,從這個層面講,福柯的主體觀也可視為對現代性的批判。
二、現代社會中主體的困境
在福柯那主體從來都不是自由的,這個被建構的主體從誕生之日起就被卷入了現代化的浪潮中。如果說在康德那主體的顯著特點是“道德化”,那么在福柯這主體的顯著特征無疑就是“現代化”。關于“現代化”這個概念有些后現代理論學者給出了這樣的定義:“現代化——一個標示了個體化、世俗化、工業化、文化分化、商品化、城市化、科層化和理性化等過程的詞匯。”[7](P3)和大多數后現代哲學家一樣,福柯也將自己的批判矛頭指向了現代化的主體,并且將現代社會中人的種種困境歸結于現代權力的運用以及話語對人的控制。在馬克思那現代社會的人是異化了的人,在馬爾庫塞那現代社會的人是單向度的人,而在福柯那現代社會的人是理性的人。筆者認為,在福柯的思想中我們可以得出現代社會中理性對主體所造成的兩大困境,第一,人在整齊劃一的社會規范中喪失了自我個性。所謂整齊劃一可看作是社會化的極端形態。在現代社會中人的言語和行為如同工廠生產的同一標準的零件,只有統一標準沒有差異性,只要不符合標準的就會被處理掉,對于零件來說可能是被丟棄,而對于作為主體的人通常都會受到懲罰與規訓,像監獄和學校這樣的機構就是在承擔著這種功能。盡管這種整齊劃一的控制模式在維持社會秩序和提高社會運行效率方面有積極的作用,可它的負面效應更是巨大的,因為在這種境遇下人的自我意愿往往被組織忽視,每個人都被規范的話語①話語不同于句子或語詞,它已經不單純是一個語言學的概念,不純指一種用來表達意義的詞語的組合,而是一種“推理的實踐”。所謂“推理的”,就是在時間和空間中一步一步地展開的;所謂“實踐”,是因為它也是一種“事件”。控制著,個人在行動之前早已被確定好的話語模式所限定了,這使得人失去了自我反思的可能,個體頭腦中的印象往往是個人必須服從社會規范,只有服從社會對個人的種種限定才能使自己成為一個成熟的人并且這種限定是不容懷疑的,因為現代化的豐碩成果是最有力的證明其合理性的證據,正如馬爾庫塞所說:“當一個社會按照它自己的組織方式似乎越來越能滿足個人的需要時,獨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對權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逐漸被剝奪”。[8](P3-4)工具理性逐漸占據了價值理性在人類意識形態中的空間,人也不再是現代化的目的,而是淪為現代化的手段了。第二,對主體的盲目崇拜。盡管在福柯之前哲學家建構了各式各樣的主體,可福柯所建構的在現代社會中的主體無疑是最瘋狂的。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使人的足跡遍布到了其技術所能窮盡的任何一個角落,人不僅僅陶醉于自己所創造的物質生活中,而且為自己不斷完成的一個又一個征服自然的“壯舉”而驕傲不已,這一切都讓人沉醉在成功的喜悅中,在喜悅的背后我們看到的是人對自己的深深崇拜,這種崇拜實質是對理性的崇拜,人對自己就是理性的化身這種觀點深信不疑,人出于理性的行為往往都被貼上了合理性的標簽,那些被判定為非理性的行為在福柯看來都是要受到規訓的。然而,理性對人類來說卻是一個神奇的東西,它取得的成就越大,人類所面對的麻煩似乎就越多,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就是很好的證明。戰爭帶來的毀滅性在現代社會顯然是不可能發生的,更可怕的是,人類并沒有進行深入的反思,盡管人類會反思戰爭爆發的偶然性與必然性,可卻忽略了一個前提,即人類創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可能性一直存在,而且人類至今認為這種可能性的存在是合理的。對此,有的后現代理論學家給出了這樣的評價:“現在,我們已經失去了不受核災難威脅的未來,并且正在失去生物圈的生態支持系統。由于對現代合理性的執迷不悟,我們正在做著將導致人類自我毀滅的非常荒謬的蠢事”。[9](P64)所以,理性的過于張揚只能使人走向理性的反面,即出于理性的動機卻產生了非理性的后果,這就是“理性的無知”。這里我們可以看出,理性本身也經受著異化,因此筆者認為這種理性的異化正是現代社會中各種異化的根源。
三、主體的未來
面對現代社會中人的困境,福柯提出了一種極端的拯救方法,這就是他驚世駭俗的論斷——“人之死”。這里面的人是哲學層面上的人,他所說的“人之死”是指現代社會中作為主體的“人”概念要重構,是對現代主體的解構。現代社會中的主體被賦予了太多意義,人成了世界的中心,現代社會對人的建構就是將人推向了中心化,而福柯的“人之死”就是要使人擺脫中心化。尼采宣稱“上帝死了”是為了將人從神學和宗教中解放出來,福柯的“人之死”則是要將人從對理性的迷信中解放出來,福柯并不反對現代科學技術,只是認為人類應該對理性加以重新審視,從而走出理性至上的誤區,達到對主體解構的目的。一直以來人類都認為自己不僅能夠建構客觀世界,更可以把握住自身的命運,然而,福柯通過對知識的考古學研究和話語的形成規律與作用機制的研究得出了一個發人深思的結論,即人自身并不完全被自己掌握,而是同時被話語限定和支配著,人和人的理性都在一定程度上被話語所建構,所以主體的解構離不開理性的重構,這種對理性的重構正是主體解構的前提,當主體認識到自己正在像他建構客體那樣被話語建構的時候其所處的境遇也就和客體沒有差別了,這也就使得理性的重構成為了可能。
四、結語
福柯對人類知識所做的考古學研究以及對話語形成所做的獨到分析,其最終目的都是對現代性的主體進行研究,就像他自己所說:“我研究的總的主題,不是權力,而是主體。”[10](P280)筆者認為,現代社會中的人既在建構客觀世界,同時也受著客觀世界的建構,所以現代社會的運行是主、客體雙向建構的過程。福柯筆下的主體消解了,人類還會建構下一個主體,歷史的輪回就在于主體的建構與解構這一過程。主體可以重構,但主客二元對立卻不會消亡,因為我們無法想象在其它動物眼中人是什么樣的,我們無法了解動物的語言,更無法使自己用動物的意識反過來審視自己,只要我們對世界的認識還依靠我們的語言去建構,那么人就必須站在客體的彼岸,而不論我們稱呼彼岸的東西是主體還是什么別的東西,在福柯之前人自己在建構自己,福柯之后客體與主體在雙向建構,這就是福柯給我們的最大啟示,也是對他筆下的主體解讀的最大意義。
[1]〔德〕卡西爾.人論[M].甘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2]〔法〕福柯.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M].莫偉民,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
[3]汪民安.福柯的界限[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
[4]汪民安.文化研究關鍵詞[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
[5]〔法〕福柯.福柯集[M].馬利紅,譯.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
[6]劉永謀.福柯的主體解構之旅—從知識考古學到“人之死”[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
[7]〔美〕凱爾納,貝斯特.后現代理論—批判性的質疑[M].張志斌,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
[8]〔美〕赫伯特·馬爾庫賽.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M].劉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
[9]〔美〕喬·霍蘭德.后現代精神的社會觀[A].〔美〕格里芬.后現代精神[C].王成兵,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
[10]〔法〕米歇爾·福柯.福柯讀本[M].汪民安,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