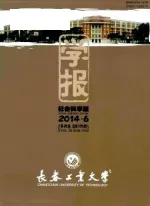中韓儒學思想比較研究
李 丹
(西北大學 哲學與社會學學院,陜西 西安710119)
中國儒學主要是指我國春秋時期孔子所創立的學派。“儒”在其前期主要是指專為各級貴族服務的巫、吏、視、卜;在經歷了春秋時期的社會大動蕩后失去了原有的主導地位,只能以擅長的“禮”來謀求生計。由此,在我國春秋末期,“儒”僅指的是個別以禮謀生的知識分子,而并非一個學派。而孔子早年就曾以“儒”為職業,并且因通曉養生送死之禮、具有豐富的文化知識,其名下弟子日益增多。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文藝有七十二人。”[1](P34)由此,便形成了以孔子為核心的儒家學派。
韓國儒教是在中國儒學傳入其本土之后,與之相關信仰相結合而構成的具有韓國思想特色的思想體系。韓國早期的儒教思想主要包含:性理學、陰陽學、實學等內容。韓國政府于1982年開始,實施了教育改革,并且以健康、獨立、創造、道德等為核心關鍵詞,力圖培養韓國國民的優秀價值觀。而此時,具有韓國特色的儒教思想名副其實的成為韓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主流。
一、中國儒學思想
(一)基本思想
考究孔子的哲學思想,可以從“天命觀”和認識論兩個方面出發。
首先,孔子繼承了自西周以來的天命思想,并以天命觀作為自己哲學思想的根本主基。在孔子看來,“天”是具有與人相似的意志的,世間萬物均是由天來主宰,而且“受之于天”的。孔子曾說過:“獲罪于天,無所禱也。”[2](P127)有一次,孔子受人圍困,危及性命,他還是寄托于天,感慨道:若是上天想讓文化滅亡,那我就不該宣揚文化,若是上天想保全文化,你們又能奈我何!不難看出,在孔子眼里,天命是不可被違背的至上精神。孔子將“天”看作是自然界最高的、最神圣的主宰者,具有最權威的力量。他認為,天雖不曾言語,不曾發號施令,不曾干預自然,但四時萬物仍在有條不紊的運行,這便是天的能量之所在。它無時無刻不在關注著世間萬物的生息發展,并且同君王一樣,能對世間萬物施以賞罰,能決定社會安定與動亂,還能決定文化、文明的產生與興亡。所以,孔子認為,作為君王,“知天命”是實現其統治的必要條件,“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其次,孔子也提出了關于哲學認識論的相關問題,他所秉持的認識論觀點是具有唯心主義色彩。孔子認為知識是與生俱來的,是先于經驗和實踐而存在的。他將人分為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以及困而不學四種。生而知之之人生來就有知識,有智慧,實踐與經驗只是存在于他們所具有的的知識之后的東西,孔子認為諸如堯舜、周公等就是生而知之之人。而學而知之和困而知之之人,是可以被教化的,屬于中人的范疇,大多數人都是中人。困而不學之人是居于中人之下的,屬“愚”的范疇,對這種人進行教化是沒有用的。孔子所說的“愚人”就是指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這些人只能充當統治階級的工具,為其統治而貢獻體力。
孔子這一具有唯心主義色彩的認識論,與其所一貫秉承的天命觀是分不開的。或者可以某一程度上說,其唯心主義認識論是其神秘主義天命觀的接續。與此同時,這種先驗式的認識論又將他牽入了天才論的理論漩渦中。他認為,天才是存在于人世間的,并且天才的智慧是與生俱來的,他不需要接觸客觀世界的任何東西就可以獲得真知。孔子還將天才論與天命論結合起來,使得其認識論的唯心色彩更為濃重。
此外,孔子的哲學觀點中還有一定的辯證法思想。例如“性相近,習相遠”,這是說人與人先天是沒有多大差別的,后天習性的不同決定了人與人的不同;又如“過而不改,是謂過也”,這是說人都是會犯錯的,犯錯了改正了就好,若是“錯而不改”,這才是“大過”。再如,孔子曾說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思想,這是正是實事求是的思想,說明了知道就是知道,不知就是不知,若是不知卻謊稱知道,那就是不謙不敬。孔子的這些思想都是符合辯證法的思想,并且仍對我們有良好的借鑒意義。
(二)基本特征
我國古代,各個學派的思想百家爭鳴,而儒學思想作為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影響甚深的思想體系,與其顯著的思想特征是分不開的。
1.視宗師孔子的言行為最高準則。儒家學者均尊崇孔子,并把孔子視為儒家的祖師。但被后世儒家學者所推崇的孔子,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孔子,僅僅只是被人為的主觀化了的孔子。這種所謂的推崇實際上只是打著孔子的招牌為自己的主張游說。諸如孟子以其主張的仁政為孔子思想的核心,而荀子卻認為孔子思想的核心亦是他所主張的禮治。
2.提倡仁義,重仁行。歷代各學派尊崇孔子思想,無一例外均推崇仁義思想,這與儒學倫理道德學的本質是分不開的。一直以來,儒學都嘗試著用仁、禮、信等道德原則來維護封建統治。儒家認為凡事均應尊崇仁義,這才能達到事物預期的目的,并且將仁義作為人的行為準則。
3.重視倫理綱常。儒家重視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的倫理關系,并且認為人們應該嚴格按照這種以孝悌為核心的倫理準則。儒家學者認為,只有做到“君臣之義、夫婦之別、兄弟之悌”,才能保持封建社會的良好運行秩序,才能夠由己及家,由家及國,真正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的。
二、韓國儒教思想
朝鮮半島社會于公元前后開始向封建社會過渡,這一時期先后出現了高句麗、百濟、新羅的儒教思想。
(一)高句麗儒教基本思想
高句麗封建國家建立于公元前1世紀后半期。[3](P66)高句麗的歷史發展我們在這里暫且不談,主要談談其儒教的基本思想。首先,主張“以道治國”。這是高句麗東明王臨終時給琉璃明王的囑咐。他重視道德的作用,反對強力治國,他認為文武兼備是“以道治國”最好的體現,是后人必須遵循的最理想的治國方略。其次,實施“安民仁政”。高句麗儒教思想認為,政治統治思想的核心應該是仁政,而要實施仁政最重要的在于“安民”,而安民的核心則在于廢除苛捐雜稅,減輕百姓負擔。《三國史記》中記載,國王應時刻關心百姓的疾苦,特別是那些孤苦無依的老人、小孩。當國家遇到什么災難或是困難時,應首要考慮百姓的利益,并且應將罪責歸結于自身的無能,任何時候都不能怪之百姓。但這僅僅是對統治者“善意的提醒”,在封建階級社會中是不可能實現的。第三,實現“有德者在位”,即國家應該積極提拔和使用人才,并且應達到野無遺賢。高句麗儒教思想認為人才是一個國家得以興盛和繁榮的前提和基礎,對社會和國家發展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這充分表明了高句麗是以儒教為統治理念的國家。第四,注重“孝悌忠信”。高句麗倫理思想最為關鍵的內容即是“忠孝”。孝敬父母,這是人類的基本屬性,但高句麗的忠孝觀念在儒教的影響下發展為對祖先的強烈崇拜之意。第五,貫穿“有教無類”。這里的“教”與我國儒學中的“教”不同,它指的是高句麗儒教大學的內容及扁堂教學內容。培養能文能武并忠于國孝于父母的人才,是太學和扁堂的主要任務。
總的來說,高句麗儒教思想對社會的發展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表現在首先在對國家體制的建立和社會規則的確立上,其次是對政治、倫理、教育上產生的全面性的、深刻的影響。
(二)百濟儒教基本思想
相比之下,百濟受儒教的影響比較大,其基本思想主要有:提出“養民之政”。據《周書·異域》記載,百濟時期國家對百姓所實施的稅收政策是按豐收年和歉收年而制定的,豐收年增稅、歉收年減稅,這些都體現了百濟社會愛民、恤民、以人為本的思想。提倡廉政。百濟社會對官吏有“三事”制度的要求,即清廉、勤身、勤勉。在這三者之中,清廉是最為重要的。百濟社會要求,為官者必須時刻保持清廉,如有受賄、偷盜之舉,將受三倍懲罰或受終身監禁之苦。祖先崇拜和宗廟制度得到了確立并延續下來。在當時的百濟社會,“孝”仍是政策的基本原則和帝王之學的根本要義。百濟將祖先崇拜和宗廟制度結合起來,建立了每四年都要祭祀歷代先王的制度,并且建立了東明王廟,以示對祖先的忠孝和崇拜。百濟也受儒教中的陰陽五行思想影響,表現在其行政首都按照前、后、左、右、內、外的劃分上。
(三)新羅儒教基本思想
在新羅時期,隨著漢文的傳入,儒學思想逐漸傳播開來,并且當時的國王派遣留學生前往大唐學習,支持儒學思想的研究。在新羅,儒教思想的影響及其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第一,以儒教思想為基礎的“王道”理念。作為儒教政治核心思想,仁政亦是新羅社會統治者主張的思想。他們認為“施仁”是王者統治的必要條件。新羅真興王尤其強調世道人心的重要性,認為修王安人是國王之本分。[4](P12)
第二,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忠孝兩全”思想。在新羅社會,忠孝思想及其重要,欽春曾教育兒子盤屈說道,臣不盡忠、子不盡孝是致命危險的事,屈則也曾對兒子令胥說過“臨陣無勇”是禮經所識,臨陣無退才是氏族之常分”。據學術界考察,新羅在統一三國之前講求“忠”,而統一之后更側重于“孝”。這歸根結底取決于統治階級的利益。
第三,以儒、佛思想為基礎的“世俗五戒”思想。世俗五戒是新羅花郎徒(于真興王37年興起的以青少年為對象的民間團體)的主要思想。花郎徒宗團的主要目的就在于灌輸孝悌、忠誠、誠信等的思想,以此來培養孝順忠孝的人才,這也就是所謂的“入則孝于家,出則忠于國”的精神。
三、中韓儒學(儒教)思想異同點評議
中國與韓國均屬于東方儒教文化圈,而且歷史上有著長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與合作,所以中韓儒學思想有著一定的相同點,也有一定的不同點。
相同點是,第一,兩者的社會政治思想基本相同。當時的中國儒學是以維護封建君主統治為目的的,并且主張孔子的“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德治思想;這與高句麗國王所秉持的“以道與治”思想如出一轍。第二,制定典章制度和法令的一句基本相同。中國古代的宗法制度是以儒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為依據的,韓國也同樣在許多方面借鑒了儒學的主張,如忠諫制度是采用了孔子“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思想,又如新羅受唐朝的影響,在朝廷設置兵部、司政部、禮部、租和部等,開始加強中央集權。第三,教育制度和內容大致相同。孔子利用自己大半生的游學經驗,總結出許多具有價值的教育思想,例如有教無類、學而優則仕、學思一致、因材施教等。孔子的這種思想廣泛在朝鮮三國得到廣泛傳播,朝鮮迅速掀起了教育熱,建立了儒學教育制度、以漢文字為本創立了本民族的文字。
三國時期,韓民族尚不具有理性文化,與中國儒學思想有很大的區別:第一,歷史背景不同。中國儒家思想產生于春秋戰國時期,后經發展形成了完整的儒家體系;韓國的儒教晚于中國,由中國儒學發展而來并且逐漸被世俗化、民族化。第二,所起的作用不同。儒學作為中國封建統治的工具,長期對中國傳統文化起著主導性的作用;而韓國儒教在三國時期雖然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新羅末期其社會地位受到佛教沖擊,最終被擠下舞臺。第三,倫理觀不同。中國儒學倫理思想以仁為核心,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而韓國儒學卻將“孝”放到極其重要的地位。第四,宇宙觀不同。中國儒學主張天命觀,認為天是有人格、有意志的;而韓國儒教的天命觀主要表現為對祖先的崇拜。
[1]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M].北京:北方文藝出版社,2007.
[2]張燕嬰.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6.
[3]樸真爽.朝鮮簡史[M].延邊:延邊教育出版社,1986.
[4]金京振.中韓宗教思想比較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