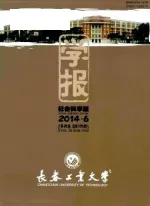論元稹的樂府觀
李 雪
(廣西師范學院 文學院,廣西 桂林541004)
元稹(779-831年),字微之,別字威明,洛陽(今屬河南)人。唐代文學家,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和小說家,其詩與白居易齊名,世稱“元白”,8歲喪父,少經貧賤,15歲以明兩經擢第。21歲初仕河中府,25歲登書判拔萃科,授秘書省校書郎,28歲列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第一名,授左拾遺。元和四年(809)為監察御史。因觸犯宦官權貴,次年貶江陵府士曹參軍。后歷通州司馬、虢州長史。元和十四年任膳部員外郎。次年靠宦官崔潭峻援引,擢祠部郎中、知制誥。長慶元年(821)遷中書舍人,充翰林院承旨。次年,居相位三月,出為同州刺史、浙東觀察使。大和三年(829)為尚書左丞,五年,逝于武昌軍節度使任上。在《古題樂府序》中元稹總結了自南朝以來,舊題樂府詩創作模式化的問題。但認為利用古題對現實進行美刺,內容文辭有所創新者,也值得肯定。因此他在創作新題樂府的同時,也寫古題樂府。不論新題古題,元稹都要求創新。本文以元稹的樂府觀為研究對象,分別從元稹的樂府源流觀、功用觀和藝術觀三個角度對他對傳統樂府的繼承和創新之處進行剖析與解讀,以便后學對樂府詩創作進行更深入的了解。
一、元稹的樂府源流觀
元稹的創作,以詩成就最大,其中樂府詩占著極大的比重。他與白居易齊名,并稱元白,同為新樂府運動倡導者。他的樂府觀對后世文學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他的樂府詩對傳統樂府詩歌的繼承,主要體現在其音樂性和人民性上。
其一,樂府詩從其來源上看,最初是一種音樂文學,因而它的發展和衍變與音樂有著不解之緣。元稹認為嚴格意義上的古題樂府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的詩、行、詠、吟、題、怨、嘆、章、篇等九名,這類樂府內容上“屬事而作”,題目上“題號不同”,先成歌詞,由審樂者“取其詞,度為歌曲”。另一類是“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的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等八名,這類作品來源于“郊祭、軍賓、吉兇、苦樂之際”,先有曲,再嚴格地按曲填詞。雖然這兩類樂府講究配樂、定詞,但由于“亦未必盡播于管弦”,而是“以句讀短長為歌、詩之異”,即體式作為判斷樂府的又一標準。這是傳統的樂府詩歌,元稹也主要是從音樂關系上來定位。
其二,樂府詩本就來源于民間文學,《漢書·藝文志》所謂“感于哀樂,緣事而發”[1]的現實主義精神,正可作為樂府精神的寫照。元稹《樂府古題序》所謂“屬事而作”“諷興當時之事”,仍可見出其對感事傳統的繼承。元稹的古題樂府同新題樂府的創作精神基本一致,都堅持了新樂府的核心主張,描寫時事,揭露弊政,反映人民疾苦,體現了風雅比興的諷喻精神。如《董逃行》結尾處詩人以諺語的形式引出新意,意在說明亂易治難的道理。但是,由于古題樂府反映現實有一定的限制作用,易造成“沿襲古題,唱和重復,于文或有短長,于義咸為贅剩”的弊端。元稹創作的新題樂府,數量上要遠遠超過古題樂府,這與他的政治思想和文學主張也是一致的。
由以上分析可見,元稹的樂府觀無論是在音樂性,還是人民性上都受到了傳統樂府的深刻影響,體現了樂府詩作為一種音樂文學的本質和現實主義精神。
二、元稹的樂府功用觀
元稹的功用觀主要體現在其新題樂府對傳統樂府的創新,他主要突出強調了兩個特點,第一是“刺美見事”,內容上要反映現實,即樂府詩歌的政教功用;第二是“即事名篇”,題目上要自創新題,即樂府詩歌的審美功用。
一方面,《古題樂府序》中“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正是樂府詩歌政教功用的表現。他又特別提出:“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反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傍。”在這段話中,元稹對杜甫“即事名篇”的歌行給予高度的評價,不僅看到杜甫在詩歌形式上的合理改革,而且注意到這是對《詩經》、漢樂府以來的寫實主義詩歌傳統的繼承與發揚。元稹指出了杜甫的作法對自己以及白居易、李紳等人的新樂府詩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大力推動了新樂府運動,使之具有實質上干預政治的積極意義。元稹還說過:“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2]可見,他推崇杜甫并不僅僅著眼于“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而且也著眼于“刺美見事”。這是對《詩三百》以來的正統儒家詩教的繼承,著重強調樂府詩批判諷喻的政教功用。
另一方面,樂府的審美功用對于其政教功用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就自創新題而言,元稹對“新題”的要求不僅僅是不再依傍“古題”,而且是新的詩題必須詩人自己首創。宋代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將樂府詩分為十二類,其中有《新樂府辭》一類,郭茂倩云:“新樂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辭實樂府,而未常被于聲,故曰新樂府也。”[3]明代胡震亨在《唐音癸簽》也區分“新題樂府”與“古題樂府”道:“樂府內又有往題、新題之別。往題者,漢、魏以下,陳、隋以上樂府古題,唐人所擬作也。新題者,古樂府所無,唐人新制為樂府題者也。”[4]郭茂倩是南北宋之交時人,他對樂府的理解、分類完全是從音樂出發,他所說的“新樂府”與元稹所主張的“新樂府”概念并不一致,郭茂倩不關心詩歌的內容,只從音樂性的角度出發,定“新樂府”為“唐世新歌”。胡震亨襲郭茂倩之說,定“新樂府”為“唐人新制”。就詩題而言,郭茂倩的新題指“唐代首創”,而元稹對新題的要求是詩題必須自己首創。因此才會出現元稹自稱的19首古題樂府《和劉猛古題樂府十首》和《和李馀古題樂府九首》中,只有8首:《冬白纻》《將進酒》《董逃行》《俠客行》《當來日大難行》《出門行》《筑城曲》《估客樂》被郭茂倩作為古題樂府收錄。另外有11首:《夢上天》《采珠行》《憶元曲》《夫遠征》《織婦詞》《田家行》《君莫非》《田野孤兔行》《人道短》《苦樂相倚曲》《捉捕歌》被收入“新樂府辭”。
其實,早在魏晉時期,文人寫樂府詩就已經有根據詩意另立新題的,如三國時期曹植的《齊瑟行》、西晉張華的《游俠篇》等,但畢竟都是偶爾為之,未成氣候。一直到唐代,自立新題創作樂府詩才逐漸流行,如劉希夷的《公子行》、王維的《老將行》、《桃源行》、李白的《江夏行》等等,都是新題樂府。這類新題樂府的內容,或吟詠古事,或出諸想象,并未用來反映社會時事,至杜甫才真正“即事名篇,無復依傍”,創作出《哀江頭》、《悲陳陶》、《悲青坂》、《哀王孫》等一系列新題樂府名作來反映社會面貌,開創了唐代創作新樂府的風氣,展現了樂府詩歌的審美功用。
綜上所述,元稹樂府觀的政教功用是審美功用的最終目的,而審美功用促進了其政教功用的實現,二者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共同促進了樂府詩歌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
三、元稹的樂府藝術觀
由于對詩歌內容“緣事而發”、“諷興當時之事”、“刺美見事”、“即事名篇”等的要求,元稹利用其在《鶯鶯傳》中擅長的敘事寫法來創作樂府詩。元稹的樂府藝術觀則主要體現在其樂府詩歌敘事的虛構性、悲劇性和諷刺性。
第一,元稹秉承著現實主義精神,通過敘事的虛構性手法,使其創作的樂府詩的藝術真實大大超過了事實的真實,起到了諷喻美刺的政教功用。根據陳寅恪先生《元白詩箋證稿》對《連昌宮詞》的考證,此詩的主要情節純屬虛構。元稹創作《連昌宮詞》的時間為元和十三年(818年)暮春,正在四川地區擔任通州司馬,此時詩人正是帶罪之身,根本沒有機會、也未曾去到連昌宮,唐明皇和楊貴妃生前也從未入住過連昌宮,所以詩中“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憑闌干立。樓上樓前盡珠翠,弦轉突煌照天地。歸來如夢復如癡,何暇備言宮里事”[5]等純屬虛擬想象之詞,是典型藝術創作的結果,但具有歷史真實性。詩人運用這樣一種虛構性藝術手法,形成其樂府詩獨特的風格特色。
第二,元稹一生仕途坎坷,并且經歷了早年喪父、中年喪妻、晚年失子的悲痛,奠定了其樂府詩的悲劇性,尤其體現在其對下層人物苦難命運的安排上。織婦、征夫、琵琶女、宮女、采珠人、田夫等這些都是苦苦掙扎在厄運中的苦命人,包括詩人自己的命運也是苦難的。在這樣的悲劇性命運結局的處理下,盡管會使他樂府詩中的人物形象模式化、單一化,但是這樣不僅可以達到樂府詩諷喻的政教功用,更貼近下層百姓的生活,增強詩歌的人民性。
第三,元稹的樂府詩無論新題還是古題,都反映了其諷刺性,他以興諷手法辛辣地諷刺了當權者的昏聵無能。陳寅恪先生這樣描述詩歌創作背景:“自安史之亂后,吐蕃盜據河漁以來,迄于憲宗元和之世,長安君臣雖有收復失地之計圖,而邊鎮將領終無經略舊疆之意志。此詩人之所以共深憤慨,而元白二公此篇所共具之歷史背景也。”[6]在這樣紛亂的社會背景下,元稹的樂府詩中更多表現的是對邊將不思進取、茍且偷安的憤慨,希望朝廷能重整旗鼓,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如其《縛戎人》詩中:“緣邊飽艱十萬眾,何不齊驅一時發。年年但捉兩三人,精衛銜聲塞溪潘。”[5]詩中描述了天寶年間的禍亂和守城主帥不負責任的棄城行為給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直接批判了朝廷的無能,僅每年捉兩三個蕃人以此邀功,諷刺了戍邊將領碌碌無為卻樂于請賞的丑惡嘴臉。諷刺時事的特色鮮明,有以前朝之事來作為本朝的借鑒,也有以當前的時政加以諷諫的。無論是新題或古題的諷刺性,都符合樂府詩反映時代盛衰、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這一功用,都反映了樂府詩諷喻的政教功用。
由此可見,元稹利用樂府詩體來寫作諷諭詩,針砭現實、改良政治。其敘事的虛構性、悲劇性和諷刺性則使其樂府詩進一步充分發揮了批判諷喻的政教功用,具有經久不衰的魅力。
四、元稹樂府觀的影響
元稹的樂府觀對傳統樂府有繼承也有創新,是對樂府創作的一次新的改革,為后學無論是在文學理論,還是在創作實踐上都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首先,元稹樂府觀對其詩學觀和詩歌創作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他對諷喻功利的主張。元稹將其所作大致分為古詩和律詩兩個大類,其中古詩又包含古諷、樂諷、古體、新題樂府四小類,律詩又包含五言律詩、七言律詩、律諷三小類,再就是特殊題材的悼亡、今體艷詩、古體艷詩三小類。我們由此可以看出其中諷喻之作所占比例甚大,包括古諷、樂諷、新題樂府、律諷,他是強調諷喻詩的價值居各類詩歌之首的,而且元稹說他作艷詩的目的是“以干教化”,那就也有諷喻之意。元稹在其《古題樂府序》中,進一步提出了“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后代之人”、“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的文學口號。當元稹說見到劉猛、李馀的古題樂府,發現這些古題樂府或“雖用古題,全無古義”,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咸有新意”,除了題目之外,既有新詞又有新意,符合新樂府的創作精神。盡管元稹宣稱他與白居易、李紳早就不寫古題樂府了,但依然“選而和之”。說明元稹主要還是強調樂府應充分發揮其“補察時政”的政教功用,感上化下,為政治服務,走現實主義道路。
其次,中唐樂府觀也受到了元稹樂府觀的積極影響。詩至唐代,經歷了唐初的宮體,“四杰”、陳子昂的改革,王維、孟浩然的發展,李白、杜甫的耕筆不輟,終于達到了鼎盛時期。輝煌過后,也就不可避免地進入了低迷時期,這時如何復興就成了當時士人的全部憂思所在。中唐大歷十才子等詩人都嘗試過改革,追求過創新,但都沒有收到太大的成效。元稹卻看到在當時異常尖銳的社會矛盾下,發揮樂府詩歌的諷喻功用才是正道。元稹的樂府觀進一步促進了唐代新樂府運動的開展,具有直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影響。他們或“寓意古題”,或效法杜甫“即事名篇”,以樂府古詩之體,改進當時民間流行的歌謠,積極從事新樂府詩歌的創作。元和四年(809),李紳首先寫了《新題樂府》20首(今佚)送給元稹,元稹認為“雅有所謂,不虛為文”,于是“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寫作了《和李校書新題樂府》12首。后來又創作了《田家詞》、《織婦詞》等,并在《古題樂府序》中將其樂府觀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對新樂府運動有極大的推動作用,從而促進了中唐樂府觀向正確的道路發展。
再次,元稹的樂府觀中所推崇的新樂府,對樂府學及后世樂府創作帶來了建設性的影響。與古樂府比較起來,新樂府具有三個鮮明而突出的特點:一是用新題。它改變了建安以來文人襲用古題寫作樂府詩的傳統,自創新題,便于更直接、更廣泛地反映現實,故又名“新題樂府”。二是寫時事。新樂府專門“刺美見事”,即反映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現實的問題。三是新樂府并不以入樂與否為衡量的標準。新樂府雖稱作“樂府”,但并不入樂,從音樂角度看是徒有樂府之名,而在內容上則是直接繼承了漢樂府的現實主義精神,是真正的樂府。同時,元稹他們所開創的新樂府運動精神,也為晚唐詩人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所繼承。皮日休的《正樂府十首》和《三羞詩》,聶夷中的《公子行》,以及杜荀鶴的《山中寡婦》、《亂后逢村叟》,深刻地揭露了唐朝末年統治者的殘暴、腐朽和唐末農民戰爭前后的社會現實。
總之,元稹的樂府觀除了對他自己詩學觀和詩歌創作有直接影響以外,還對中唐樂府觀、樂府學以及后世樂府創作具有建設性的指導意義,使儒家知識分子通過新樂府創作這一途徑來寄托那份對朝廷的責任和對百姓的關心。
[1]〔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卷二十九)[M].北京:中華書局,2007.
[2]〔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3]〔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十一)[M].北京:中華書局,1979.
[4]〔明〕胡震亨.唐音癸簽[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5]〔唐〕元稹.元稹集(卷二十四)[M].北京:中華書局,1982.
[6]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陳寅恪集[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