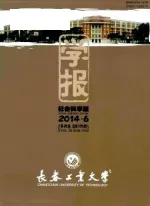《葛特露和克勞狄斯》中的后現代性探析
艾利敏
(江蘇大學 外國語學院,江蘇 鎮江212013)
約翰·厄普代克是美國文壇頗負盛名的作家之一。上個世紀中期,他以小說“兔子四部曲”開始進入大眾讀者視野,由此被稱為“兔子作家”。隨后,他發表了一系列小說、詩歌等,獲得無數贊譽,逐步躋身美國主流文學作家之列。《葛特露和克勞狄斯》這部典型的后現代主義作品,是他的第十九部作品。小說一經出版即引發了激烈的爭論與探討,于2000年被《紐約時代周刊》評為十大最佳圖書之一。
本文運用后現代性中的互文性和解構性,聯系當時男權制的社會矛盾及蓬勃發展的女性主義思潮,深刻分析小說中人物性格特征、不同時期的心理特征及情感走向,試圖揭示《葛特露和克勞狄斯》所要表達的豐富內涵。
一
后現代主義于上個世紀60年代興起于一些主要的歐美國家。隨著科學技術革命和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西方國家陸續進入“后工業社會”,在文化形態方面成為“后現代時代”,而隨之流行的后現代主義對這些國家的科學、文化、生活等領域產生了根本性變化,并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的文化思潮。總的來說,后現代主義是現代主義內部的一種逆動,是對現代主義的純理性的反叛,它摒棄了現代主義的根本基礎,對社會及傳統及文化等方面進行批評和重新定位。上個世紀后半葉,邏各斯被認為是存在于世界的基本準則。歐美哲學家們認為它是主掌世界萬物的神靈,并促使這個世界合理而有序地運行,所有人都應該遵循邏各斯的運轉邏輯,若不尊崇則將走向謬誤之路。邏各斯在西方世界風靡的同時,結構主義也得到了迅猛發展,最終,解構主義在這個時期內應運而生,并得到進一步發展,從而成為了后現代主義的基本理念之一。解構主義對長時間存在于社會當中的正統理論和正統標準進行了強烈有力的否定與批判。它要求摒棄現有的僵化的社會秩序和思想意識,形成新的文學形式。后現代主義學者認為,小說的作者不僅是其作品的著作人,還明確告訴讀者們小說是文字游戲,是虛構的,同時引領讀者們走進這個虛構的空間。德里達解構主義指出,文學作品的完成,意味著在場的消失和死亡,于此同時又在讀者閱讀中開始重建。這種文學作品在場的消失和重建也是其擺脫邏各斯主義束縛的表現。
《葛特露和克勞狄斯》是后現代主義代表作品之一。《葛》改編自莎士比亞的經典作品《哈姆雷特》,主要呈現《哈姆雷特》之前幾十年的場景,即他的母親葛特露和克勞狄斯在王宮中發生的情感生活。故事發生在宮廷之中,但作者有意淡化政治,對政治之事的描寫一筆帶過,濃墨重筆于生活在宮廷之中人物的情感內心。故事的開端,哥特露的父親要求她下嫁給霍文迪爾。這場婚姻的實質其實是葛特露父親與霍文迪爾的一場政治交易,葛特露只是這場交易中的犧牲品。葛特露父親逝世后,霍文迪爾成為丹麥國王。他登基后忙于國家政事,婚后葛特露和國王的婚姻生活不盡人意。兒子性格憂郁冷淡,母子之間沒有深刻的感情。在富麗堂皇的皇宮之中,葛特露的內心孤獨寂寥,而國王的弟弟馮貢,也就是克勞迪斯,愛上了葛特露,葛特露對馮貢慢慢開始心生愛慕,冰封多年的心也開始隨之瓦解。第二部分中,哈姆雷特離開丹麥,遠赴他鄉求學,馮貢歸國,兩人之間少了距離的牽絆,感情更是迅速升溫,如膠似漆。紙里包不住火,這段感情最終東窗事發。千鈞一發之際,馮貢毒死了自己的哥哥。第三部分中,馮貢登上王位,并改名為克勞迪斯。葛特露得成所愿,與克勞迪斯成婚。而從國外趕回國為父親吊喪的哈姆雷特卻對繼父充滿憎恨,不愿與他們生活在一起。葛特露希望兒子能與大臣的女兒結婚,在王宮里過上快樂的生活。
二
互文性主要用于多個文本中,強調它們之間的互指以及影射。此處的文本有兩個方面的意思:狹義上指具體的文學文本,廣義上指如音樂、美術、新聞等一系列有意義的符號實體。在本文中,這兩方面的含義兼而有之。一般來說,互文性具體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指最終文本和與之相關的其他的文本之間的引用、改寫、吸收等轉化關系;另一方面,它強調文本間都具有互文性,所有的文本都是相關的。一個文本和同時期的或者之前的文本都具有互文關系。不同時期的作家對于文章的撰寫都是在先前文本的基礎上,或多或少的受到了比如文化氛圍或寫作風格等方面的影響。
朱莉亞·克里斯蒂娃最早提出互文性,并對其進行了一番描述。她認為:“不同的引文進行拼聯之后形成了我們所看到的文本。”而這個文本實際上是吸收了其他文本,并對之進行合理而適當的轉化。這也就是說,每個文本就像是一面鏡子,而不同的文本也就是很多面不同的鏡子,這些鏡子彼此間相互映射,最后構成了一個網絡。在這個網絡中,不同時期和不同形式的文本相互滲透,促進了文學符號學的發展進程。
巴赫金曾指出文本間具有“對話性”,朱莉亞·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也強調了這一點。她認為所有的文本都不是相互隔離的,它們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并將各種不同的文化文本進行重新組織和編寫。這些文本都蘊含了不同文化文本中所體現的不同的思維觀點,它們將其糅合,并進一步深化。她同時也認為,互文性不僅存在于文學作品中,它也存在于非文學中。
《葛》同《哈姆雷特》兩個文本,在故事發生背景、角色及各角色間的關系糾葛等方面均存在互文性關系。兩部小說皆取自在丹麥廣為流傳的哈姆雷特的故事。厄普代克在創作該小說時,參考了很多莎士比亞以前用過的資料。故事發生背景都在丹麥皇宮中,小說中的場景,如故事發生地點都是一樣的。書中人物均為哈姆雷特、葛特露、克勞迪斯等。小說中人物關系一脈相承,《葛》結束時故事人物之間的關系和情感糾葛是《哈姆雷特》故事背景的開端,《葛》可以看作是《哈姆雷特》的前傳。《葛》從這一點開說,豐富了《哈姆雷特》故事發生的背景,充實了故事中失語的他者。讀者對兩部小說進行遷移閱讀,有助于進一步了解小說中人物的復雜豐富的內心世界,探析人物之間情感糾葛的由來。
《葛》與當時的創作背景,即女性主義,也存在著互文性關系。上個世紀后期,后現代女權主義時代已經到來。而與之相應的女權主義文學也蓬勃發展開來。當時男權制文化在文學作品中占主導地位,影響著人們的思想意識和社會生活。而女性主義文學家希望改變被歪曲的文學世界,給予女性自我表達的權利,使女性在思想上重新認清自己,實現自身的價值,進而改變當時的以男權為中心的社會,使男性和女性在文化領域處于平等地位。雖然這種變化是文學上的,但它在影響女性的思維方式和文化意識的同時,也相應地促進了人類社會的共同進步。這場氣勢恢宏的后現代女權主義思潮被作家厄普代克捕捉到了。他思維敏銳,與時俱進,很快著出了這本嘉獎無數的小說《葛》。這本小說很顯著的特點之一就是以另一視角,即女性的視角對故事進行敘述。它同時也是后現代女權主義的典型代表作品,其中很多后現代女權主義理論在這本小說中均有涉及。
這篇小說中,男性是占有絕對的主導地位的。葛特露作為一位男權社會的被壓迫者,經常受到來自語言等方面的攻擊與羞辱,這些攻擊主要是來自于她的父親、丈夫以及第二任丈夫。在小說的字里行間都能體現出,她是男權社會的受迫害者。實際上,在小說中她經常通過話語來表達自己對男權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的反抗思想。
葛特露在與功臣霍文迪爾結婚之前,就具有很強的女性主義意識,她對男權社會是很有抵觸的。她認為男女平等,女人不應該任人擺布,女人在教育、經濟和社會生活等方面應該擁有同男人一樣的權利,女人不是男人的附庸。當她的父親要求她跟霍文迪爾結婚的時候,她說自己就像皇宮的飾品一樣,除了是國王的女兒以外,什么價值也沒有。在她看來,霍文迪爾驕傲自大、傲慢無禮,把她作為男人打仗時的戰利品,對她只是冷漠的敷衍。她認為霍文迪爾娶她不是真正的愛,只是男人的虛榮心而已。在女英雄塞拉為國家犧牲以后,她的父親認為國家失去了一名女性并沒有什么大不了,男人的犧牲比女人的犧牲有價值得多。對于這種明顯對女性鄙夷的態度,葛特露對此表示強烈的反對。
三
在20世紀60年代,德里達受海德格爾的影響,不僅批判結構主義,也反對當時頗負盛名的邏各斯主義。他從語言學和符號學兩個方面著手研究,最終提出解構主義這一理論。解構主義,也被稱為后結構主義。德里達認為,世界是多元化的,并非二元的。世界處于不停的運動當中,在這種永不休止的運行狀態里,世間的萬事萬物一直經歷著創造,毀滅,再創造,并在這種狀態下生生不息。因此他反對形而上學,反對僵化的試圖強調世界是永恒不變的理論。在解構主義之前,形而上學已經在西方主導了幾千年,這種觀念在人們內心深處早已根深蒂固,限制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和思考模式。上世紀,隨著語言學在諸多方面的突破性進展,人們逐步認識到語言同人的內在意識之間的關聯性。敏銳的德里達從語言學的角度找到反對邏各斯主義的突破點。在小說《葛》發生的時代背景中,男女不平等,等級制度森嚴,女性沒有選擇的自由,女性的內心意識被父權制和男權制社會所壓制,而解構主義主要反對二元對立,反對權威,反對等級對立等,這些思想在厄普代克的小說《葛》的主要人物中得到了體現。
在這個經典的復仇故事中,作者別開生面,以女性的角度重新詮釋了自己對該故事的理解。作者根據女性主義理論和后現代主義理論,重新塑造故事中的人物性格特征,尤其是女主人公葛特露。她在故事中的角色不斷轉變,她婚前身份是女兒,婚后作為妻子、母親和皇后,后來身份轉變為別人的情婦。在她身份的諸多轉換之中,她的人生之路和感情生活不斷曲折發展,故事情節也隨之不斷鋪陳發展。她在人生之路上不斷前行時,她的內心世界也不斷改變。她不斷尋找自我,希望通過自己獲得人生的選擇權。在當時等級森嚴、男性女性地位懸殊的情形下,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而已,地位低下。葛特露不僅渴望擺脫這樣壓迫的生活,更渴望擺脫父權制和男權制的束縛,獲得女性的獨立人格和自由的生活。
小說中,葛特露曾經受馮貢的邀請,去看他的獵鷹。馮貢告訴她,獵鷹都是雌鷹。在參觀獵鷹的過程中,葛特露突然發現有一只鷹的眼睛竟被針線縫了起來,她對此感到非常驚訝和恐懼。馮貢安慰她說,這是為了保護這只鷹,鷹看不見對鷹本身是有益處的。身處在黑暗的世界中,鷹才會安靜,否則它會為了回到自由的天空而拼命掙扎,性格也會變得躁動易怒,這樣不易被馴服。葛特露看到,鷹的爪子被系上了鈴鐺。馮貢解釋說,鷹的脾性敏感而復雜,訓鷹人通過這鈴鐺時時刻刻關注著鷹的行動狀態。正因為鈴鐺對鷹的限制,訓鷹人才能更好地馴服獵鷹。葛特露內心深處不禁唏噓不已,女人就如同那雌性的盲眼的鷹。無盡的黑夜壓抑著那顆渴望重回自由天空的心,而沉重的鈴鐺使自己行動笨拙。訓鷹人訓鷹就像“男人用誓言降服女人一樣”。這鷹和女人雖同為雌性,物種不同,命運卻同樣的悲慘,不由自己掌控。她的丈夫有一次在戰場上強奸并殺害了一名敵國的女性,她對此表達了強烈譴責:“沒有女性是愿意作為裝飾品,被人作為交換的物件,肆意處理,最后被踩在腳底下。”
在當時的父權制和男權制主導的社會環境下,女性的任何反抗都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但在壓抑生活下的葛特露,仍然還有對生命自由的向往,最終放棄了沒有任何感情的婚姻生活,同克勞狄斯相戀,追逐自己的幸福生活。在這方面,厄普代克從深層次角度解構分析了在當時占據主流的女性觀、世界觀和人性善惡觀。女性以前是被男性評說的,這個現象在《葛》中不復存在。葛特露以主人公的地位傾述著自己的苦悶與心傷。讀者對她的態度也由鄙夷轉向理解和同情。厄普代克在書中指出,道德具有歷史性、模糊性和相對性,而且人性是矛盾而又復雜的。因此,非善即惡兩極性的絕對善惡觀也被摒棄。
這個故事由葛特露為敘述者,也就意味著原故事以哈姆雷特及其父親為中心的故事建構的轉移。哈姆雷特的父親失去了在《哈姆雷特》中的絕對發言權。在《葛》中,主人公葛特露用直白的語言譴責老哈姆雷特的濫殺無辜、暴虐的脾性。她指責道:“你雖然戰功顯赫,卻四處燒殺搶奪,帶領著那些暴徒一樣的士兵,還有那些只會禱告的僧人。我甚至能從你的一言一行中覺察出你的殘忍冷酷以及剛愎自用。”[3](P213)老哈姆雷特在莎士比亞著作里面如神靈一樣光輝偉大的形象在《葛》中被葛特露揭露的無處遁形,他那殘忍冷酷,充滿陰謀算計,又詭計多端的不為人知的一面就這樣赤裸裸的呈現在讀者面前。他不僅是一個不擇手段追逐權力和政治的國王,也是一個對待妻子不甚體貼的丈夫。
在莎士比亞筆下,主人公哈姆雷特是“一朵萬眾矚目的嬌嫩的花兒;他是當時社會的明鏡、倫理道德的典范、世人所驚羨的中心”。這些無與倫比的高尚品質在《葛》中卻消失殆盡,不曾表現出點滴分毫。通過解構后的中心人物葛特露的口中,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哈姆雷特只是一位冷漠傲慢,對待親人也不近人情的王子而已。總而言之,哈姆雷特及其父親在《葛》中被重新建構,之前為人所稱贊的、光輝的、正面的形象被徹底顛覆。
在《哈姆雷特》中,克勞迪斯被塑造成了一個謀權篡位的人,這一點從老哈姆雷特對他的嘲諷、貶低、責罵等方面可以看出來。正是這種發自老哈姆雷特單方面的言語,使大批讀者先入為主的站到了老哈姆雷特的陣營當中,認為克勞迪斯是一個“無能的人”。而在《葛》中,敘述者開始質疑老哈姆雷特獲得王權的合理性。從一定層次上說,老哈姆雷特國王的位置只是他通過政治聯姻謀取的。如果不是他如此有心機的策劃聯姻,最后有資格真正坐上國王寶座的人可能就是克勞迪斯了。厄普代克筆下的克勞迪斯被賦予了更多特質,這些特質是老哈姆雷特遠不能比擬的。從領導國家來說,他有著卓越的軍事能力和政治指導才能;從戀人的角度來說,他是一個好男人,他讓葛特露擁有真正的愛情并成為一個幸福的女人。
四
《葛特露和克勞狄斯》一經出版,當即進入到暢銷書行列,獲得了無數嘉獎贊譽。作者運用獨特新奇的筆法,通過后現代主義理論中的互文性和解構性,重新詮釋了葛特露這一人物形象以及她的情感生活,表達了作者對于社會生活中男權統治的譴責和批判。小說揭露了女性長期被男權制壓抑的生活情形,突出反映男女不平等的社會現實。它從男女性別差異方面,真實揭露了故事中的兩性差異,顯示了與前人不同的價值判斷理念。厄普代克通過作品反映時代社會矛盾,并希望通過文學的方式來改善社會上的兩性地位和觀念,無疑是十分具有人性化的。另一方面,這部小說在人物描寫和新穎獨特的敘事視角等方面均透露出明顯的后現代主義氣息,是后現代主義小說的代表作。
[1]Updike,John.Gertrudeand Claudius [M].London:Penguin Books,2000.
[2]opate,Leonard.TheWriting Life and Times of John Updike[A].in The Writer[C].Vol.114.No.7.New York,2001.
[3]〔美〕約翰·厄普代克.葛特露和克勞狄斯[M].楊莉馨,譯.北京:譯林出版社,2002.
[4]〔法〕蒂費娜·薩莫瓦約.互文性研究[M].邵偉,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5]〔英〕威廉·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全集[M].朱生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
[6]張曉琴.《葛特露和克勞狄斯》的互文性解讀[D].臨汾:山西師范大學.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