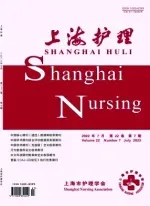產后抑郁相關危險因素及護理研究進展
朱春香
(復旦大學附屬婦產科醫院,上海 200090)
產后抑郁癥是指產婦在分娩后出現的一種精神和行為失調癥狀,是產褥期精神綜合征中最常見的一種類型[1]。產后抑郁癥涵括了產后心緒不良、產后抑郁癥以及超出產后心緒不良界限又未達到產后抑郁癥診斷標準的產后抑郁狀態[2]。于產后6周內起病,通常持續3~6個月,但也可持續1~2年。近年來,國內外對產后抑郁癥的研究比較重視,尤其對產后抑郁癥的相關因素及護理的研究更為深入,取得了重大的進展。現將有關文獻綜述如下。
1 產后抑郁的患病率及危害性
產后抑郁患病率高,影響人群巨大。據報道,國外產后抑郁癥的患病率為3.5% ~33.0%;國內為13.1% ~16.3%[3-4];再次妊娠則有 20% ~30%的復發率[5]。尤其是既往存在經前綜合征的患者更為多見。Garcia-Esteve等[6]研究認為,經前綜合征被確認為產后抑郁癥的一個獨立的危險因素。研究認為,產后抑郁癥不僅影響產婦的身心健康,而且影響母親的能力來照顧嬰兒和伴隨的負面影響孩子的身心發育及行為發展[7]。產婦在抑郁狀態下泌乳延遲,乳汁分泌較少,嚴重影響嬰幼兒的身體發育與行為、認知和情感的發展,甚至成為新生兒猝死綜合征的誘發因素之一[8]。產后抑郁癥是一個重要的心理健康問題,影響到婦女本身,還影響夫妻關系以及整個家庭和社會[9]。同時,產婦在抑郁狀態下體內去甲腎上腺素分泌減少,導致子宮收縮乏力,可誘發產后出血。人際關系協調障礙,喪失熱情與信心,甚至出現自殺或擴大性自殺現象。
2 產后抑郁癥的相關危險因素
2.1 生理因素 產后心緒不良與體內內分泌的改變和某些神經遞質的改變有關,發生率相當高,約有一半以上的女性在產后出現這種情況[10]。內分泌的變化主要是孕激素和雌激素水平在產后突然下降;研究發現,雌激素的變化致使腦內和內分泌組織的兒茶酚胺減少,影響神經遞質的變化,容易引起情緒波動,從而出現抑郁癥狀[11]。而孕激素減少導致類似于苯二氨芷類藥物突然戒斷,促進抑郁情緒發作[12]。產后血清甲狀腺素水平迅速下降,產后T3<140 ng/mL的產婦為產后抑郁癥的高危人群,推測甲狀腺功能降低可能為產后抑郁癥的發病因素之一[13]。
2.2 遺傳因素 有專家從遺傳學的角度分析,認為產后抑郁癥屬于內源性抑郁癥,發病的主要原因是遺傳及生理因素。有經前期緊張史和產前抑郁癥;親屬有精神病史和產后抑郁家族史者容易發生。研究顯示,許多情況下產后抑郁癥從妊娠期開始,產前抑郁癥是產后抑郁癥最重要的危險因素,產前抑郁產婦發生產后抑郁的幾率明顯高于無產前抑郁患者[14]。懷孕前已有抑郁癥但未及時發現,其產后發病的可能性高達30%以上[15]。研究發現,有抑郁癥家族史的女性中產后抑郁癥的患病率高[16]。
2.3 心理因素 由于產婦缺乏對分娩過程的正確認識,家人對孩子期望值過高,對嬰兒是否健康、有無畸形、嬰兒性別是否理想等的擔憂無形中給產婦帶來很大的心理壓力。
2.3.1 個性因素 性格內向的產婦,個體素質有神經質、不成熟人格或強迫人格,平時又不善于處理人際矛盾,產后發生此癥較多。袁冬梅等[17]研究發現,孕產婦心理不健全、孤僻自卑、不合群、謹小慎微、易鉆牛角尖、愛猜疑和不善表達等,這些人群易發生產后抑郁癥。年齡偏小或偏大的初產婦,容易發生產后抑郁,可能是由于年齡偏小的婦女生活閱歷淺,還沒有從過去的孩子角色中脫離出來,對承擔母親的角色不適應。有證據表明,產后抑郁癥患病率在青少年可能會更高[18]。在產后2~3個月,青少年產后抑郁癥患病率為25.9%,而成年人是9.3%[19]。而年齡偏大的產婦又因過分擔心自己年齡偏大,害怕難產,在分娩前及分娩時精神高度緊張,分娩后擔心母乳不足和育兒困難等導致心理壓力增大。
2.3.2 角色缺如 從懷孕到產后,產婦經歷了多角色的迅速轉換,產婦對母親角色缺乏認同或產生沖突和適應不良,無法克服做母親的壓力。韓思敏等[20]研究表明,角色的突然轉換考驗著產婦的心理適應能力和承受能力,產婦的心理因此發生變化。特別是產后1周情感變化明顯,心理處于嚴重的不穩定狀態,未進入母親角色,擔心孩子缺乏家庭成員和社會的關心。張穎等[21]研究顯示,孕期心理準備越充分則產后抑郁癥狀檢出率越低,即在孕期對母親角色、產后休養、孕期和產后工作安排、孕期和產后經濟等問題做好了充分心理準備,則產后抑郁癥的患病率大大降低;反之亦然。
2.3.3 心理壓力 分娩前對可能出現的情況估計不足,尤其初產婦缺乏護理喂養新生兒的知識和技巧,對孩子哭鬧手足無措,嬰兒喂哺困難;并且產后身體的各種不適,產婦會覺得委屈,產生煩心、焦慮的情緒。產婦擔心自己照看不好嬰兒,又因為照顧嬰兒導致睡眠失調,從而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研究表明,非計劃妊娠的女性沒有為孩子的出生做好孕前、孕期和產后的準備,就增加了產后的心理壓力,增加了產后抑郁癥的患病率[22]。
2.3.4 形象壓力 生產后,產婦因為體形發生改變,若心理調適不當,可能會產生憂郁情緒。張國琴等[23]研究顯示,孕前體重指數及其孕期體重指教的變化是影響產后抑郁的重要因素,肥胖產婦比正常產婦更容易發生產后抑郁。
由牽引力公式可知,牽引力大小是由氣流特性和紗線特性決定的,氣流特性由氣流密度ρ和氣流速度V組成,紗線特性由紗線直徑和紗線阻力系數CD組成。由于輔助管道中氣流參數相對比較穩定,可知突出物通過改變紗線直徑和紗線阻力系數CD來影響牽引力的大小。
2.4 社會因素
2.4.1 家庭因素 家庭支持是一個主要因素,包括丈夫家人支持及其本人對婚姻的滿意程度。懷孕后得不到丈夫的關心愛護,是產后發生抑郁的不利因素。在產后抑郁中丈夫的角色非常重要,產后家庭關注重心的轉移及丈夫的體貼不夠,且自己的身體正處在調養和恢復階段,生活習慣的改變和再適應,如果得不到家人的體諒和幫助,會使產婦感覺委屈、煩躁、疲倦和焦慮,產生失落感。傅紅珠[24]研究表明,缺乏家庭的支持和幫助,尤其是缺乏丈夫的支持,是產后抑郁的危險因素。家庭矛盾、夫妻關系不和、產后缺乏家屬和親人朋友的關心是促進產后抑郁癥的危險因素。
2.4.2 經濟因素 孕產婦生活條件,如住房擁擠和經濟困難等可導致情緒低落;家庭經濟狀況是影響產后抑郁的又一重要因素,家庭經濟優越的女性不必為孩子出生及撫育的費用擔憂,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產后的壓力,減少了產后抑郁的發生。研究表明,婦女產后情緒變化多由于生活條件造成,產后抑郁癥與近期應激生活事件有關,夫妻分離、親人喪亡、住房擁擠和經濟困難等均與產后抑郁癥的患病率有關[25]。
2.4.3 缺乏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和社區護理不完善,從醫院獲得的信息也不足以滿足其信息需求,家庭中可以幫忙照顧產婦和小孩親屬也極其有限,產后自己又缺乏育兒及自我護理的經驗和知識,造成精神上的壓力,從而導致產后抑郁。女性在分娩過程中非常脆弱,她渴望得到醫護人員的幫助,醫務人員的言語、態度和行為可影響和改變產婦的情緒和狀態,如果態度生硬、惡劣會對產后抑郁的發生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潘青葉[26]對75例產婦進行研究,得出夫妻關系不融洽者發生產生抑郁癥的危險性較大。王彩霞[27]對80例產婦研究結果表明,產婦的家庭收入、家庭關系、分娩方式、住院環境及醫院的服務質量等因素、對產后抑郁癥的影響有顯著性差異。
2.5 產科及兒科因素
2.5.1 擔心分娩時的疼痛、能否順利分娩。研究表明[28],分娩方式是產后抑郁癥的風險因素。自然陰道分娩和陰道助產的產婦產后抑郁癥的患病率比緊急剖宮產的低,選擇性剖宮產的風險比緊急剖宮產的高。手術分娩可使產婦產生抑郁和焦慮等消極情緒,剖宮產的婦女產后發生抑郁癥的危險是陰道分娩的6.82倍[7]。剖宮產術,是一種非生理性的過程,孕婦在術前高度緊張和焦慮,擔心并發癥的發生等,對產婦的情緒影響很大。剖宮產術大多較順產者失血多,失血可能導致大腦皮層處于抑郁狀態,故而產后抑郁癥患病率高。
2.5.2 嬰兒是否健康、有無畸形、嬰兒性別是否理想等,使產婦的心理產生不良影響。應用產鉗和胎頭吸引器助產的產婦擔心其對嬰兒產生不良影響,對分娩感到恐懼、緊張導致神經內分泌功能失調,免疫下降等一系列變化,影響產程進展,又進一步加重焦慮、不安情緒。此外嬰兒出現健康問題如畸形、生病和愛哭鬧等都會引起產婦產后抑郁。另外,不良的分娩結局,如看到或接觸死胎和死產嬰兒易產生精神傷害。曾經歷了不良產史的產婦往往精神高度緊張,更易導致產后情緒低落,引起產后抑郁。
2.6 季節因素 分娩的季節也可能增加發生產后抑郁癥的風險。文獻資料顯示,與春夏季相比,產后抑郁的患病率在秋季和冬季更高;由于陽光照射少,從而降低光刺激在視網膜上,從而導致情緒障礙[29]。Yang等[28]對2 107例婦女的研究表明,與其他季節比,產后抑郁癥更可能發生在冬季。
3 護理措施
產后抑郁高發病率及危害性提示醫護人員要充分重視,對于存在抑郁癥的產婦及時發現及時干預治療。從而促進產婦的康復,減少對嬰兒的影響。
3.1 產前護理 一個完善的產前心理社會干預可成功地減少產后抑郁癥。
3.1.1 加強產前保健及教育 從產前檢查開始,向孕婦宣教孕期正常的心理變化;孕晚期每周由資深助產士進行一對一指導,使其了解分娩過程,為分娩做心理和技術上的準備;同時解答有關分娩的疑問,從中獲得相關的衛生保健知識,共同制定分娩計劃,使其有歸屬和依托感。妊娠期健康教育可以降低抑郁,防止產后抑郁應從產前開始,把孕期抑郁情緒篩查和心理健康教育納入常規的產前檢查和宣教內容,產前教育干預可以持續到產后時期[30]。開設孕婦學校,利用圖譜和多媒體讓孕婦學會給嬰兒哺乳、換尿布和洗澡等技能,為孕婦向母親角色的過渡在思想上和技能上做好準備。同時,加強胎兒監測,及早發現畸形兒,避免因畸形兒出生造成產婦沉重的心理打擊。Zlotnick等[31]證明,標準的產前保健加上人際關系心理治療,可有效的降低產婦在產后3個月內重度抑郁癥的發生。
3.1.2 建立良好的醫患關系 孕晚期通過助產士門診,提供咨詢、孕婦與助產士建立信任、伙伴關系[32];產前參觀產科病房熟悉環境,有利于產婦的心理改變,促進護患相互信任[33]。入院熱情接待孕婦,介紹病區環境、床位醫師和責任護士,提倡導樂陪產,對產婦進行分娩過程基本知識的宣教,主動與產婦交談,認真回答孕婦及家人提出的問題,針對孕婦普遍存在的恐懼和焦慮等心理活動進行情感疏導和健康教育,使孕婦情緒穩定。
3.1.3 加強妊娠期營養 日本1項前瞻性研究建議,懷孕期間食用的食物中含有多量核黃素(維生素B2),豐富DHA和高血糖指數膳食(碳水化合物迅速分解,提高血糖)均與降低產后抑郁癥的風險有關[34]。DHA高度集中在腦細胞膜和突觸末端,在神經化學傳遞時起重要作用,對婦女的情緒具有正面的影響[35]。高血糖指數的食物,從而促進胰島素分泌,激化大腦中的5-羥色胺的前體,色氨酸的釋放。由于5-羥色胺水平的升高,抑郁癥狀隨后減弱[36]。
3.2 產時護理
3.2.1 導樂分娩 臨產時由助產士及丈夫陪伴產婦分娩,提供分娩指導和心理支持,收效良好。根據產婦的喜好播放音樂、電視節目,營造輕松舒適的氛圍,分散產婦對分娩痛的注意力;同時關心產婦,協助飲水、進食、擦汗和如廁等生活護理,適時地給予撫摸,指導產婦正確運用腹壓,運用無痛分娩技術,盡可能減輕疼痛及不適。多鼓勵產婦,給產婦以生理、心理和情感上的支持,對產婦丈夫及家屬進行宣教,強調和諧家庭關系及有效的關心支持對分娩和產婦、嬰兒的身心健康的重要性,讓家屬了解并主動參與分娩期間的護理活動,調整好心態,配合醫師的治療和助產士的指導。陸麗等[37]研究表明,采用導樂陪伴分娩可降低初產婦產后抑郁的患病率。
3.2.2 傾聽與討論 在分娩后由助產士與產婦討論分娩過程和經歷,強調產婦對分娩這一壓力實踐所表現的反應是正常的情感變化,教育產婦如何初為人母。對預防產后抑郁癥,有效的干預措施需要盡早啟動,同時要求丈夫共同參與傾聽與交流。資料表明,丈夫的情感支持、言語交流對產婦產后抑郁的預防和改善有重要意義[38]。心理咨詢和形體訓練在緩解產后抑郁上有正面作用。
3.3 產后護理
3.3.1 產后心理疏導產婦 由于分娩消耗體力較大,產后會陰切口痛,剖宮產術后的切口痛,產后更需要有充分的睡眠和休息。給產婦創造一個良好的休養環境,運用護理心理學,社會學知識,適時實施心理干預,減輕心理負擔,增強自信心,提高自我價值意識。雖然產后住院是短暫的,給產婦的教育和新生兒保健的教育,出院前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在護理過程中,護士盡量集中進行治療操作,宣傳母乳喂養的優點,指導母乳喂養及新生兒撫觸,促進母嬰互動情感的交流,教會她們護理孩子的一般知識和技能,使產婦及早進入母親角色。林秀英等[39]認為,對產后抑郁癥產婦的護理主要是防止自殺,因為產后抑郁癥最大的危害是發生自殺。故應做到早識別,早防范,早發現并做好自殺的預測,高度警惕產婦自殺的反常行為。加強產后早期鍛煉,不僅有利于促進產后子宮復舊,還能夠恢復腹部肌肉緊張度,防止乳房下垂和產后肥胖,有利于產后形體的恢復,從而增強產婦的自尊心和自信感。一個全面的出院教育干預包括產婦護理和新生兒護理,提供產后抑郁癥的資料,使產婦在產后保持健康的心理,減少分娩后的心理疾病[40]。
3.3.2 產后家庭訪問鼓勵傾述 許多新媽媽都不樂意談論抑郁癥狀,衛生人員需要關心產婦的健康,由助產士或社區工作者對高危產婦提供生理和情緒的支持,可減少抑郁癥的發生,增加家訪次數,可促進產婦的心理健康。研究發現,產后6周持續給予產婦家庭訪視,產婦了解產后抑郁癥相關信息,在產后3個月得到愛丁堡產后抑郁量表(EPDS)低的評分[41]。目前認為,產后預防不僅對產婦的生理,心理問題進行有效的指導和教育,還能協調家庭,指導其丈夫及父母積極參與照顧產婦,照顧嬰兒及提供物質幫助及精神支持,同時還應提供多方信息指導,正確認識反常心理,解決生活難題,樹立信心,提高心理素質。
3.3.3 其他護理 合理降低住院治療等費用,倡導母乳喂養,減輕經濟壓力,以消除產婦后顧之憂。醫務人員應給予產婦及家屬提供有關信息和技能支持,幫助產婦掌握喂養技巧,照顧嬰兒方法,講解產后保健知識和有關育兒知識等,讓產婦對照料嬰兒和自己充滿信心。同時,還應做好藥物護理,由于抗抑郁用藥初期患者往往有焦慮不安等不適,適當加服安定藥物。用藥必須及時正確,觀察藥物不良反應,告訴患者服用藥物要堅持療程,逐漸減藥,偶爾情緒波動無需緊張。對哺乳的產婦進行藥物治療時,需考慮藥物由乳汁排泄,盡量不用或小劑量使用精神科藥物。此外,安全護理不宜放松,患者自殺多發生在凌晨,要加強這段時間的病房巡視護理,并做好相關的心理疏導,避免事故的發生。
4 小結
產后抑郁癥影響著產婦的健康,危及嬰兒的身心健康,而且影響家庭和社會。令人不安的是,許多產后抑郁的女性仍未被發現,也缺乏適當的治療。因此我國加強產后抑郁研究,針對各種相關危險因素,早期、準確的識別和實施干預具有重要現實意義,有針對性地開展心理促進工作,從而有效地預防和防治產后抑郁癥的發生。
[1]夏海鷗.婦產科護理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7:144.
[2]張玲娟,張靜.婦產科護理查房[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1:216.
[3]邱忠君,汪俊紅,呂翠.孕產婦情緒評估調查與產后抑郁癥預防[J].中國婦幼保健,2010,25(19):2710-2712.
[4]錢耀榮,晏曉穎.中國產后抑郁發生率的系統分析[J].中國實用護理雜志,2013,29(12):1-3
[5]韓愛卿,單瑞芹,李娟.孕期健康教育對產后抑郁癥發病的影響[J].中國婦幼保健,2010,25(30):4345-4347.
[6]Garcia-Esteve L,Navarro P,Ascaso C,et al.Family caregiver role and premenstrual syndrome as associated factors for postnatal depression[J].Arch Womens Ment Health,2008,11(3):193-200.
[7]Yozwiak JA.Postpartum depression and adolescent mothers:a review of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approaches[J].J Pediatr Adolesc Gynecol,2010,23(3):172-178.
[8]謝迅頻.產后抑郁對母體乳汁分泌的影響[J].護士進修雜志,2010,25(8):766-767.
[9]Perinatal Mental Health Consortium.National Action Plan for Perinatal Mental Health 2008– 2010 Full Report[R].Melbourne:beyondblue the national depression initiative,2008.
[10]Brummelte S,Galea LA.Depression during pregnancy and postpartum:contribution of stress and ovarian hormones[J].Prog Neuropsychopharmacol Biol Psychiatry,2010,34(5):766-776.
[11]曹澤毅.中華婦產科學[M].第2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5:295-302.
[12]范學紅.產后抑郁癥發病危險因素研究[J].臨床和實驗醫學雜志,2008,7(5):27,29.
[13]Drevets WC,Todd RD.Depression,mania and related disorders.In:Rubin EH,Zorumski CF,eds.Adult psychiatry[M].2nd ed.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5.
[14]廖妮虹,陳艷,陳秀甜,等.產前抑郁與產后抑郁相關性研究[J].吉林醫學,2012,33(4):713-714.
[15]Pereira PK,Lovisi GM,Pilowsky DL,et al.Depression during pregnancy: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among women attending a public health clinic in Rio de Janeiro,Brazil[J].Cad Saude Publica,2009,25(12):2725-2736.
[16]錢寶鳳.產后抑郁癥的成因分析及預防[J].中國醫療前沿,2008,3(17):110-111.
[17]袁冬梅,李莉.淺析產后抑郁癥的病因及護理干預體會[J].甘肅醫藥,2012,31(12):947-949.
[18]Figueiredo B,Pacheco A,Costa R.Depression during pregnancy and the postpartum period in adolescent and adult Portuguese mothers[J].Arch Womens Ment Health,2007,10(3):103-109.
[19]Schmidt RM,Wiemann CM,Rickert VI,et al.Moderate to severe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adolescent mothers followed four years postpartum[J].J Adolesc Health,2006,38(6):712-718.
[20]韓思敏,許波,何文靜.產后抑郁癥的相關因素分析及護理對策[J].中國醫學創新,2012,9(11):59-60.
[21]張穎,王燕.產后抑郁影響因素分析[J].中國婦幼保健,2008,23(29):4170-4272.
[22]Kheirabadi GR,Maracy MR,Barekatain M,et al.Risk factors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in rural areas of Isfahan Province,Iran[J].Arch Iran Med,2009,12(5):461-467.
[23]張國琴,左彭湘,張瀾.孕前體重指數及孕期增重對產后抑郁的影響[J].現代預防醫學,2008,35(13):2441-2442.
[24]傅紅珠.產后抑郁的原因及護理對策[J].中國現代醫生,2011,49(13):65-66.
[25]Adewuya AO,Fatoye FO,Ola BA,et al.Sociodemographic and obstetric risk factors for postpartum depressive symptoms in Nigerian women[J].J Psychiatr Pract,2005,11(5):353-358.
[26]潘青葉.產婦產后抑郁的原因分析及護理干預[J].臨床護理雜志,2011,10(5):34-36.
[27]王彩霞.產婦產后抑郁相關因素及認知功能護理干預分析[J].護理實踐與研究,2011,8(18):40-41.
[28]Yang SN,Shen LJ,Ping T,et al.The delivery mode and seasonal variation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J].J Affect Disord,2011,132(1-2):158-164.
[29]Yang SN,Shen LJ,Ping T,et al.The delivery mode and seasonal variation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J].J Affect Disord,2011,132(1-2):158-164.
[30]Hiltunen P,Jokelainen J,Ebeling H,et al.Seasonal variation in postnatal depression[J].J Affect Disord,2004,78(2):111-118.
[30]陳靜,王玉瓊.產前心理健康教育對產后抑郁的作用研究[J].護理研究,2011,25(7A):1729-1730.
[31]Zlotnick C,Miller IW,Pearlstein T,et al.A preventive intervention for pregnant women on public assistance at risk for postpartum depression[J].Am J Psychiatry,2006,163(8):1443-1445.
[32]顧春怡,張錚,朱新麗,等.孕晚期干預支持對孕婦產時認知行為及分娩結局的影響[J].中華護理雜志,2011,46(6):569-571.
[33]劉曉光.產后抑郁癥的原因及護理[J].現代護理,2008,14(24):180-181.
[34]Murakami K,Miyake Y,Sasaki S,et al.Dietary glycemic index and load and the risk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in Japan:the Osaka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Study[J].J Affect Disord,2008,110(1-2):174-179.
[35]Miyake Y,Sasaki S,Yokoyama T,et al.Risk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in relation to dietary fish and fat intake in Japan:the Osaka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Study[J].Psychol Med,2006,36(12):1727-1735.
[36]Miyake Y,Sasaki S,Tanaka K,et al.Dietary folate and vitamins B12,B6,and B2 intake and the risk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in Japan:the Osaka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Study[J].J Affect Disord,2006,96(1-2):133-138.
[37]陸麗,代莉,劉嵐,等.導樂分娩對預防初產婦產后抑郁發生的影響[J].護理實踐與研究,2013,10(6):23-25.
[38]畢文香,孫向芹.產后抑郁癥患者與人格、社會支持的相關研究[J].精神醫學雜志,2011,24(4):254–256.
[39]林秀英,林小紅.26例產后抑郁癥的臨床護理分析[J].中國計劃生育和婦產科,2009,l(1):37-39.
[40]Ho SM,Heh SS,Jevitt CM,et al.Effectiveness of a discharge education program in reducing the severity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a randomized controlled evaluation study[J].Patient Educ Couns,2009,77(1):68-71.
[41]Heh SS,Fu YY.Effectiveness of informational support in reducing the severity of postnatal depression in Taiwan[J].J Adv Nurs,2003,42(1):3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