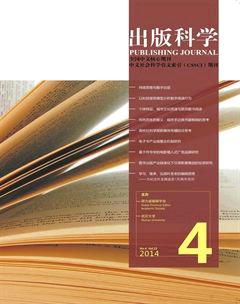余也魯和他的“編輯圣經(jīng)”
2012年9月8日,一代傳播學(xué)大師余也魯教授在香港病逝,享年93歲。為了紀(jì)念這位香港傳播學(xué)的開(kāi)山鼻祖,香港《基督教周報(bào)》[1]、臺(tái)灣燕京大學(xué)都曾有學(xué)者撰文懷念余教授,贊譽(yù)他的學(xué)術(shù)貢獻(xiàn)[2]。其實(shí),余也魯教授不僅開(kāi)香港傳播學(xué)研究、傳播學(xué)教育之先河,而且也是大陸傳播學(xué)、廣告學(xué)、編輯學(xué)研究和教育的先驅(qū)。他1965年出版的《雜志編輯學(xué)》作為我國(guó)第一本研究雜志編輯的書(shū),不但被譽(yù)為“編輯圣經(jīng)”,而且多次再版,影響很大。只可惜大陸至今沒(méi)有人介紹和研究。因此,為了紀(jì)念余教授,本文僅對(duì)余也魯和他的《雜志編輯學(xué)》做一簡(jiǎn)論。
1 余也魯?shù)闹饕獙W(xué)術(shù)貢獻(xiàn)
余也魯,江西奉新人,青年時(shí)代獲美國(guó)名門(mén)高校斯坦福大學(xué)人文科學(xué)院傳播學(xué)博士學(xué)位,師從傳播學(xué)創(chuàng)始人施拉姆教授。學(xué)成后曾任香港浸會(huì)大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院院長(zhǎng)兼?zhèn)骼韺W(xué)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學(xué)講座教授兼?zhèn)鞑パ芯恐行闹魅巍?晚年親手創(chuàng)辦香港海天書(shū)樓及海天資訊企業(yè)、海天基金會(huì)。曾被澳門(mén)東亞大學(xué)、香港基督教嶺南大學(xué)及廈門(mén)大學(xué)、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浙江大學(xué)、江西師范大學(xué)先后頒授榮譽(yù)教授頭銜。
余也魯作為傳播學(xué)大師施拉姆的東方弟子,他的學(xué)術(shù)貢獻(xiàn)主要集中在五個(gè)方面:一是1968年在香港浸會(huì)學(xué)院創(chuàng)辦傳理學(xué)系,被譽(yù)為香港“傳理系之父”。二是1983年幫助廈門(mén)大學(xué)開(kāi)設(shè)新聞傳播系廣告專(zhuān)業(yè),開(kāi)啟中國(guó)廣告教育的先端。三是親手翻譯多本施拉姆傳播學(xué)著作,并陪同施拉姆到中山大學(xué)、復(fù)旦大學(xué)、人民日?qǐng)?bào)社、中國(guó)社科院演講,致力于傳播學(xué)研究的中國(guó)化。四是用傳播學(xué)理論來(lái)闡述解釋《圣經(jīng)》,開(kāi)啟了華人教會(huì)學(xué)者的時(shí)代。五是主編英文《傳播季報(bào)》,出版《傳播教育現(xiàn)代》《雜志編輯學(xué)》《門(mén)內(nèi)門(mén)外——與現(xiàn)代青年談現(xiàn)代傳播》《中國(guó)傳播資料摘萃》等學(xué)術(shù)著作,創(chuàng)辦海天書(shū)樓,在香港中文大學(xué)新聞系講授《雜志編輯學(xué)》課程,是自1949年李次民在廣州出版《編輯學(xué)》、教授編輯學(xué)課程以來(lái),中國(guó)較早從事編輯學(xué)研究和編輯學(xué)教育的專(zhuān)家學(xué)者。
特別是《雜志編輯學(xué)》,有“編輯圣經(jīng)”之稱(chēng)。1965年出版后不久,“便成為每個(gè)做編輯的人的手冊(cè),一再重版”,這是作者始料未及的。作者在1965年初版自序中寫(xiě)道:“辦報(bào)、編雜志、出版書(shū)籍,這三種看似不同但應(yīng)該綜合地加以研究的行業(yè),我都長(zhǎng)期地從事過(guò)。從小記者到老編,從一個(gè)標(biāo)題做到整套叢書(shū)的設(shè)計(jì)與編輯,所遇到的困難,可以說(shuō)屈指可數(shù)。要解決只有靠摸索、靠觀摩、靠實(shí)驗(yàn)……在沒(méi)有專(zhuān)書(shū)可讀、沒(méi)有專(zhuān)師可問(wèn)的情況下,我只有不斷付高昂的‘學(xué)費(fèi),向經(jīng)驗(yàn)學(xué)習(xí)。”正因?yàn)樽髡呱钪O“沒(méi)有專(zhuān)書(shū)可讀、沒(méi)有專(zhuān)師可問(wèn)”的痛苦,才期盼“如果有一本小書(shū)來(lái)綜合已有的雜志編輯的經(jīng)驗(yàn),除了可以幫助雜志的編輯工作外,對(duì)報(bào)紙與書(shū)籍的編輯工作都能有參考的價(jià)值。而這百年來(lái)中國(guó)人自己摸出來(lái)的經(jīng)驗(yàn),也的確早就應(yīng)有一本小書(shū)來(lái)記敘”了。作者熟悉編輯工作,知道編輯辛苦,且有豐富的編輯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有過(guò)得去的編輯本領(lǐng),《雜志編輯學(xué)》才“一再重版”(國(guó)內(nèi)一般見(jiàn)到的是1994年第5版);“它是中文出版物中第一本講雜志編輯的書(shū);但沒(méi)有想到,十五年后的今天仍然是唯一的一本”。足見(jiàn)它在中國(guó)編輯學(xué)研究和建設(shè)中的地位。
2 《雜志編輯學(xué)》的基本內(nèi)容
關(guān)于《雜志編輯學(xué)》的內(nèi)容,由于筆者費(fèi)盡心力也沒(méi)能找到1965年的初版本,只能以海天書(shū)樓1980年12月初版“最新修訂本”為依據(jù)進(jìn)行介紹。
打開(kāi)該書(shū),作者最先向讀者展示的是一句醒世座右銘:“只見(jiàn)讀者,不見(jiàn)自己;只見(jiàn)大眾福利,不見(jiàn)個(gè)人私利,是經(jīng)得住時(shí)代與歷史考驗(yàn)的編輯人應(yīng)該常銘于心的座右銘。”如果說(shuō),為人作嫁、默默無(wú)聞是編輯工作的特點(diǎn)的話,那么,甘愿為人作嫁、甘當(dāng)無(wú)名英雄就應(yīng)該是編輯高尚品格的寫(xiě)照。作者以此作為開(kāi)篇之言,足見(jiàn)其對(duì)編輯的性質(zhì)、編輯工作的特點(diǎn)認(rèn)識(shí)深刻。接下來(lái)是目錄和《新版自序》。在《新版自序》里作者首先闡述了他1965年《初版自序》對(duì)雜志編輯的觀點(diǎn):“報(bào)紙是雜志這個(gè)細(xì)胞中分裂出去的:而初期雜志也可以說(shuō)是自書(shū)籍的細(xì)胞中分裂出來(lái)的。研究雜志的編輯,進(jìn)一步可以編輯報(bào)紙,退一步可以編輯書(shū)籍。”接著,他又詳細(xì)介紹了自1965年《雜志編輯學(xué)》問(wèn)世之后到1980年15年間傳播世界發(fā)生的巨大變化。像雜志功能的演變、雜志媒介的發(fā)展等,他說(shuō):“十五年中變化最大的是工藝,是‘硬件。原來(lái)的第八、九、十章幾乎要全部重寫(xiě)。十五年來(lái)變化最少的是原則、是理論……十五年中,當(dāng)然有若干新的理論上的發(fā)現(xiàn),新的問(wèn)題的出現(xiàn),我把這些綜合起來(lái)寫(xiě)了一章。叫做‘廣告、發(fā)行與專(zhuān)門(mén)化……全書(shū)只比初版多了這一章,列為第十六章。”1980年版相對(duì)于1965年初版,內(nèi)容更加全面,且與時(shí)俱進(jìn)了不少。
全書(shū)共17章。第1章導(dǎo)論,主要是借傳播觀念和傳播工具為雜志編輯理論做鋪墊。作者身為傳播學(xué)大師,開(kāi)篇娓娓道來(lái),通過(guò)生動(dòng)的故事,講述了人與人之間的傳播需求和傳播方式。在作者看來(lái),“作為傳播工具的雜志,若要辦得好,辦得有效,必須先認(rèn)識(shí)這個(gè)工具的性能和它活動(dòng)的過(guò)程。”(14頁(yè))“能夠認(rèn)識(shí)一位傳播者所能做到和所不能做到的,對(duì)我們從事編輯一本雜志的工作,當(dāng)然有極大的幫助。”(18頁(yè))尤其是“傳播工具的比較”和“傳播與社會(huì)”這兩部分,不僅比較了雜志與報(bào)紙、書(shū)籍、廣播、電影、電視的不同,而且還闡明了雜志傳播的特點(diǎn)和規(guī)律。第2章主要講述了雜志、雜志史和雜志的功能。關(guān)于雜志,作者首先試圖下一個(gè)定義:“雜志是定期印刷出版物里的一種,是大眾需要各種生活資料供閱讀,需要智據(jù)作決定,和社會(huì)需要知多識(shí)廣的公民之后的產(chǎn)物。”(27頁(yè))在這個(gè)定義的基礎(chǔ)上,闡述了雜志名字的由來(lái)、“為什么要讀雜志”、“雜志史三百年”、雜志在現(xiàn)代社會(huì)中的功能及其讀者對(duì)雜志、雜志編輯的期待。
第3—17章主要探討的是具體的雜志編輯工作流程和編輯出版知識(shí)。從標(biāo)題看,依次是:編輯政策的制訂;編輯的設(shè)計(jì);稿件的征集與管理;稿件的整理;標(biāo)題作法研究;紙張與油墨的研究;中西活字研究與展望;檢字、植字、電腦排版;圖片與空白;封面與目錄的設(shè)計(jì);版面設(shè)計(jì)的原理與原則;版面設(shè)計(jì)的實(shí)物;校對(duì)、校對(duì)術(shù)、印刷方法;廣告、發(fā)行與專(zhuān)門(mén)化;編者與讀者。毫無(wú)疑義,這是全書(shū)的中心、重心、核心,作者所要闡述的主要內(nèi)容——雜志編輯應(yīng)該如何從宏觀上制定總體的編輯政策和方針,從微觀上如何整理修改稿子、制作標(biāo)題、識(shí)別字體字號(hào)、設(shè)計(jì)封面與目錄、處理版面;如何了解和懂得紙張與油墨的研究、活字研究、檢字植字與電腦排版、印刷方法等有關(guān)出版、印刷知識(shí);如何參與廣告、發(fā)行;如何與讀者進(jìn)行交往、傳播等,幾乎全部集中在這里。像作者結(jié)合自己的雜志編輯工作經(jīng)驗(yàn)對(duì)編輯工作的流程的講解:“一本雜志的編輯政策至少應(yīng)包括下列幾項(xiàng):宗旨、對(duì)象、性質(zhì)、言論立場(chǎng)、內(nèi)容、開(kāi)本、容量與頁(yè)數(shù)、刊期、名稱(chēng)、版權(quán)、封面、廣告。包括這幾項(xiàng)在內(nèi)的編輯政策,是編輯之前設(shè)計(jì)的規(guī)范,是編輯進(jìn)行時(shí)的規(guī)律,是雜志出版后檢討的標(biāo)準(zhǔn)”(55頁(yè))。“編輯將一期或幾期的題材選定,并將內(nèi)容計(jì)劃妥當(dāng)以后,他得去把稿件找來(lái)。這是他跨出設(shè)計(jì)的階段進(jìn)到實(shí)際編輯工作的第一也是最困難的一步”(96頁(yè))……。結(jié)合自己的編輯出版知識(shí)對(duì)排版、校對(duì)等的要求:“我們研究檢字與排版,正像我們研究活字一樣,不是想做一個(gè)排字工人,而是希望充分認(rèn)識(shí)編輯過(guò)程中每一種工具的性能與潛能,現(xiàn)狀與展望,讓我們?cè)谶\(yùn)用時(shí),能充分把握它們,盡量發(fā)揮他們的優(yōu)點(diǎn)。”(227頁(yè))“我們?nèi)粝M岣咭槐倦s志的質(zhì)量,徹底消除版面上可能出現(xiàn)的各種錯(cuò)誤和毛病,一定要重視校對(duì)工作”(355)。特別對(duì)于當(dāng)時(shí)僅在美國(guó)等發(fā)達(dá)國(guó)家得到大面積普及而在華文出版界還處于萌芽階段的“電腦編輯”技術(shù),他強(qiáng)調(diào)說(shuō):“新的工藝要求編輯的是更精確的計(jì)劃,與更充分的訓(xùn)練。”(257頁(yè))如此等等,作者不厭其煩地講,苦口婆心地教,知無(wú)不言,言無(wú)不盡,只要是編輯應(yīng)該知道的知識(shí),編輯應(yīng)該掌握的技能,即使是電腦編輯這樣的新生事物,他也依然鐘情,依然看重。endprint
3 《雜志編輯學(xué)》的特點(diǎn)與意義
3.1 《雜志編輯學(xué)》的特點(diǎn)
運(yùn)用傳播學(xué)理論,闡述雜志編輯的編輯原理和原則。《雜志編輯學(xué)》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它從傳播學(xué)理論出發(fā),探討雜志編輯的原理和原則。比如,它利用傳播學(xué)關(guān)于“受眾”的理論,論述讀者——雜志的讀者是一群“看不見(jiàn)的人”,認(rèn)清讀者是雜志編輯必須遵守的第一個(gè)信條;“今天辦雜志,必須有周詳與深入的讀者和市場(chǎng)研究”(394);“新的傳播學(xué)理論,認(rèn)為大眾雖然大,決非烏合之眾,也不是‘黑壓壓的一群,而是有個(gè)別需要、能作獨(dú)立決定的個(gè)人”(387頁(yè))。它利用傳播學(xué)關(guān)于傳播功能的理論,闡釋“報(bào)紙、廣播、電視、雜志、書(shū)籍都在‘守望、‘報(bào)警、‘交流意見(jiàn)、‘促成行動(dòng)以及‘教導(dǎo)等方面發(fā)揮文化的功能”(24頁(yè))……傳播學(xué)作為“舶來(lái)品”,20世紀(jì)70年代才被正式引入我國(guó),《雜志編輯學(xué)》作為20世紀(jì)60年代的產(chǎn)物,它運(yùn)用傳播學(xué)理論闡述編輯學(xué)原理,不僅開(kāi)編輯傳播學(xué)研究的先河,而且以“媒介交互理論”[3]觀之,它借助于中國(guó)古老的編輯傳統(tǒng),也開(kāi)傳播學(xué)本土化建設(shè)的先端。
重視雜志編輯學(xué)理論與實(shí)踐的結(jié)合。“編輯學(xué)作為一門(mén)在編輯活動(dòng)基礎(chǔ)上建立起來(lái)的新興學(xué)科……加強(qiáng)理論和實(shí)際相結(jié)合,這也是理論工作的一條原則”[4]。《雜志編輯學(xué)》盡管17章中有15章講的是技術(shù),是工藝,是編輯流程、編輯方法,但在具體的、形象的、工藝的、方法的描述中,作者所要闡述的編輯原理、編輯原則看似不經(jīng)意間都得到了表達(dá),一些精彩的編輯理論和觀點(diǎn)融入其間,幾乎每一章、每一部分都有新論。比如,在第1章里,他把包括雜志之內(nèi)的傳播結(jié)構(gòu)看做是“社會(huì)的耳目”、“社會(huì)的喉舌”;第2章里,他精辟地說(shuō):“雜志在許多方面很像建筑物,不只反映著每個(gè)時(shí)代的社會(huì)、政治與經(jīng)濟(jì)狀況,也是時(shí)代動(dòng)向的最好測(cè)量器”(34頁(yè));在第3到到17章里,他認(rèn)為,銷(xiāo)數(shù)是發(fā)行的主要目標(biāo),但雜志“不能無(wú)限度發(fā)行”,靠廣告與零售收入支持的報(bào)刊,都有“最低銷(xiāo)數(shù)”、“最適中銷(xiāo)數(shù)”和“最大銷(xiāo)數(shù)”幾個(gè)概念,一旦發(fā)行量超出最大銷(xiāo)數(shù),就會(huì)出現(xiàn)經(jīng)濟(jì)方面的危險(xiǎn);在工業(yè)高度發(fā)展的國(guó)家,雜志傳播有從一般走向?qū)iT(mén)的趨勢(shì)。特別是關(guān)于雜志編輯的修養(yǎng),他指出,“編輯雜志必須要有高度的道德基礎(chǔ),才能不將這個(gè)社會(huì)公器誤用、濫用,編輯雜志應(yīng)有高度的責(zé)任感,才能讓這現(xiàn)代傳播利器成為造福社會(huì)的工具”(399頁(yè));“認(rèn)真、嚴(yán)肅而負(fù)責(zé)任的雜志編輯人的首要責(zé)任,就是勇敢而公正地刊登消息、意見(jiàn)與知識(shí)。其次,但同樣重要的,是為公眾的利益服務(wù),勇往直前,充當(dāng)社會(huì)的尖兵。第三,永葆獨(dú)立,決不向邪惡妥協(xié),而這正是他能負(fù)起前面兩大責(zé)任的基本條件”(410頁(yè));“偉大的雜志都是它主編身影的伸長(zhǎng)”(51頁(yè))。如此等等,不僅對(duì)編輯、雜志編輯以及編輯學(xué)有一定的理論認(rèn)知,而且對(duì)雜志讀者、廣告、銷(xiāo)售以及走專(zhuān)門(mén)化道路、編輯社會(huì)責(zé)任的思考,有新意,有思想,實(shí)踐闡述中迸發(fā)著理論的火花,理論總結(jié)又出自于編輯的實(shí)踐,二者水乳交融、交相輝映,彰顯了理論與實(shí)踐相結(jié)合的特色。
散文化的語(yǔ)言,講故事的手法,寓教于樂(lè),別具特色。全書(shū)另一大特色是,一個(gè)個(gè)寓意深刻的標(biāo)題、一個(gè)個(gè)生動(dòng)有趣的小故事貫穿全書(shū),像標(biāo)題 “南北美味”講的是“稿件的征集與管理”,“櫥窗陳列術(shù)”講的是“標(biāo)題制作研究”,“白紙黑字”講的是“紙張與油墨的研究”,“美容師”講的是“封面目錄的設(shè)計(jì)”,“伸長(zhǎng)的身影”講的是“編者與讀者”等,既寓意深刻,又形象生動(dòng),既緊扣主題,又通俗易懂。而把“一群看不見(jiàn)的人”比作讀者,把“交響樂(lè)的指揮”喻為編輯,把“清茶代價(jià),王者享受”看作編者,把“第四種人”擬為“校對(duì)”等,可謂新穎、獨(dú)特、生動(dòng)、傳神。特別書(shū)中穿插的“一杯黑咖啡”、“這朵花是黃的”、“縫衣機(jī)不能煮雞蛋”、“昨日黃花”、“一見(jiàn)鐘情”、“秀外慧中”、“百萬(wàn)元的美腿”、“女人世界”、“尋寶圖”、“倫敦的霧”等精彩小故事,不要說(shuō)對(duì)雜志編輯的吸引了,即使是不從事編輯的人,看了這樣的題目,又何嘗不被吸引呢?抓住你的眼球,就抓住了你的錢(qián)袋。難怪《雜志編輯學(xué)》一再重版,影響巨大。
3.2 《雜志編輯學(xué)》的意義
《雜志編輯學(xué)》開(kāi)雜志研究之先河。《雜志編輯學(xué)》是我國(guó)兩岸三地第一本研究雜志編輯的書(shū),它開(kāi)雜志研究之先河。首先,從出版時(shí)間上看,這本《雜志編輯學(xué)》出版于1965年,13年后的1978年臺(tái)灣才有了張覺(jué)明的《現(xiàn)代雜志編輯學(xué)》,26年后的1991年中國(guó)大陸才有了徐柏容的《雜志編輯學(xué)》,至于陳仁風(fēng)的《現(xiàn)代雜志編輯學(xué)》(1995年)等則更晚。其次,從研究?jī)?nèi)容看,《雜志編輯學(xué)》是借對(duì)雜志編輯工作流程、工作內(nèi)容的探討,研究的是雜志編輯的編輯原理、原則和方法。如果說(shuō),當(dāng)初李次民出版《編輯學(xué)》,開(kāi)辟一門(mén)新學(xué)科是“無(wú)心插柳柳成蔭”的話,那么,余也魯?shù)摹峨s志編輯學(xué)》也同樣是“無(wú)心插柳”之舉,開(kāi)辟了編輯學(xué)研究的新領(lǐng)域——編輯學(xué)研究的分支學(xué)科——雜志編輯學(xué)。從它以后,編輯學(xué)研究的家族中才有了“雜志編輯學(xué)”的名分。
作為編輯學(xué)創(chuàng)立以來(lái)第二本研究編輯學(xué)的個(gè)人專(zhuān)著,它推進(jìn)了編輯學(xué)研究的向前發(fā)展。編輯學(xué)雖然起源于中國(guó)本土,具有很深的民族文化淵源,但它作為一門(mén)學(xué)科,誕生的時(shí)代是1949年。從1949到1965年,我國(guó)僅有李次民、余也魯兩本編輯學(xué)書(shū)出版,當(dāng)時(shí)他們兩位也不知道“編輯學(xué)”算不算“學(xué)”,至于學(xué)科能不能“立起來(lái)”,他們自己想都沒(méi)有想過(guò)。但從中長(zhǎng)時(shí)段的歷史觀進(jìn)行回溯,《雜志編輯學(xué)》通過(guò)研究雜志編輯的工作流程、編輯實(shí)踐、編輯技藝,探討的是雜志編輯的編輯原理、原則、方法、理論,不但“成了一本編刊物的人的重要參考書(shū);連教科書(shū)與報(bào)紙的出版人,也用它來(lái)訓(xùn)練新手”(初版自序)。從實(shí)踐的角度來(lái)說(shuō),它一定程度改寫(xiě)了中國(guó)幾千年來(lái)編輯行業(yè)師徒相傳的“傳幫帶”方式,推進(jìn)了編輯學(xué)實(shí)踐的發(fā)展;從編輯學(xué)學(xué)科建設(shè)的角度來(lái)說(shuō),它作為編輯學(xué)創(chuàng)立以來(lái)第二本研究編輯學(xué)的個(gè)人專(zhuān)著,其對(duì)編輯“學(xué)理”的探討,為后來(lái)編輯學(xué)成為一門(mén)學(xué)科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畢竟沒(méi)有一磚一石就不會(huì)有宏偉的大廈,“編輯學(xué)學(xué)科建設(shè)的成熟……必須經(jīng)過(guò)許多人前赴后繼、長(zhǎng)時(shí)間的努力奮斗”[5]。
總之,全書(shū)既有理論論述,又有實(shí)踐分析,既重“學(xué)”,又重“術(shù)”,雖以實(shí)用之“術(shù)”見(jiàn)長(zhǎng),但也不乏理論上的真知灼見(jiàn)。作為教科書(shū),它生動(dòng)、有趣,散文化的語(yǔ)言、鮮活的故事,寓教于樂(lè),誨人不倦。作為學(xué)術(shù)書(shū),它是中文出版物中第一本講雜志編輯的書(shū),其在編輯學(xué)研究歷史上的地位以及開(kāi)拓一門(mén)新學(xué)科的價(jià)值不容低估。
(《雜志編輯學(xué)(第五版)》,余也魯著,海天書(shū)樓1984年出版,487頁(yè),定價(jià)495元。)
注 釋
[1]李志剛.懷念余也魯教授:傳理系之父善用恩賜傳揚(yáng)教理[N].基督教周報(bào),2012-09-23
[2]林觀福,郭鵬飛,周志俊.花香滿徑:著名教會(huì)學(xué)者、傳播學(xué)宗師余也魯教授學(xué)術(shù)貢獻(xiàn)概覽[EB/OL].[2013-01-11].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aaf93301015nb0.html
[3]王振鐸.媒介交互視野中的比較新聞學(xué)研究[J].河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2(5)
[4]姬建敏.編輯學(xué)研究的現(xiàn)實(shí)路徑探尋[J].河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3(3)
[5]靳青萬(wàn).編輯學(xué)應(yīng)是一門(mén)獨(dú)立學(xué)科:論劉杲先生的編輯學(xué)學(xué)科思想[J].河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2(4)
(收稿日期:2014-01-2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