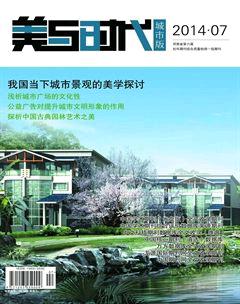道教元素在禮服中的接受與運用
陶源
摘要:
接受美學雖是一種文學理論,但它同樣適用于其他領域。在禮服中也存在著接受問題,并且同文學文本一樣,離開了接受,毫無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關鍵詞:接受美學;道教;道教元素;禮服
一、接受美學產生的歷史背景以及思想淵源
接受美學又稱接受理論或接收研究,產生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的德國南部康斯坦茨大學。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在國際政治風云的變化的背景下,日益引起人們關注的文學社會功能和社會效果問題已經無法由遵循本文的“獨立性”的主張和形式主義理論作出解答。同時,由于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人際間交流研究逐步展開,許多重要的美學家和美學流派開始關注和重視藝術和審美活動中讀者的地位和作用問題,文學理論的思維重點就自然而然地轉移到對文學的接受與影響問題的研究上。
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姚斯和伊瑟爾為代表的聯邦德國的康斯坦茨學派迅速崛起,確立了以讀者為中心的美學理論,實現了文學研究方向的根本轉變。在姚斯等人看來,接受美學正是在反對純本文注意和純結構語言運動的精神指導下形成的,并根據新的歷史主義要求,站出來與唯本文主義爭辯。
接收美學的理論基礎主要是現象學美學和解釋學美學。除此以外,它還吸收了布拉格結構主義理論家穆卡洛夫斯基的“空白論”思想,并且從保爾·利科爾的解釋學理論、哈貝馬斯的交往理論、薩特的《何謂文學》中的恢復讀者地位的理論和馬克思的“循環模式”理論中汲取營養,從而使接受美學成為文學理論研究中的全新方法論體系。
二、道教的歷史起源以及道教元素的宗教寓意
道教歷史悠久,淵源廣泛,它不僅源于古代宗教和民間巫術,并且也源于戰國至秦漢的神仙傳說和方士方術。道教的歷史淵源上溯很早,有據可考的醞釀時期是在西漢,正式誕生則是在東漢。《天皇至道太清玉冊》說:“古者衣冠,皆黃帝之時衣冠也。自后趙武靈王改為胡服,而中國稍有變者,至隋場帝東巡便為畋獵,盡為胡服。獨道士之衣冠尚存,故曰有黃冠之稱”。道教之所以被稱為“黃冠”源于其黃色的戒衣。道教的戒衣是黃色,大襟,長及腿腕,袖寬二尺四寸以上,袖長隨身。在堯舜時期,中國服飾有“玄衣黃裳”之說。《易·坤卦》曾有這樣記載“六五,黃裳,元吉。”
根據道教服飾的用途,分為法服和常服。道教的之法服,按照其描繪的神仙境界而繡上不同于世俗的尊貴圖案。如我們通常所見的高功服,背面一般繡有郁羅簫臺、金烏玉兔、仙鶴、祥云、蟠龍等,這些圖案代表著三界最尊貴的神明,故高功披上法衣,得神鬼欽服,眾靈拱衛,而能通達于天庭。在道教盛行之時,所有的道教法服和仙服都有精美的刺繡工藝。裝飾的圖案,都是傳統的吉祥紋樣,尤其是八卦和萬字文在道教服裝上應用極為廣泛。
同時,作為道教思想核心的五行同樣也可以用色彩來表達和傳遞。縱觀我國傳統服飾圖案演變史,應用五行色彩最早可以追溯至新時期時代晚期,《尚書·黃櫻》中這樣寫道:“以五彩章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說明這一時期先民們就在五行思想的支配下用染過色的織物制作衣服。具體來說,五行色彩體系即我們目前所采用的色立體中的“青、紅、皂、白、黃”,其中青代表木、紅代表火、皂代表水、白代表金、黃代表土,這五種顏色被稱為正色。
三、從接受美學看道教元素在現代禮服中的運用
接收美學和接收理論的興起,不僅強烈沖擊了傳統文學文本研究,同時被迅速的應用到音樂、建筑、影視等領域中。禮服作為重大場合的正式服裝對接收理論的吸收與應用也成為必然的發展趨勢。現代社會,由于人們的生活經歷、興趣愛好、社會地位、審美習慣等都表現出很大的差異性,人們對于時尚和美的欣賞也日益多元化。禮服的設計和元素的運用,面對龐大的受眾群體,不能以設計者自身為中心,必須轉向受眾為主體。
在第63屆戛納電影節上,身著明黃色龍袍禮服的范冰冰借一襲龍袍裝在紅毯驚艷了世界。她的禮服上繡有兩條高高躍起的飛龍,拖地的水腳上繡出許多翻滾的波浪仿似滿耳波濤洶涌聲有“萬世升平”之意。在龍紋之間,繡以五彩云紋的吉祥圖案寓意祥瑞之兆。龍紋是五千年華夏文明里形成的中華審美模式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產生于陰陽五行和中庸之道,龍紋的形成正是積淀了華夏文化的道教觀念。禮服中以大面積明黃色為底色,圖形中包含了祥云、波浪、雙龍,色彩上運用了道教的五行色彩”青、紅、皂、白、黃”,工藝上使用了刺繡,完美的將道教的文化融入其中。在第64屆戛納國際電影節,范冰冰再次以一身紅色的仙鶴禮服艷壓全場。仙鶴禮服中,有九只形態各異的鶴舞繚繞中,間綴梅蘭竹菊四君子繡紋。在中國道教文化中,“九”為最高數,又與“久”諧音,仙鶴象征長壽及富運長久,仙鶴在道教中代表著三界最尊貴的神明之一。在道教中,仙鶴刺繡應用廣泛,在道服、仙服和桌圍等等服飾用品中,我們都可以看到精美的仙鶴繡品工藝。
當然,道教元素在禮服中的運用也不是一帆風順的。范冰冰身著“龍袍”禮服后,引起了很大的爭議。首先,在中國,龍代表男性,鳳凰才代表的女性。其次,龍袍代表權力,也讓大家質疑范冰冰“把野心穿在了身上”。同樣,第64屆法國戛納電影節上展示的仙鶴裝也未能幸免。有所謂的專家學者跳出來,指認“仙鶴”被法國人視為惡鳥,這個詞在法語中更是愚蠢和淫蕩的象征。然而事實上,法國人也都喜歡仙鶴,甚至認為如果在夢中見到仙鶴,就預示著會見到親切的人,并將有幸福的事發生。雖然這兩套禮服的呈現略有爭議,但是所帶來的中國熱是我們不容小覷的。只是在接受美學的角度來看,受眾的文化差異有時候也是值得我們考慮的。
隨著近幾十年中國國際地位的上升,中國文化的影響力也逐漸增大,越來越多的人熱愛和渴望了解中國的文化。道教元素在禮服中的展現正是完成了“從作品中心到讀者中心”的邏輯轉變,把禮服的接受者提到了相當重要的地位,即受眾在審美過程中的能動作用,這樣才使得禮服本身的意義和藝術效果能夠具體的體現出來。
【參考文獻】
[1]姚斯.審美經驗與文學解釋學“序言”[M].麥納蘇泰大學出版社,1982
[2]胡經之、王岳川.文藝美學方法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3]田誠陽.道教的服飾[J].中國道教,1994(03)
[4]黃壽祺、張善文.周易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5]馬以鑫.接受美學新論[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5
[6]李薇.中國傳統服飾圖鑒—中國傳統文化圖鑒系列[M].北京:東方出版社,2010
【作者單位:武漢紡織大學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