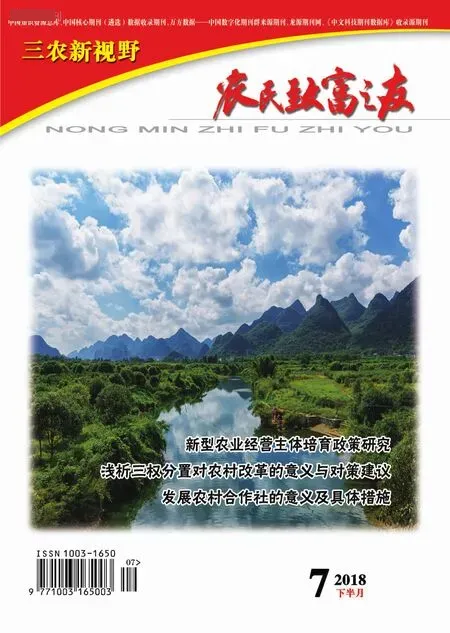靖邊縣發(fā)展節(jié)水農(nóng)業(yè)帶動馬鈴薯產(chǎn)業(yè)發(fā)展
李寧+李琴+陳艷。
引言
靖邊縣如今發(fā)展節(jié)水農(nóng)業(yè),大力發(fā)揮馬鈴薯種植,帶動本地農(nóng)民增加收益。本文陳述了馬鈴薯生產(chǎn)的現(xiàn)狀,解析靖邊縣馬鈴薯種植的優(yōu)點(diǎn),提出產(chǎn)業(yè)發(fā)展存有的緊要弊端,確立日后馬鈴薯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思路,并從品種選擇、技術(shù)推廣、加工企業(yè)、市場營銷、政府扶持等方面提出對應(yīng)發(fā)展方針,對于今后靖邊縣的馬鈴薯產(chǎn)業(yè)持續(xù)穩(wěn)定發(fā)展,有深遠(yuǎn)意義。
靖邊縣地處陜西省西北地區(qū),地處毛烏素沙漠與黃土高原過渡地帶,土層深厚、土質(zhì)疏松、氣候冷涼、雨熱同季、晝夜溫差大、日照時數(shù)長,十分適合種植馬鈴薯。馬鈴薯具備較高的營養(yǎng)與藥用價值,不但可以作為糧食,也可以用來做菜。同時也是很好的磁療,與我們?nèi)粘I罹o密相關(guān)。大力推廣馬鈴薯種植,既可以發(fā)展節(jié)水農(nóng)業(yè),也有益于本地農(nóng)民的收益增多。
1發(fā)展優(yōu)勢
靖邊縣擁有全面推廣馬鈴薯種植的三大優(yōu)勢前提。一是生態(tài)境況適宜。靖邊縣擁有寬闊的田畝,土壤肥沃,含有豐富的鉀元素,陽光充足,雨季相同,晝夜溫差大,境況未受污染,屬于國家新一輪指定的西北馬鈴薯優(yōu)勢地區(qū)其一。二是推廣空間大。靖邊縣礦產(chǎn)資源富裕,特別是石油和天然氣,縣區(qū)經(jīng)濟(jì)發(fā)展迅速,兩千零八年步入全國百強(qiáng)縣之列,擁有財政扶持農(nóng)業(yè)的上風(fēng)條件,而農(nóng)民比其他關(guān)鍵糧食作物對于種植土豆的熱情更高。三是技術(shù)水準(zhǔn)提升。在兩千零七年和兩千零八年間,靖邊縣馬鈴薯創(chuàng)造國家和省級三大記錄。四是商品的品質(zhì)好。馬鈴薯商品淀粉和干物質(zhì)含量高且蒸汽,表面平滑,品行優(yōu)良,病蟲害少,物產(chǎn)高,降解綏慢,產(chǎn)品銷往全國各地。
2存留的弊端
靖邊縣的馬鈴薯發(fā)展根基是很好的,可是如今存有多處弊端。一是品種技術(shù)推新過慢。目前主要注重的馬鈴薯品種是食用型鮮薯,這種專業(yè)化程度不高,對于品種的防止病蟲害措施、種植的方法、土壤的肥料配置等推新過慢。二是馬鈴薯的供種系統(tǒng)不完善。在目前的種植系統(tǒng)中沒有構(gòu)成完整的從基本種到優(yōu)良種的供種系統(tǒng),確保馬鈴薯的品質(zhì)。三是加工廠的力量不足,發(fā)展方針不正確。馬鈴薯副產(chǎn)品的加工產(chǎn)業(yè)鏈,定位低,產(chǎn)品線單一,導(dǎo)致經(jīng)濟(jì)收益也不高。四是銷售系統(tǒng)不完善。農(nóng)民大多自產(chǎn)自銷,與合作社的組織交流不夠,信息不暢通,運(yùn)輸儲藏的方式并沒有與時俱進(jìn),及時更新,不利于當(dāng)今產(chǎn)銷一體化的發(fā)展趨勢。
3產(chǎn)品發(fā)展思路
要分析了解縣區(qū)的地理與資源優(yōu)勢,以新時代科學(xué)的方式,立足市場需求,為本地農(nóng)民創(chuàng)收。調(diào)節(jié)布局、完善結(jié)構(gòu)、將品種品牌化,進(jìn)行區(qū)域化種植、結(jié)合新技術(shù)科學(xué)栽種、與銷售商聯(lián)合產(chǎn)品銷售,達(dá)到產(chǎn)銷結(jié)合、合理分布、形成銷售產(chǎn)業(yè)鏈,擴(kuò)大產(chǎn)品銷售范圍;將馬鈴薯副產(chǎn)品加工多樣化,讓靖邊縣的馬鈴薯產(chǎn)業(yè)做的更好更優(yōu)。截至二零一五年,馬鈴薯產(chǎn)品的整體目標(biāo),栽種面積達(dá)到四萬公頃,產(chǎn)量達(dá)到每公頃二十二點(diǎn)五噸,總產(chǎn)值達(dá)到七億元,收益增加四億元。加工產(chǎn)品轉(zhuǎn)換宗旨:對于目前縣城的加工企業(yè)做技術(shù)改良,以至產(chǎn)量增加。利用招商引資吸引多樣化馬鈴薯副產(chǎn)品加工企業(yè),讓產(chǎn)品的品種變的豐富,同時也能夠增加企業(yè)收益。對于馬鈴薯的實際銷售,可以建立專項集中銷售市場,設(shè)立專場采購會,吸引各地的銷售商。同時,可以利用網(wǎng)絡(luò)銷售平臺,線上線下結(jié)合,能夠推動全縣的馬鈴薯銷售到更遠(yuǎn)的地方。
4發(fā)展方針
4.1立足市場,擴(kuò)展多樣化馬鈴薯品種
目前靖邊縣的品種推新不夠及時,銷售方式過于單一。想要改善現(xiàn)狀,首先需要立足市場需求,解析目前市場的需求方向。現(xiàn)在的市場對于食品加工與淀粉加工的種類不多,所以可以從這方面入手,經(jīng)過引進(jìn)新的品種,著重對該品種的栽培,適合淀粉加工、油炸加工的優(yōu)質(zhì)品種,達(dá)到市場的需求。
4.2完善種薯的繁供系統(tǒng),加強(qiáng)種薯監(jiān)督力量
一是完善縣、鄉(xiāng)、村基本種、優(yōu)良種的繁供系統(tǒng);二是嚴(yán)格依照國家的馬鈴薯檢測標(biāo)準(zhǔn);三是強(qiáng)化品種管理部門的監(jiān)督力量,嚴(yán)格認(rèn)真的實行對脫毒種薯品質(zhì)檢測;四是根據(jù)品質(zhì),實行品牌化,創(chuàng)建線上線下一體、專項銷售市場等多種銷售系統(tǒng),推動馬鈴薯產(chǎn)業(yè)的全面持續(xù)發(fā)展。
4.3推動標(biāo)準(zhǔn)化生產(chǎn)技術(shù),提升產(chǎn)品品質(zhì)
標(biāo)準(zhǔn)化是產(chǎn)業(yè)化的前提。靖邊縣的馬鈴薯品種多,可是產(chǎn)品的品質(zhì)卻不能得到保證,產(chǎn)品成色不好,加工產(chǎn)品線單一,種植的技術(shù)不更新,當(dāng)務(wù)之急是需要實行標(biāo)準(zhǔn)化生產(chǎn)。所以應(yīng)當(dāng)利用當(dāng)代最新的科技技術(shù),全面改良經(jīng)典的小戶自產(chǎn)模式,需要推動同一品種、同一技術(shù)、同一產(chǎn)品標(biāo)準(zhǔn)的規(guī)范化生產(chǎn)技術(shù),在產(chǎn)量與品質(zhì)上達(dá)到市場的需求。
4.4強(qiáng)化銷售系統(tǒng),創(chuàng)立良好銷售市場
市場需求決定馬鈴薯產(chǎn)品的開展是否成功。靖邊縣應(yīng)當(dāng)招商引資創(chuàng)建馬鈴薯的專項銷售市場,零售與批發(fā)相結(jié)合。也可以設(shè)立馬鈴薯產(chǎn)品的專場采購會,吸引全國乃至國外的供應(yīng)商來采購。如今網(wǎng)絡(luò)銷售平臺的力量不容小覷,能夠利用線上線下相結(jié)合,形成系列產(chǎn)品銷售鏈,政府積極大力支持馬鈴薯產(chǎn)品的發(fā)展,在一定范圍內(nèi)給予適當(dāng)?shù)膬?yōu)惠政策,招商引資,推動本縣的種薯、商品薯、馬鈴薯的加工副產(chǎn)品銷往全球各地。申請綠色食品基地、有機(jī)食品基地,樹立當(dāng)?shù)貎?yōu)良品種的品牌,利用網(wǎng)絡(luò)信息平臺,實時給予種植農(nóng)戶有益的輔導(dǎo)。
5發(fā)展前景
馬鈴薯的生產(chǎn)技術(shù)并不復(fù)雜,同時收益還是不錯,對于品種再加工之后,經(jīng)濟(jì)收益能夠變得更多,是可以帶動靖邊縣農(nóng)民脫貧致富的關(guān)鍵作物,推動馬鈴薯產(chǎn)業(yè),收益可觀,市場的發(fā)展前景好。有數(shù)據(jù)表明,馬鈴薯的經(jīng)濟(jì)收益可觀,把它加工成一般淀粉,能夠價值翻倍,生產(chǎn)吸水樹脂能夠增值八倍,生產(chǎn)生物膠能夠增值六十倍以上。在食品加工也中,用馬鈴薯作原料,能夠加工成多種速食食品,如速凍薯條、油炸薯片等。
6結(jié)束語
馬鈴薯的營養(yǎng)豐富,經(jīng)濟(jì)收益也很好,擴(kuò)展加工品種,也能夠使收益倍增。本身靖邊縣對于發(fā)展馬鈴薯生產(chǎn)的地理條件就很適宜,產(chǎn)品的前景很明朗。所以全面推動本縣的馬鈴薯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改善馬鈴薯產(chǎn)業(yè)的構(gòu)造,多樣化持續(xù)發(fā)展,能夠帶動農(nóng)民增收,改善生活品質(zhì),達(dá)到農(nóng)民脫貧致富的宗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