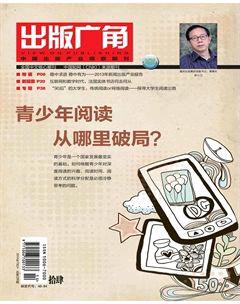《五朝皇帝與圓明園》記
孫元元
以人為鑒,可以知得失;以史為鑒,可以見興替。清朝一百五十余年之歷史人文,圓明園為一大見證者。
甲午年仲春,《五朝皇帝與圓明園》一書幾經(jīng)刪改,終于清明付梓。不日,樣書即至。予觀之清麗工整,厚重雅致,甚合本意。遂告知于作者劉陽兄,兄大喜,急赴鄙社觀之。談笑間亦推敲近之小稿,論中國、西方之建筑,博古通今,侃侃而談。用時不多,但予收獲頗豐,不亦樂乎!
猶記2013年元月,予尚待產(chǎn)。查閱史料之余,得知劉陽兄乃通曉清史、建筑史之達人。遂聯(lián)絡之,兄亦有意撰文。六月,乃付稿。予讀之感慨頗多,常與夫君提及劉兄此人此事,曰:“我等當效劉君之孜孜以求,志存高遠。倘時時研習,術業(yè)專攻之事皆爛熟于心,自當?shù)闷涿!狈蚓囝h首。
國人論及圓明園,多限于清咸豐十年,圓明園為外虜一炬,嗚呼哀哉云云。予嘗記兒時之觀《火燒圓明園》《兩宮皇太后》之所謂巨制,似舉慈禧太后為清國腐敗之源、紅顏禍水之意。中學歷史教材,亦云慈禧“量中華之物力,結(jié)與國之歡心”之語。圓明園所謂何物,所知寥寥。
讀此書,乃知“圓明園”之得名,取自《中庸》“圓而入神,君子之時中也,明而普照,達人之睿智也”一句,康熙帝之厚望可見一斑。“圓”即希后世帝王個人品德圓滿無缺;“明”乃國家政治明光普照之意旨。此外,“圓明”亦雍正帝之佛號。蓋各朝創(chuàng)立之初,君王多勤勉,冀本朝千秋萬載永續(xù)不止。嘆身后后世之事,豈本人可主宰乎?徒添憤懣耳。
今日之圓明園,植被居多,娛人游樂居多,年代較久者,僅限目睹火燒圓明園之若干大石,殘垣猶有燃跡,如訴如泣。南北之游客多走馬觀花,殊不知真實之圓明園“檻花堤樹,不灌溉而滋榮;巢鳥池魚,樂飛潛而自集”;“萬象畢呈,心神怡曠” 。亭臺樓榭,奇珍異寶,不可逐一而舉,“萬園之園”之名絕非夸夸其談。其間諸多史實,亦令人回味。三朝皇帝共賞牡丹,“樣式雷”家族之營造功勛,《四庫全書》與“五福五代堂”,六世班禪園內(nèi)游歷,趣聞頗多。予深感于心者有二:一為道光帝與孝和皇太后之情誼,善始善終,予信諸君讀及此處,將無不為之動容;一為圓明園遭蹂躪之經(jīng)過,每讀至此,淚目迷離,已“出離憤怒”矣!
圓明園自興建至焚毀,歷經(jīng)一百五十余年,其間五位清帝耗盡財力私心,傾畢生之力營建,始有此園。類清帝皆鐘愛一園者,前朝未有此事。圓明園之地位誠不亞于故宮、清漪園。圓明園罹難之前,實乃中華國之瑰寶,國人之榮耀。唯嘆其結(jié)構(gòu)之精巧,意境之源遠,難敵西洋炮火之無情,英法侵略者之無恥殘忍。此事乃中國近代史之大恥!
予之拙見,圓明園之殤始自清國妄自尊大。康熙帝一朝稱“盛世”,然此時,英國正值產(chǎn)業(yè)革命浪潮,社會進步突飛猛進,誠乃“新時代”之來臨,非清國可比擬。此后之百年,西方諸國多革命變法,沖破經(jīng)濟發(fā)展之束縛,富國強兵,侵略擴張。清各君王仍藐視外國使節(jié)之通商要求,持續(xù)閉關鎖國,乾隆帝如是,嘉慶帝亦如是。無奈歷史之前進步伐非人為可阻擋,道光二十年,英國終以炮火開啟中國之門,中國近代之恥自鴉片戰(zhàn)爭始。若清帝小心翼翼,時刻自省,試圖了解他國之現(xiàn)狀,縱只為保皇位永續(xù),結(jié)局未必至此。今日中國仍難躋身于強國之列,吾輩更需謙虛謹慎,勿蹈前朝覆轍。
四大古文明約形成于六千年前,然今只剩中華文明者存,實屬萬古難得之事!今之中華少年,妄自尊大者多,日益西化者多,渾渾噩噩、無思考之心者亦眾矣。華夏子孫,當胸懷天下,渡己渡人,知自身文明之燦爛,思為先祖續(xù)傳國學。中國地廣人雜,政治之變法變革,非一日可成之事;文明之延續(xù)繼承,當自我等始!唯本國人心可救國救民,不可寄此厚望與他人,甚至他國。
以人為鑒,可以知得失;以史為鑒,可以見興替。清朝一百五十余年之歷史人文,圓明園為一大見證者。觀中國之歷史,皆系前人無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縱如此,歷朝歷代皆有助歷史前進、福澤民生之士。予等自幼苦讀,得父母恩,得師長恩,曾不如貧弱中國之國民哉?
是為記。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