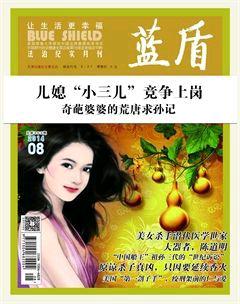“中國船王”祖孫三代的“世紀訴訟”
1988年12月30日,原告陳震、陳春等為與被告日本海運株式會社(現為商船三井株式會社)定期租船合同欠款及侵權賠償糾紛一案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訴訟,追索“順豐”輪、“新太平”輪船舶租金及經濟損失。
2003年11月25日,該案在上海海事法院開始了它的第五次庭審。這場中國第一代船王祖孫三代的世紀訴訟,是對日民間索賠時間最長、金額最大的官司。
商船三井株式會社全面履行判決
上海海事法院解除日方船舶扣押
新華社上海4月24日電 2014年4月1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海事法院為執行生效民事判決,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的相關規定,對停泊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浙江省舟山市嵊泗馬跡山港的被執行人商船三井株式會社所有的“BAOSTEEL EMOTION”輪實施了扣押,并向被執行人送達了《執行裁定書》和《限期履行通知書》。
被執行人商船三井株式會社于2014年4月23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海事法院《限期履行通知書》的要求,全面履行了生效民事判決確定的全部義務,包括船舶租金及孳息、船舶營運損失及孳息、船舶損失及孳息,共計2916477260.80日元;支付了一、二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2122575.41元、申請執行費人民幣298356元,共計人民幣2420931.41元;同時就支付延遲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及其他費用提供了充分可靠并可供執行的擔保。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海事法院經審查,認為商船三井株式會社已全面履行了法院生效判決確定的義務,故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于2014年4月24日上午8時30分下達裁定,解除對“BAOSTEEL EMOTION”輪的扣押,同時發布《解除扣押船舶命令》。
船王第一代:
北伐戰爭立下汗馬功勞
1895年出生于浙江寧波的陳順通,14歲闖蕩上海灘,由見習水手成長為一名技藝嫻熟的船長。因拯救被軍閥追捕的國民黨元老張靜江,陳被張舉薦為國民航運公司經理,為北伐軍暗中運送軍火立下汗馬功勞。
北伐勝利后,陳順通在上海均泰錢莊優惠信貸支持下買入“太平”號貨輪。1930年9月1日,陳順通的中威輪船公司成立。此為中國第一家獨資海運公司。4年內,陳又先后從英、澳購進“新太平”“順豐”“源長”三輪,其中的“順豐”號時為中國最大的貨輪。中威公司船只總噸位2萬噸,陳為中國第一船王。后來的香港船王、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華的父親董浩云,當時曾是陳的助手。
1936年10月14日,應日本大同海運株式會社要求,陳順通代表中威與“大同”在上海簽訂定期租船合同,將6725噸的“順豐”與5025噸的“新太平”租給“大同”使用。合同規定,從船舶交付之日起,租期為12個月。合同11月1日生效。為預防風險,中威公司分別將兩輪向日本“興亞”、“三菱”兩家海上保險株式會社投了船體保險。
1937年“8·13”事變后,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為響應國民政府堵塞航道防御日本大舉進攻的要求,陳順通將中威公司剩余的兩輪“太平”號和“源長”號分別自沉于江陰口與寧波灣航道。
而日本“大同”租船期滿,“順豐”與“新太平”兩輪卻下落不明,中威公司海運業務全面停止。1939年春,陳順通赴日找到大同海運株式會社。對方告以兩輪均被日本軍方“依法捕獲”,而且大同海運株式會社也瀕臨倒閉。
陳順通東京之行一無所獲,而他在上海為維修船只的中威機器廠亦被日本占據。一代船王回到上海大病一場。
1940年4月9日,日本大同海運株式會社正式發函給陳順通,介紹兩輪無法返還的緣由:兩輪被日本政府于1938年8月22日“依法捕獲”,所有權被宣布歸日本國遞信省(交通部),又通過定期租船合同將兩輪轉租給“大同”,現由“大同”使用兩輪并向日本遞信省支付船租。
但陳順通不知道,事實上在這封信之前的1938年12月21日,“新太平”號就已在“大同”的營運中在北海道觸礁沉沒。他更不知道,若干年后的調查表明,大同海運株式會社亦早將此船的保險金領取。
抗戰勝利后的1947年,陳順通憑此信請求國民政府赴日代表團索取被“捕獲”的兩輪,并向駐日美軍司令麥克阿瑟發信求援。這時他才得知戰爭中兩輪均已沉沒(“順豐”號1944年12月25日在南海觸雷沉沒)。
陳順通一病不起,于1949年11月14日病逝。但日本在1947年5月3日頒布的新憲法中有國家承擔戰爭賠償的規定,給陳順通留下了索賠的希望,他立下遺囑,要求兒子陳恰群全權處理兩輪的索賠事宜。
船王第二代:
日本訴訟十年勞而無功
1958年,陳恰群自上海遷居香港。陳抵港第一件事就是與日本“大同”聯系。他注冊的中威輪船就是為了繼承父親的事業,打贏官司。而“大同”每次都以人事變動和船只為日本政府奪去、應由日本政府負責等作答。
心有不甘的陳恰群1961年奔赴日本,開始了漫長的索賠之旅。他根據大同海運株式會社1940年的信向日本政府索賠,不斷在日本外務省、大藏省、遞信省之間奔波。日本政府經1961-1964年的漫長調查后做出答復:兩輪被日本政府“依法捕獲”一事查無實據,不予認可。
陳恰群聘請曾代理韓國向日索賠獲勝的日本著名律師緒方浩做律師,緒方浩建議與日本政府打官司,陳遂委托緒方浩起訴日本政府。
1964-1967年,日本東京簡易裁判所受理中威公司與日本政府的民事調停。26次調停的最終結果是,日本政府答辯:此兩輪是否為日本“捕獲”情況不明,拒絕做出賠償。
1970年4月25日,陳在東京地方法院正式起訴日本政府,“陳恰群訴日本國”成為1970年代日本轟動一時的報道。不過,此案開庭所需的巨額費用讓當年的船王之子陷入窘境,幸得有“日本良心”之稱的緒方浩的資助使得訴訟能夠進行。
這是一場耗費時間和精力的拉鋸戰。僅因陳恰群在回答“中國人是個籠統概念,到底是哪里?大陸、臺灣還是香港的中國人”時,答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合法居住香港”,法庭為確認這一身份就耗時5個月。此事還得到周恩來總理親自關照,迅速出具了身份證明。
經過數十次庭審,1974年10月25日,陳恰群最終卻得到了一個意外的判決:“時效消滅”。這個結果又讓陳恰群大病一場。
10年日本訴訟被畫上句號:律師要求在東京高等法院繼續上訴,已拿不出錢繼續上訴的陳恰群被視為撤訴。
船王第三代:
歷經波折打贏官司
陳恰群日本索賠失敗后徹底絕望了。但1987年1月1日頒布施行的《民法通則》為陳氏帶來了柳暗花明的轉機,因《民法通則》的時效性,最高法院規定“凡是在《民法通則》頒布前民事權利受侵害未被處理的案件,在《民法通則》頒布后的兩年內提起訴訟都有效”。此舉意味著,中威船案可在中國本土受理。
但陳恰群已于1985年8月中風半身不遂,將中威船只索賠案的接力棒交到了第三代人陳震、陳春兄弟手上,陳氏兄弟通過北京中國法律中心為訴訟代理,于1988年12月31日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訴訟。
這次在中國本土打官司,陳氏家族組織的律師團人數創造了中國民事案的紀錄。囊括了大陸、香港、美國、臺灣法學界名流的律師團和顧問團成員,總數多達56人。
而該案此時的被告則由日本政府變成了日本企業并且被告對象一變再變。當年的大同海運株式會社在20世紀60年代并入日本海運,日本海運又在80年代并入日本NAVIXLINE(日本奈維克斯海運株式會社),1999年4月它又被并入日本第二大海運公司商船三井船舶株式會社。
律師團仔細研究后還發現,大同海運株式會社當年對“船王”陳順通稱兩輪被日本政府“捕獲”無任何證據,是欺詐行為,應負全部賠償責任。
此案于1991年8月15日第一次開庭審理,到2003年11月26日,一共5次開庭。但陳恰群沒看到最終的結果,于1992年4月去世。庭審時,原告律師團名單上15的成員被畫上了黑框,而被告方律師亦是前赴后繼。陳春說:“官司打了我們祖孫三代人。當年56人的律師和顧問團里,今天已有15不在人世,想起來真是一場悲壯的索賠。”
關于巨額賠償金,陳春解釋說:“我們提出這么多的(賠償)數字不是沒有理由的。我們請了專門做海運海事的上海大樣行資產評估,我們在1995年的第四庭上派代表到法庭,出具了被告應對原告的賠償費用,測算到1995年11月30日,應賠償312.7億日元,根據當天外匯市場的牌價,折算合3.12億美元。現在又經過了8年,如果算上這段時間,我想賠償額度該有5億多美元。”
中威最后的出庭律師葉鳴補充說:“這個賠償金額中并未包含因被告的欺詐(稱兩輪被日本政府“依法捕獲”),造成陳氏兩代人與日本政府交涉帶來的巨大的心力和精神損失。”
在1996年5月20-28日的第四次庭審時,被告當庭承認對中威的損失負有道義的責任,愿意做出補貼。盡管雙方在賠償金額的主張上存在很大差距,但被告的和解意圖意味著該案前景開始明朗起來。
但就在此時,陳氏家族內部突然出現了危機——陳震、陳春的叔父陳乾康訴船王陳順通給陳恰群的遺囑為偽造。上海一中院在受理糾紛后,于1996年9月16日做出判決:50多年前船王陳順通的遺囑無效。
該判決從根本上動搖了上海海事法院正在審理的世紀訴訟。陳春說:“(這一判決)震驚了顧問團,全體上訴上海高院,并向最高院反映上海一中院枉法判決。”
上海高院受理了這一糾紛。1998年6月10日高院重新開庭審理,最后做出撤銷一中院判決的裁定。這個轟動性的意外插曲使索賠案被延遲了整整兩年。陳春說:“這是被告挑起中威家屬內部矛盾。”“本來1996年、1997年就該判定,因對方不擇手段干擾這個案子,所以拖到了現在。”
該案的最終結果沒有讓陳氏家族失望,“中國船王”陳順通、陳恰群父子可以瞑目了! 據人民網
(摘自《蘭州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