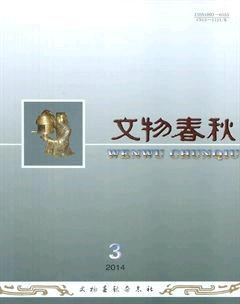北京地區遼代火葬墓及相關問題試析
李偉敏
【關鍵詞】北京地區;遼代;火葬墓
【摘 要】從20世紀50年代至今,北京地區陸續發現了40余座遼代火葬墓,其形制可分為土壙磚室墓和磚石混筑墓兩類,以圓形為主,墓主人多為漢人。北京地區遼代火葬流行主要受佛教影響,同時亦與契丹人的火葬風俗有關。
20世紀50年代以來,北京地區陸續清理發掘了一批遼代火葬墓,為研究遼代該地區的火葬習俗提供了較為豐富的考古實物資料。本文擬對此作一梳理并做粗淺探討。
一、發現與發掘
北京地區遼代火葬墓的發掘始于20世紀50年代,截止目前已發掘40余座。其工作大致可分兩個階段:20世紀中后期發現的數量較少,且分布零散;21世紀后,為配合基建發掘的數量較多,且分布集中。
1.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調查研究組在永定門彭莊發掘遼墓7座,其中1號墓為火葬墓[1]。
2.1957年10月28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調查研究組在北京西郊月壇北的洪茂溝清理遼代火葬墓1座。該墓為圓形磚室墓,出土“濟陰董府君夫人王氏墓志銘”一方[2]。
3.1958年4月,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在西郊百萬莊發現遼代磚室墓2座,均為火葬墓,其中M1,為圓形雙室墓,前室出土“丁公墓志”一方,后室出土“丁洪墓志并序”一方;M2為單室,平面呈八角形[3]。
4.1960年8至10月,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調查研究組在永定門外海慧寺西1公里處發掘磚室墓1座。該墓為三進九室,平面均為圓形,葬二人,其中一人為火葬。發掘者據所發現的墓志,認為該墓為遼代趙德鈞和妻種氏合葬墓[4]。
5.1971年11月,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在西城區大玉胡同發掘1座遼代火葬墓[5]。
6.1973年初,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在宣武區先農壇南部工地發現遼墓1座,墓室內發現盛骨灰的陶罐[6]。
7.1979年10月,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在大興區京開公路西紅門段東側液壓機械廠清理遼墓1座,該墓為圓形磚室火葬墓,出土“清河郡夫人張氏墓志”一方[7]。
8.1981年6月,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在八寶山殯葬管理所院內發掘1座遼代火葬墓,出土韓佚墓志和其妻王氏墓志各一方[8]。
9.1986年8月,昌平縣文物管理所在南口鎮陳莊村發掘遼墓2座,其中1號墓為火葬墓。發掘者判斷該墓主為契丹平民,墓葬年代為遼末金初[9]。
10.1987年11月4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門頭溝區新橋大街39號院發現1座遼代火葬墓[10]。
11.2002年3月31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海淀區增光路中國工運學院住宿樓北部發現1座遼代火葬墓,出土 “康公墓志”一方[11]。
12.2003年10月至2005年8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北京亦莊經濟技術開發區69號地發掘遼代墓葬25座,其中M16為火葬墓[12]。
13.2004年4月至5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五棵松籃球館發掘墓葬48座,其中M26為遼代火葬墓[13]。
14.2005年5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門頭溝區龍泉鎮龍泉務村西北發掘遼金墓葬22座, 其中19座為遼中晚期至金初的火葬墓[14]。
15.2007年1月至3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密云縣城關鎮大唐莊村東南發掘漢代至明清時期各類墓葬122座,其中M14、M15為火葬墓。發掘者認為M14、M15的年代為遼代晚期[15]。
16.2008年5月至6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大興區黃村鎮北程莊清理遼代墓葬12座,均為火葬墓。發掘者認為墓葬年代為遼代中晚期[16]。
二、墓葬形制
北京地區發現的遼代火葬墓根據構筑材質的不同,可分為土壙磚室墓和磚石混筑墓兩類,其中土壙磚室墓數量較多。
(一)土壙磚室墓
據墓室數量可分為單室、雙室和多室,其中單室墓數量最多。所用磚有勾紋磚、繩紋磚和素面磚。
1.單室墓
據墓室平面形狀可分圓形、長方形和八角形,其中圓形數量最多,長方形和八角形發現較少。
圓形單室墓由墓道、墓門、墓室組成。墓道多呈階梯狀。墓門多為拱券頂,用勾紋磚封堵。墓門一般用雕磚做出仿木結構,繁復者有檐椽、瓦壟、門脊及斗拱等,簡單者僅有立頰、門額、門簪、
長方形單室墓僅發現2座,即海淀區五棵松籃球館工程M26和亦莊開發區69號地遼墓M16。此類墓葬平面呈長方形,其中亦莊開發區M16墓室內有長方形祭臺,骨灰置于長方形木匣中。
八角形單室磚墓僅發現1座,即西城區百萬莊遼墓M2,平面呈八角形,墓室中央長方形磚槽內置骨灰。
2.雙室墓
雙室墓僅發現3 座,由墓道、墓門、前后甬道、前后墓室組成。墓道呈斜坡狀,墓門和墓壁有磚雕仿木構裝飾。平面形狀互不相同。西城區百萬莊遼墓M1前室和后室均為圓形,該墓為丁文
3.多室墓
多室墓僅發現1座,即豐臺區遼趙德鈞夫婦合葬墓。該墓為北京地區發現的墓室最多的墓葬,共三進九室,皆圓形,頂部為穹窿頂。墓室有壁畫,僅存三幅。墓壁有磚雕仿木結構的立柱、闌額、柱頭枋、斗拱、門框、直欞窗等。墓主兩人,其中一人為火葬。
(二)磚石混筑墓
磚石混筑墓均為單室,據墓室形狀可分為圓形和長方形兩類。
圓形磚石混筑墓除門頭溝區新橋街遼墓和昌平區陳莊遼墓M1外,主要發現于龍泉務墓地。此類墓葬多由毛石或花崗石與磚混筑,構筑方式略有不同。門頭溝區新橋街遼墓外壁由毛石砌成,內壁由勾紋磚砌成。昌平區陳莊遼墓墓門及墓室下部圍壁由花崗石砌成,上部由勾紋磚壘砌。龍泉務墓地部分墓葬墓道南端設祭臺,墓壁由不規則形石塊壘砌,起券部分以上用勾紋磚券筑。墓室多砌棺床,形狀有半圓形、長方形。
長方形磚石混筑墓僅發現西城區大玉胡同遼墓1座,墓壁由勾紋磚砌成,墓底鋪磚,墓頂用石板覆蓋。
磚石混筑墓有合葬,亦有單葬。葬具有磚槽、磚龕或磚棺。
三、幾點認識
1.北京地區遼代火葬墓有土壙磚室墓和磚石混筑墓兩類,未見豎穴土坑墓和石室墓;平面形狀多為圓形,方形較少,晚期出現六角形及八角形。墓內流行仿木結構和壁畫裝飾,多設置棺床。墓葬規模的大小及隨葬品多寡與墓主身份地位有關。
2.目前發現最早有紀年的火葬墓是遼應歷八年(958)的豐臺區趙德鈞夫婦合葬墓,其后有統和十五年(997)的石景山區韓佚墓,咸雍五年(1069)的洪茂溝遼墓,咸雍七年(1071)的海淀區中國工運學院康公墓,天慶元年(1111)的西城區百萬莊遼墓M1和天慶三年(1113)的大興區馬直溫夫婦合葬墓。此外,發掘者依據墓葬形制及隨葬器物演變,大致確定了崇文區彭莊遼墓M1不早于遼圣宗時期,昌平區陳莊遼墓為遼末金初,門頭溝區新橋街遼墓屬于遼代晚期,密云大唐莊遼墓M14、M15為遼代晚期,龍泉務遼墓為遼代中晚期至金初,大興北程莊遼墓為遼代中晚期。由此可見,北京地區遼代早期的火葬墓并不多見,大量出現于遼代中晚期。
3.北京地區遼代火葬墓墓主族屬以漢人為主,契丹人少見。目前僅有昌平區陳莊遼墓墓主為契丹人,其余墓主均為漢人,如洪茂溝遼墓為國子監祭酒董匡信和妻王氏,豐臺區趙德鈞夫婦合葬墓為盧龍軍節度使中書令趙德鈞和妻種氏,石景山區韓佚墓為營州刺史檢校工部尚書韓佚和妻王氏,海淀區中國工運學院康公墓為檢校尚書右仆射康貴,大興區馬直溫夫婦合葬墓為右散騎常侍馬直溫和妻張氏,西城區百萬莊遼墓M1為潞縣商曲鐵都監丁文
4.遼代中晚期北京地區漢人流行火葬主要受佛教影響。有遼一代,佛教極其盛行。燕京(今北京地區)佛教為遼五京之首,“僧居佛寺,冠于北方”,成為遼代佛教發展的基地。北京地區遼代火葬墓中發現的佛教因素亦可看出其火葬習俗深受佛教影響。如大興區馬直溫夫婦合葬墓采用真容骨灰葬,這是佛教火化埋葬方式的典型代表。大興北程莊遼墓部分墓葬頂部為塔形,塔為佛教中的紀念性建筑。石景山區韓佚墓墓室穹頂正中繪蓮花,墓壁起券處還有12個磚雕蓮瓣影作,蓮花作為佛教教義的表征,是佛教裝飾藝術的常用題材。豐臺區趙德鈞夫婦合葬墓中出土銅質迦陵頻伽的佛教色彩也很濃厚。海淀區中國工運學院康公墓出土的墓志云:“咸雍七年歲次辛亥當四月丙辰朔八日癸亥逝,往中京大定府鎮國寺北街出廓火葬訖,遷神柩來于先祖墳塋……”[17]志文說明康貴死后是依佛禮就近舉行儀式火化的。
除受佛教影響外,遼代中晚期北京地區漢人流行火葬還受契丹火葬風俗的影響。據《北史·契丹傳》載,契丹人“其俗與
————————
[1][2]蘇天鈞:《北京郊區遼墓發掘簡報》,《考古》1959年2期。
[3]蘇天鈞:《北京西郊百萬莊遼墓發掘簡報》,《考古》1963年3期。
[4]蘇天鈞:《北京南郊遼趙德鈞墓》,《考古》1962年5期。
[5]蘇天鈞:《近年來北京發現的幾座遼墓》,《考古》1972年3期。
[6]馬希桂:《北京先農壇遼墓》,《文物》1977年11期。
[7]張先得:《北京市大興縣遼代馬直溫夫妻合葬墓》,《文物》1980年12期。
[8]黃秀純,傅公鉞:《遼韓佚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4年3期 。
[9]周景城等:《北京昌平陳莊遼墓清理簡報》,《文物》1993年3期。
[10]劉義全:《門頭溝新橋街遼墓》,《北京考古信息》1990年1期。
[11][17]朱志剛:《海淀中國工運學院遼墓及墓志》,《北京文物與考古》第六輯,民族出版社,2004年。
[12]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亦莊考古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09年。
[13]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奧運場館考古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07年。
[14]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龍泉務遼金墓葬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09年。
[15]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密云大唐莊白河流域古代墓葬發掘報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16]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大興北程莊墓地》,科學出版社,2010年。
[18]《北史》卷94《契丹》,中華書局,1974年,第3128頁。
〔責任編輯:張金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