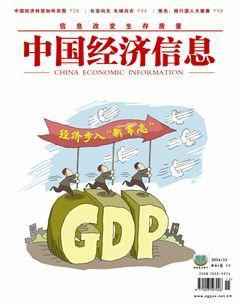金磚國家“平行金融體系”三大隱憂
王靜文
“金磚五國”切不可沾沾自喜,試圖與發達國家徹底“脫鉤”,到“平行金融體系”中去尋找安全感。
7月15日,“金磚五國”領導人在巴西福塔萊薩簽署協議,宣布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并且將上海作為新建開發銀行的總部,由印度選出首任行長;同時建立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
經濟實力與金融權利的不對等,以及現有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惰性,使“金磚五國”萌生了另立門戶的念頭。早在2012年,五國就曾提出金磚銀行的暢想,并在去年南非德班的金磚峰會之后正式提上日程。經過一年多的醞釀和準備,金磚銀行與應急儲備安排同時落地。
從功能定位來看,金磚國家銀行同世界銀行極為類似,主要是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中長期低息貸款,滿足其在基礎設施等方面的資金需求。而金磚國家應急基金,則明顯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翻版。眾所周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當今國際金融體系的兩大基石。金磚國家試圖在此之外打造了一個“平行體系”,既體現了對發達國家的失望和不信任,也反映出創立一個更適宜、更便利、更有彈性的金融發展環境的訴求。
愿望固然美好,但最終能否實現,還需要各方付出艱辛的努力。至少從目前來看,這一“平行金融體系”可能還面臨著以下三個方面的隱憂。
一是如何兼顧平等與效率。從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發展歷程來看,美國居于絕對主導地位。一則因為當時美國的經濟實力首屈一指,二則因為二戰之后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有求于美國,而美國的主導角色也確保了這兩個機構的正常、高效運行。但金磚銀行從醞釀到成立,一直在極力避免某國主導的情況發生,從平均出資到商定總部,這種平等色彩一直貫穿始終。這一方式能夠保證金磚銀行和應急儲備安排的順利出生,但并不能夠確保后續的運行效率。在缺乏主導者的情況下,如何維持這兩個機構的高效運作,平衡其政策性特征與市場化運營模式,可能會是一個考驗。
二是選擇何種貨幣。金磚銀行和應急基金選擇什么性質的貨幣作為信貸、援助活動的媒介將是另一個關鍵問題。目前絕大多數國際和區域經濟組織都以美元作為媒介,但致力于打造平行體系的“金磚五國”,卻未必愿意選擇這么做。那么,是選擇某一國的貨幣還是選擇類似于SDRs的一籃子貨幣?如果選擇后者,都有哪些貨幣有資格進入這個籃子,按照什么樣的比重?這對金磚國家而言,也是一個非常現實的難題。
三是如何應對風險。金磚國家金融體系的發展程度相對滯后,抗風險能力較弱,一旦面臨系統性的金融危機(如美國加息引發外資大規模回流),可能包括金磚五國在內所有的新興經濟體都將受到劇烈沖擊。如果出現這種局面,金磚銀行和應急基金將面臨著如何展開救援的問題。在這一平行體系中,因為缺乏一個“最終貸款人”的角色,一旦遇到某種極端情況,可能難以避免自顧不暇乃至資本耗盡。
總而言之,“金磚五國”切不可沾沾自喜,試圖與發達國家徹底“脫鉤”,到“平行金融體系”中去尋找安全感。因此,理性選擇應該是利用金磚銀行的低廉資金改善本國的基礎設施,利用應急基金的保障防范金融風險,同時盡力提高自己在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和話語權。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