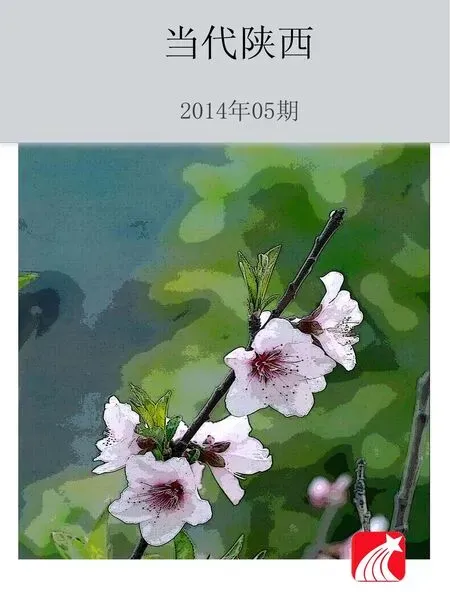移民搬遷倒逼陜南城鎮化“靚變”
文/劉書云 鄭 昕(新華社記者)
移民搬遷倒逼陜南城鎮化“靚變”
文/劉書云 鄭 昕(新華社記者)
干凈寬敞的街道、鱗次櫛比的樓房,綠樹環繞的廣場,這是記者在陜南地區搬遷安置的新社區里看到的景象。
涉及陜南三市240萬群眾的避災扶貧移民搬遷工程,自2011年啟動以來,已將20多萬戶、70多萬人口從秦嶺滑坡等危險區域搬遷至山下安全地帶。“靠城靠鎮靠園區”和“進城入鎮住社區”的集中安置,催生了一大批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新社區。專家認為,這種看似違背規律的“倒逼”法只要引導得當,完全可以成為貧困地區加快城鎮化進程的有力推手。
創新搬遷模式加快移民聚集
以避災為主、兼具扶貧與發展任務的陜南移民搬遷,作為民生工程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記者調研發現,這一工程之所以進展順利,一方面是農民搬遷愿望強烈,另一方面是陜西通過創新搬遷新模式,初步破解了資金困局和移民“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的難題。
根據規劃,陜西省10年內將搬遷陜南危險和貧困地區居民240萬人,需要投入1100億元,其中建房資金就需688億元。而陜南地區28個縣區中有21個國家或省級貧困縣,農民收入也不高,地方政府和群眾個人籌資壓力都比較大。為解決這一問題,省政府在建房資金的籌措上采取政府兜底、群眾封頂、讓群眾少拿錢或不拿錢的辦法,按人均25平方米的標準為搬遷群眾提供基本住房保障。實施集中安置的搬遷戶按照不同的戶型面積分別負擔1萬元、2.5萬元和4萬元,其余資金由各級財政補助,并整合項目資金統籌解決。搬遷群眾中的特困戶、五保戶和孤寡老人按照規定面積由政府免費提供住房。分散安置按每戶3萬元的標準予以補助。這極大地調動了當地群眾的積極性。
為加快推進搬遷步伐,省財政和省有色集團共同出資組建了“陜西陜南移民搬遷安置工程有限公司”,貸款籌集了60億元,主要用于解決移民搬遷的啟動和周轉資金。這筆周轉金在基層移民安置點的啟動和建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與此同時,各地也在積極探索吸納社會資本參與移民搬遷安置。寧陜縣皇冠鎮利用企業和社會資金實施全鎮的移民搬遷,把搬出后的山溝建成了旅游景點,現在投資已增加到20多億元,農民不花錢就住上了寬敞的大房子。
大規模移民搬遷,讓長期在深山居住的農民改變了此前近乎自然狀態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邢錦林是白河縣西營鎮人,2011年搬入集鎮上的天逸社區。“以前住的村子醫療條件太差,孩子上學也要走好幾里山路。現在一家5口人全搬下來,連裝修花了20多萬元買了一套120平方米住房,政府還給補貼了3萬多元。”他說。原來只有7000多居民的西營鎮自天逸社區的移民住進來后常住人口已上升至13000多人,天逸社區二期建成入住后,加上流動人口,這個小鎮人口將達到兩萬左右。記者在小鎮街道看到,這里商鋪林立,人來車往,醫院、學校、幼兒園一應俱全。
據統計,3年來陜南移民搬遷工程總共投入資金359億元,搬到城鎮規劃區的群眾占到總搬遷人口的50%以上,超過12萬人“進城入鎮住社區”,這個規模相當于把陜西城鎮化率提高了3.47%。當地干部認為,從長遠看,通過搬遷擴大城鎮人口,建設新型移民社區,可不斷增加新的消費人群、擴大內需,有利于城市經濟的發展和城鎮化程度的不斷提高。預計經過10年建設,整個陜南地區城鎮化率可提高10至20個百分點。
陜南干部群眾開始把搬遷當作一項任務來做;之后覺得這是本地一個發展機遇,全力攻堅克難做好;直到近一年來,才意識到移民搬遷對于陜南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來說不啻為一場‘革命’,因為群眾生活方式的轉變和當地經濟發展模式、產業結構的轉變都面臨巨大的轉變,開始主動積極地做。
社區化集中安置造就“新社區人”
住在白河縣西營鎮的潘布國,2012年一家5口搬到天逸社區居住。在他花費20萬元購置的新居中,客廳一角擺滿了盆栽。“以前在城里打工,很向往城市人的生活,現在有條件進城鎮,住進了樓房,盡管不像以前是獨門獨院,但也慢慢習慣過上城市人的生活了。”他說。
還有很多像潘布國這樣通過陜南移民搬遷入集鎮、住社區的群眾,生活方式和習慣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在安康市漢濱區晏壩鎮,每到晚飯過后,鎮中心幼兒園門前的廣場上都聚集不少打羽毛球和跳廣場舞的人;在漢中市西鄉縣楊河鎮,安置戶也習慣了在傍晚走出家門,搬把凳子到廣場的大屏幕前一邊聽新聞一邊聊天。
“以前住在山里,根本沒什么娛樂活動,除了打牌,就是串門走親戚。現在搬下來鄰里多了,也有更多的社區活動可以參加。”搬到晏壩鎮移民社區的王永勝說,現在他很享受每晚和3個孩子一起坐在沙發上看電視的感覺,這與城市人下班后的生活沒什么兩樣。
在現有情況下,群眾沒有條件想住在哪里,公共服務就能配套到哪里。因此,用集中安置的方式,以較小成本為大部分人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務,是實現公共服務城鄉均等化、為搬遷戶提供和城市人一樣的生活條件的途徑。
省委農工辦主任鄭夢熊認為,如果公共設施的配套程度能夠維持一個城市人的正常生活習慣,縣城、城鎮相比大城市有其比較優勢。
從鄉村到社區,搬遷戶生活環境的變化直接導致其生活習慣的變化。“一是改變了農民的居住條件,二是改變了農民的生活環境,三是轉變了農民的生活理念。農民互相之間思想也在影響,比如你創業了,我就跟著你學。”安康市副市長鄒順生這樣形容“新社區人”觀念的產生。

盡管住進了樓房,村民們依然保持著一起“烤火盆”這種睦鄰習慣。
“衛生問題,原來在農村隨地吐痰、大小便,現在社區有專門從事清潔的人員;以前農民做飯、取暖都靠燒柴,現在進屋就有煤氣灶和電,這既保護了生態環境,也讓搬遷戶有了現代環保意識。”鄒順生說,住在新型社區,享受著和城里人幾乎均等的公共服務,搬遷戶真正有了城市人的生活觀念,才是陜南移民搬遷工程避免在未來出現“空殼化”的保證。
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院賀東航教授認為,采取綜合考慮的城鎮化,基本解決就業問題,確保貧困人口在城鎮化過程中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實現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當群眾的養老、醫療等方面得到保障,貧困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人口有了集中度產業有了聚合度
白河縣茅坪鎮棗樹社區的一家服裝加工廠里,七八名女工正在縫紉機前埋頭工作。35歲的楊女士說,她們都是棗樹社區的居民,在2008年之后陸續從山中住進社區。“這家廠子是計件工資,我們的工作時間很靈活,平時有四五十人在這里工作。”楊女士說。
社區干部楊登寶告訴記者,這個社區不僅有一家外地人投資的制衣廠,還有一家面條加工廠,規模都在50人以上。另外,超市、發廊、打印店等在社區里也有很多家,都是當地搬遷戶經營的。
在西鄉縣桑園鎮,食用菌作為主導產業,在移民搬遷的人力和資金的聚集下已初具規模,目前有食用菌專業合作社7家、食用菌生產大棚150個。浙江人卓炳長2013年在火地溝村搬遷安置點周邊投資300多萬元生產“云和師傅”黑木耳(帶料),雇傭的50多人里大部分是搬遷戶。
卓炳長的房東范湖芳就是其中一位,她2012年7月從山里搬遷至火地溝村移民安置點后,不僅把老家的土地流轉出去種核桃,自己每年春季還會外出采茶,再加上丈夫的打工收入以及房屋租金,相當于有4份收入。“現在收入多得以前根本不敢想。”她說。
桑園鎮副鎮長秦學寶說,該鎮有11萬畝森林資源,每年發展木耳1.5萬架,香菇1萬架。“作為鎮上的主導產業,我們加大食用菌種植產業的投入,一方面保證了一部分搬遷戶的就業、創業,另外參與進去的村民多,產業也更容易擴大。”
對于自2011年工程啟動以來完成搬遷的70萬群眾來說,在新社區購置新居是最大的投資之一。盡管有政府補貼,不少人還是花去了幾乎前半生的積蓄,還有人向親友借錢,至今沒還上。
鄒順生表示,人們搬下來后開支可能比以前大了,要買糧買菜、交物業管理費,現實經濟情況倒逼著搬遷戶去思考發展的問題,去創業致富。“有的人祖祖輩輩住在山上,勉強自己解決了生計,很可能就不會費心考慮致富,現在他們必須積極尋找致富門路。”
陜南移民搬遷重視產業配套,特別是安康市“一區一策、一戶一法”政策的實行,要求實現搬遷戶每戶主要勞動力至少掌握1到2門致富技能、至少有一人穩定就業,夯實了“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搬遷目標的基礎。
在平利縣,政府依托現代農業園區、工業園區和旅游景區建設,引導搬遷戶從事務工、經商、旅游服務等二、三產業,搬遷戶收入由單一的種養業逐步向加工業、運輸業、服務業、勞務輸出等轉變,拓寬了增收渠道,加快了致富步伐。經統計,搬遷戶的年人均純收入,由搬遷前不足3500元增長到目前的7000元以上。
而在紫陽縣雙橋鎮,兩年內將搬遷700余戶,千畝示范茶園和8萬畝厚樸基地成為搬遷戶增收的重要來源。蒿坪鎮硒谷生態工業園區聚集了一批勞動密集型企業和食品加工企業,吸納附近的雙星移民安置社區農民就地變身職業工人。紅椿鎮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紅椿盤龍茶葉公司新建茶葉示范園區,帶動8個茶業專業村的4500名茶農成為職業茶農。
“移民搬遷促進城鎮化這個路子能不能走通,不取決于能不能把人搬下來,而是取決于產業。”鄭夢熊認為,如果產業配套跟不上,人們通過工程可以搬下來,但三五年后的發展就成了問題。“要布局一些對環境影響不大的項目。應當吸收當地的民營資本參與搬遷工程,因為民營資本擁有企業和產業,它的參與會把配套產業考慮進去。”
社區化管理倒逼干部“官念”轉變
“短短3年時間里,陜南的干部群眾對移民搬遷工程的認識經歷了三個階段。開始是把搬遷當作一項任務來做;之后覺得這是一個機遇,全力攻堅克難做好;近一年多來,不少干部才意識到移民搬遷對于陜南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來說不啻為一場‘革命’,因為群眾生活方式的轉變和當地經濟發展模式、產業結構的轉變都面臨巨大的轉變,開始主動積極地做。”安康市扶貧開發局副局長薛玉發說。
從被動到主動,從管理到服務,陜南涉及到移民搬遷的干部特別是基層干部的“官念”與“管念”隨著移民搬遷工程的深入,也產生了巨大的轉變,“與安置戶們住得更近了,服務熱情也更足了。”棗樹社區干部楊登寶說。
今年50歲的陳玉明,八十年代就當村干部,陜南移民搬遷工程啟動后,他所在的黑虎村合并入晏壩鎮中心社區,他也由村支書變成了中心社區管委會的主任。“以前在村子,無論什么事情,都是用行政命令壓下去。現在不僅要解決社區日常用電、用水,給群眾提供便民服務甚至紅白事都要由社區牽頭,統一管理,工作壓力明顯比以前大了。”陳玉明說。
“一些村轉變成社區,村干部經培訓后去做社區管理人員,協助日常的衛生環境、供電供水。過去群眾找你得跑三四十里地,現在就住在家門口了,這樣節省了行政成本,社區管理服務質量自然有了提高。”李永平認為,在新社區形成小政府、大服務的格局,村委會的管理體制在社區形成需要轉變,過去的官員需要把身份變成服務者。
“過去的行政管理政府責任小,兜底的是群眾。城鎮化的要求倒逼移民搬遷,就是政府要把困難攬在身上,想辦法把握問題、解決問題,給群眾更大的空間。”省國土廳副廳長雷鳴雄說。
“干部觀念的轉變是要害,基層干部能夠形成共識,要按照省、市的思路去開展工作,都是要在實踐中造就的。干部認識的轉變慢慢跟上來,實踐會告訴他們需要怎樣做。”在薛玉發看來,干部的所見比所學更重要,安康市定期組織現場會培訓,讓干部到小區去感受、體會。
而鄒順生則總結說,移民搬遷是一個歷史過程。“必須要用歷史的眼光和態度對待這個過程。工程啟動才三年多,現在談成功為時太早,要靠歷史的檢驗。至少是這個地方的人在心理和文化上與新社區逐步融合,生活質量穩步提高。”他說,“到了現在搬遷戶的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當你問他‘你的家在哪里’時,他給你指他現在住的新房子,而不是十幾里外的山上、溝里時,到那時再談成功與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