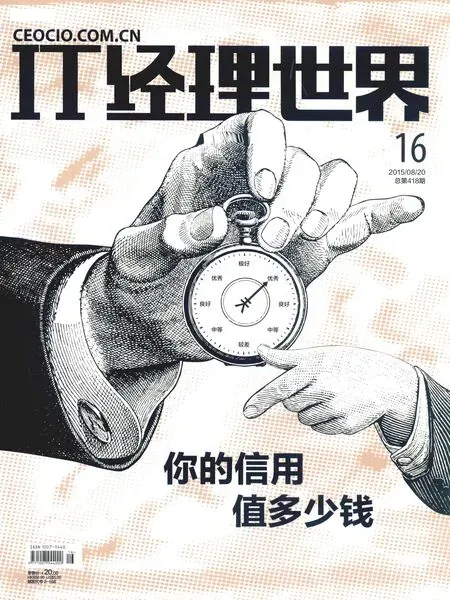員工賦能面面觀
員工賦能踐行出色的企業(yè)也通常是領(lǐng)先競爭對手的行業(yè)翹楚,那么當(dāng)中有什么訣竅?
“在我第二次錯(cuò)過叫醒服務(wù)的電話后,一位前臺(tái)的侍者親自上樓來,優(yōu)雅地敲響了我的房門……”
盡管并不身負(fù)“秘密試睡員”的角色,但資深客戶服務(wù)與體驗(yàn)咨詢師米卡·索羅門先生還是對其下榻的麗思卡爾頓酒店的溫馨服務(wù)留下了好印象。他起身之后來到了樓下鱗次櫛比地排列著棕櫚樹的露臺(tái)餐廳,帶著愉悅感目睹了一眾服務(wù)生在那里布置餐臺(tái)。
索羅門后來在其《福布斯》專欄中寫道,“乍看之下這簡直就像一場魔術(shù)秀,但它如此滴水不露,讓人無從挑剔魔術(shù)師的生疏做作,也無從辨識(shí)參與其中的哪怕一員技藝業(yè)余或心不在焉……一種行云流水般的高效自我管理是精彩呈現(xiàn)出什么是嶄新層面的領(lǐng)導(dǎo)力——而這種展示將那些只在監(jiān)督下才會(huì)出現(xiàn)的逢場作戲的勤勉劃入了可笑地帶。”
的確,在這家星級酒店,自主導(dǎo)向管理作為“員工賦能”理念的一個(gè)重要部分而全面推行,一名叫作Erika的酒店一線員工也對這種管理方式予以充分肯定:“酒店讓我在維護(hù)客戶至臻體驗(yàn)方面擁有很大的自主權(quán)。這不僅讓客人常常感到出其不意的驚喜,于我而言這份工作本身也變得更生動(dòng)、更有意義。”
事實(shí)上,員工賦能踐行出色的企業(yè)也通常是領(lǐng)先競爭對手的行業(yè)翹楚。明尼蘇達(dá)礦業(yè)制造公司(也就是3M公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即歸因于員工賦能。公司鼓勵(lì)員工支配其15%的工作時(shí)間用于“不務(wù)正業(yè)”:無論是立項(xiàng)一個(gè)創(chuàng)新研究或是啟動(dòng)某個(gè)跨部門合作,等等。——而如此的賦能投入回報(bào)也是相當(dāng)可觀:便利貼就是一款誕生于貌似不經(jīng)意的靈感碰撞中的創(chuàng)新產(chǎn)品,而它卻獲得了風(fēng)靡全球的佳績,并為3M公司帶來每年超過1億美元的收益。
而在另一家企業(yè)——星巴克——索性“員工”的概念被“星巴克伙伴”所替代。這家員工流動(dòng)率比行業(yè)平均水平低250%的公司成功搭建了一派獨(dú)特的企業(yè)文化,使賦能、創(chuàng)業(yè)家精神、高尚品質(zhì)和至臻服務(wù)成為定義價(jià)值的核心元素。公司還建立了一套嚴(yán)謹(jǐn)完善的培訓(xùn)體系,用以幫助“星巴克伙伴”們來向客戶推廣咖啡文化,包括普及咖啡知識(shí),增進(jìn)客人對咖啡生產(chǎn)地的認(rèn)知等;在一定年紀(jì)的員工中,針對“領(lǐng)養(yǎng)孩子者”群體提出的希望多一點(diǎn)時(shí)間陪孩子的訴求,星巴克特別辟出了每年兩周的額外帶薪假期,以助他們獲得與子女相伴的幸福時(shí)光。而對較年輕一族,星巴克最近宣布將為他們報(bào)銷兩年的大學(xué)學(xué)費(fèi)——CEO舒爾茨對這個(gè)新推行的教育激勵(lì)機(jī)制也異常重視,他說不希望“星巴克伙伴”因?qū)W歷門檻而落后于這個(gè)經(jīng)濟(jì)高速發(fā)展的時(shí)代,星巴克希望這項(xiàng)措施能夠重建他們的美國夢。
英國克蘭菲爾德大學(xué)管理學(xué)院學(xué)者Yasar Jarrar博士與布拉德福德大學(xué)M.Zairi教授圍繞員工賦能課題發(fā)表的一份研究報(bào)告,提煉了該領(lǐng)域管理實(shí)踐的若干成功因素——
最佳實(shí)踐思路之一:員工應(yīng)能最大化地參與決策。美國西南航空公司可謂是管理教育者最為津津樂道的案例(可能已經(jīng)到了“祥林嫂”般重復(fù)而令人煩心的地步),不過從員工賦能的視角來看,西南航空的確在業(yè)界獨(dú)樹一幟。有一位著名作家某次登機(jī)時(shí)竟然忘帶身份證件,這在其他航空公司鐵面無私的政策面前一定會(huì)遭遇不小的麻煩:一線地勤須向上級逐層匯報(bào)請示,而即使能等來一份人性化的批復(fù)沿著漫長的匯報(bào)通路而返至一線時(shí),乘客大抵是要面對誤機(jī)的無奈事實(shí)。但這種情形在西南航空不會(huì)發(fā)生:值機(jī)服務(wù)臺(tái)的員工可以自行定奪核實(shí)乘客身份信息的方式——同樣的案例中,他們可借助作者出版作品的封面來驗(yàn)明正身,讓乘客無憂登機(jī)。
西南航空將員工責(zé)任心視為最寶貴的無形資產(chǎn)之一,對組織架構(gòu)中的鐵板一塊屬性進(jìn)行設(shè)限,而更多的是賦予各個(gè)工作委員會(huì)甚至員工個(gè)體以決策權(quán)力,來處理工作中的大小事務(wù)。而有效的員工賦能又反過來促進(jìn)了運(yùn)轉(zhuǎn)高效,以及乘客的便利和貼心,也使西南航空成為客戶最少投訴的承運(yùn)人和業(yè)界品牌標(biāo)桿。
最佳實(shí)踐思路之二:員工有權(quán)決定自己工作場所的環(huán)境設(shè)置。“即使不銷售任何咖啡飲品,星巴克也依然能讓顧客流連忘返,“在《體驗(yàn)星巴克》一書中,作者援引了一位隨機(jī)受訪的消費(fèi)者這樣的評述,“他們完全可以做到只收取入場費(fèi),然后為公眾提供一個(gè)回繞著Bob Marley音樂的舒適空間,也同樣能保證穩(wěn)定的客流量。”
作者寫道,星巴克人心懷臻求完美服務(wù)的真誠愿望,讓消費(fèi)者在這樣一個(gè)環(huán)境氛圍中自始至終體驗(yàn)卓越的貼心服務(wù)——這種服務(wù)在星巴克與客戶之間產(chǎn)生的共鳴要遠(yuǎn)比那些例行公事的問候來得強(qiáng)烈。
最佳實(shí)踐思路之三:員工應(yīng)對自身的工作目標(biāo)問責(zé),也更應(yīng)該有權(quán)力去打破固有規(guī)則,從而保證優(yōu)質(zhì)的服務(wù)和客戶的綜合滿意度。當(dāng)然,“打破規(guī)則”并非意味著突破法律規(guī)則或者公德束約,而是旨在改變因循守舊的習(xí)慣、尾大不掉的沉珂,以及那些在執(zhí)行中漸漸變成呆板“規(guī)則”的一切——諸如模式、節(jié)奏、傾向性方針等。
前文提到的麗思卡爾頓酒店,但凡客人發(fā)生物件損壞或者其他突發(fā)問題,行李服務(wù)生和門童均可以“在現(xiàn)場”(不需要走流程請示)自行裁定最高達(dá)2000美元的預(yù)算費(fèi)用來解決客人遇到的問題。該酒店能夠贏得波多里奇國家質(zhì)量獎(jiǎng)(MBNQA)想必亦是實(shí)至名歸。
值得一提的是,員工“賦能”(empowerment)與“授權(quán)”(delegation)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員工賦能使得眾多一線員工投身到改善服務(wù)、解決問題和創(chuàng)新產(chǎn)品的進(jìn)程中去,強(qiáng)調(diào)的是決策力賦予和自主管理導(dǎo)向,并能讓客戶得到更好的直接服務(wù)與體驗(yàn)。而員工授權(quán)則是經(jīng)理人將工作分配至下屬,從而將經(jīng)理人從事無巨細(xì)的微觀管理中解放出來,盡管他依然要對分配下去的工作進(jìn)度、交付和質(zhì)量進(jìn)行跟蹤和監(jiān)督。
而在學(xué)術(shù)界,對員工賦能這一做法并非無人持批判視角。例如,有主張?jiān)诠緳?quán)力結(jié)構(gòu)中如果缺失了直接上下級的責(zé)任代表關(guān)系,則可能使得實(shí)際權(quán)力聚居于公司頂層,最終讓“員工賦能”演變成“員工失能”。另有學(xué)者批評說,賦能管理在某些情境下會(huì)變成“僅是以不明顯的控制手段來加劇約束員工”,諸如用工作團(tuán)隊(duì)制約方式使員工無不時(shí)刻置身于“同儕競爭”(peer pressure),而這種競爭壓力反而對員工帶來更明顯的權(quán)力剝奪感,從而無所適從。
(曹嘉建對本文亦有貢獻(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