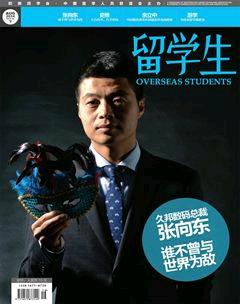專訪香港科技大學首席副校長史維:左手治學,右手治校
張曉雅


史維,出生于臺灣,美國密歇根大學航空工程學博士,曾任職于美國通用公司全球研發中心、美國空軍研究實驗室,全球第一條計算機研發的飛機引擎燃燒室方程式的發明者,現任香港科技大學首席副校長
7月30日,在香港科技大學的辦公室里,記者見到了史維。這位美國空軍研究室的前首席研究員,全球第一條用計算機研發燃燒室的方程式的發明者,他的一切似乎都與飛機、戰斗機有關。
史維的辦公室,一走進去便看到亮點,不大的空間里整齊地擺放著各種航空航天的飛行器模型。史維笑著幫助《留學生》記者辨認模型屬性,用手來回一揮:“航天在右邊,航空在左邊。”然后,他拿起一架P-38J Lightning戰斗機模型詳細解說,這架曾被當時的軸心國成員稱為“雙身惡魔”的戰機是他最喜歡的飛機,曾因擊落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元帥的座機而扭轉二戰局勢。
于是,我們的談話便從那些神秘的飛行器說起。
“GE賣了很多飛機引擎,我有貢獻”
史維成長于臺灣,20歲便赴美求學。在密歇根大學獲取博士學位之后,他進入位于紐約的通用公司(GE)全球研發中心工作,研究飛機引擎燃燒室。在GE工作的五年里,他成就非凡,寫出全球第一條用計算機研發燃燒室的方程式,這一模式GE至今使用了二十多年,制造出更為精密的CMF56發動機被廣泛用于波音737以及F-16戰斗機。史維笑言:“GE賣了很多飛機引擎,我覺得我有貢獻。”離開GE赴佛羅里達大學教書,那時他正值而立之年。
其后,他離開通用公司,任美國空軍研究實驗室、波音航天科學合作中心的首席研究員。
1988年后,史維開始在美國一些大學中任教,并先后任職于美國佛羅里達大學與密歇根大學。2010年9月,史維離任密歇根大學航天工程學系系主任一職,回到中國,出任香港科技大學首席副校長,主管學術。
剛到香港的史維,依然難以割舍他所熱愛的航天器引擎研究。
在香港科技大學工作的前三年,史維在密歇根大學仍然保有自己的科研團隊。他說,作為學術帶頭人,不能因為工作轉變而撒手不管。香港與密歇根時差12小時,所以到香港上任的前三年里,史維結束在香港的工作之后,回家仍要隔著太平洋參與討論。暑假里,密歇根團隊的學生會飛到香港與他會合做研究。
因為史維在過去30年中于航天器引擎方面的杰出成就,他先后被評為美國航天及宇航學會、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院士,并獲得美國航天及宇航學會2003年Pendray航天文獻獎、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2005年熱能轉換紀念獎等。
保護“非主流”
對史維而言,離開亞洲三十多年之后的回歸,是一種情懷。他對《留學生》記者解釋促使自己歸來的動機:在美國待久了,想回來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對個人職業和家庭來說都是全新的體驗。
“說老實話,我們是中國人,都希望對社會人民有一點所謂的貢獻,當然這講起來比較抽象,但也是一直以來的情懷。”
史維個子很高,以至于走路步子也邁得很大。他和善儒雅,說話邏輯輕快,言談間多有笑聲,他的同事用“陽光”一詞來形容這位校長。香港科技大學數學系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勵建書曾向媒體這樣評價史維:“他沒有做過院長,直接從系主任做了副校長,認識他之前,我對他沒有觀點。但和他交談一次后,就知道這個副校長找對了。他是那種非常Sharp的人,你的需要他可以第一時間理解,并給予充分支持——資源上、情感上、態度上。事實證明,他不僅學術很強,也是個非常厲害的行政人才。和這樣的人共事你會非常服氣。”
2011年,香港科技大學首次超過東京大學、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等亞洲老牌名校,在“QS亞洲大學排名”榜上拔得頭籌,并在之后連續三年穩坐頭把交椅。2014“QS世界大學排名”中,科大位居34。
采訪中,談到而今的科大,史維多次強調,香港科技大學的崛起與當年創校者密不可分。“我入職時科大發展得已經很好,教授平均素質很高。創校時的校長、院長、系主任和資深教授都已在美國學術界有相當的成就和地位。他們對科大的定位很明確:第一,我們會是一所非常國際化的大學;第二,對教授的要求相對嚴格。”
史維作為學術副校長,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為學校延聘教授,這一過程復雜嚴格。他向《留學生》記者舉例說明:聘請一位教授,需要經過學系、學院再到學校三個級別的教授委員會審核,并且同時要請系主任、院長與副校長三位學術行政主管復核,最后遞交校長,除非是程序犯規,否則校長不能否決。能闖過重重關卡獲得聘任的機會實在微乎其微。史維說:“這一點科大做得跟美國一流大學相比絕不遜色。”
當然,史維也主管科大的學術研究管理。相較挑選人才的清晰嚴密,學術研究則是獨立于苛刻行政之外的系統,可謂不拘一格,對人才的保護也尤為關鍵。他說:“對大學而言,很重要的起點是我們尊重獨立性,尊重原創性,尊重不同的想法。即便這個人只是極少數,我們也要保護他。”不強調所有人都做主流研究,越是非主流越應保護,史維特別提到:“而且‘非主流又如何被定義呢?只能給予空間,尊重創造性、原創性,拋棄階層意識。學校不是一言堂,學術研究不是說靠大多數決定,這不是一個民主的東西,不是投票決定的事物。”
相較香港其他大學,科大“國際化”得更徹底,這些與眾不同當然與它年輕有關,“可也不只是年輕,學校的同仁努力想要把科大發展得更出色,這樣的企圖心非常旺盛。”言談間,史維對自己的同仁與學生持有無比信心。
此時的史維,已然完成從科學家到教育家的轉變。
科大給全世界培養人才
留學生:近年,香港科技大學招收了很多內地高考狀元。
史維:按香港教育制度的規定,香港高校可招收20%的非本地生,今年科技大學招收了150名內地生,比往年稍微少一點。香港的大學門檻高,基本是四五十個學生中錄取一個,不過這四五十人都有希望,狀元并不是唯一,并且入校也需要再經過面試。我大學老師當年跟我講:“你要做第一流,不需要做第一名。”這很有想法。
留學生:香港社會有一些爭議,說香港把太多的教育資源給了內地生,你怎么看?
史維:我們來借鑒美國,美國今天能在國際上保持各方面相當大的領先優勢,當然是因為能夠吸收各地人才。美國大學的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的研究生超過50%是外國人。雖然香港面積小,吸收能力可能受到挑戰,這是爭議的角度,而并非說學生質量不好。其實香港科技大學尤其對研究生類招收本地生花很大力氣,有特別專款,希望給本地學生一些支持。但是個人對前途定位不一樣,如果說讓本地生失去機會,這不是公平的說法。此外,即便把學生比例全部換成來自一個地方,他們的學術都不會有問題,但無法保持學校國際化的本質。我們的政策是,中華區學生最多50%,另外50%非本地生從全球招收,科大的學生來自于全世界60多個國家,不是交換生,他們都是我們自己錄取的。
留學生:香港的科技產業并不發達,所以有一種觀點認為:“科大是給外地培養人才”,你如何看這點?
史維:社會發展會有很多變數,重要的是所有學生各得其所,真正發揮最大的人生價值。學校以培養學生為前提,科大受香港政府資助,自然應該對香港有回饋,可是回饋不是賣雜貨,不能短視。以美國為例,美國的大學是各自所在州資助設置,不能說在麻省訓練的學生,去紐約上班就會有問題,很多年之后,學生也許會回來扮演不同的角色。過去臺灣一直講人才外流,每年好幾千大學畢業生去了美國。可是到了80年代,臺灣經濟很大一部分就是這些從美國回來的人所創造的,臺灣半導體工業世界領先,就得益于許多人才從美國的回流。
科大憑什么“一流”
留學生:在2014“QS世界大學排名”中,科大位居第34位,你如何看待類似的大學排名?
史維:排名有指標性的合理,但不是絕對的合理。如果說這所學校什么都排不上,那一定是有問題的,排名有依據性。尤其亞洲社會把排名看得非常重要,覺得第一名比第二名好,第七名比第八名好,這不合理,任何排名都是有限的框架,給學校全面打出一個總分而已,不同學校總分差別很多時候都是相對而言。應該考慮這所學校是不是第一流,而不是第一名。如果認為科大不是第一流的學校,那一定是我們事情沒做好。全世界這么多學校,今天第一,明天第八,后天第十,都正常。排名看太重,會失去對大學的信心。科大沒有醫學院和法學院,那拿我們與哈佛相比,有很多不合理,哈佛的工學院比科大少,科大工學院甚至比哈佛要好,科大商學院有本科生,哈佛沒有,如果要制定客觀架構比較本身就困難。但家長和學生希望能給出簡單答案,我們必須接受。所以從負責的態度,我絕對不可能也沒有資格說所有排名我們完全不在乎。在這個時代,沒有一所大學可以說不在乎排名,但在學校內部就沒有必要再提。
留學生:科大沿用了美國一流大學的運作體系,國際化更徹底,是這樣嗎?
史維:大致這樣,但并不完全。“國際化”最基本的定位,是以能夠在國際上有與世界名校相比較的實力而言。另外的期許就是我們的創造有國際影響力。不能說與某一所大學類似,這很被動。雖然學人家要虛心,但其他學校也能學習科大。牛津和劍橋也向科大提出合作意向,完全是互惠平等的前提,這是非常重要的自我定位。否則,我們就一沒自信,二沒方向。
留學生:“多元化”一直是科大立校的根本?
史維:科大從創校起就強調多元化,多元化是學校立足的前提,多元化讓社會、文化更開放。大家的意見、想法、做法不同,相碰撞時才會更具創新。我們希望能保持一些非華裔教職工的比例,是說這個精神能留住。再一方面,男女比例這點也特別重要,但科大做得也不夠好。希望男女學生人數對半,如果沒有達到則表示分配不是很理想。參照麻省理工,它的女性學生數基本接近50%。這樣的環境更開放。
留學生:很多高校非常羨慕科大的經濟實力,你對這點怎么看?
史維:一個學校,沒有硬體,沒有資金,做起來會很困難。可是光有很多經費,一點都不表示有學術氣氛。每3年左右香港的8所大學要寫一個學術研究成果通報,香港教育署依此評分,并進行排名。這是公開的競爭。這一點科大是做得不錯,一直排名第一,并且通常比第二名高出10個點。
給教師最好的待遇
留學生:據說貴校每外聘一名教授,都會提供一套140平方米的海景房給其全家居住,房租只是月薪的10%,情況是否屬實?
史維:大致如此,但并非一定是140平方米。在香港,我們在這方面確實是得天獨厚,教職員宿舍在海邊有400多套。房子分給你之后,只要你在學校當教授,就可以一直住下去,租金為你月薪的10%。月薪高的付得多一些,月薪低的付得少一些。相較市場價格,這個制度也更合理,不管教授之間的資歷深淺、薪水高低,都只是10%的月薪。
留學生:科大對教師的考核與晉升制度是怎樣的?
史維:科大的教授從延聘到入校考核、培養,這幾方面跟美國一流大學相比絕不遜色。創校時期,科大同仁們對科大的定位就很明確,第一,我們會是一所非常國際化的大學;第二,對教授的要求相對嚴格。在科大PHD畢業后留校任教基本不可能,除非是非常特殊的情況。原因很簡單,近親繁殖不是好事,同一個環境培養出來的人風格相近,不是好事。而外聘的教師,從國外的環境,到達中國人的環境他會帶來不同的東西;第三點就是科技大學考核與晉升等制度,從一開始就非常完整,與美國最好的大學沒有差別。獲得永久教職(Tenure)被要求在學術上有獨立造詣,有原創性,當然,他同時也需要在教學上十分優秀。
留學生:我了解到,你們對于教員有一個6年期的考核期。6年后,如果通不過考核,他就會失去工作。
史維:是的,這個考核給教員壓力非常大,在6年之內,你要證明你合乎資格,讓學校對你有信心,認為你獲得終身合同是合理的,這是很大的磨煉。考核要求很清晰明確,系主任要為教員寫一份評估,教員本人也需提交評估報告,然后上報到學院,院長做出獨立判斷,再為之寫一份報告。在此之前,學校會邀請對應領域的專家、國外的著名學者,把該教授的審核材料寄給他,要求他們做評審,寫獨立的審核意見,這并不是一封介紹信,而是從專業角度做出評估,并且清晰到從世界定位來講這位同仁處于怎樣的水平。然后,學校由四個學院各出兩名教授組成校委員會,再將已經過院系審核的報告做一次客觀評審。從系到院再到學校的意見往往不一樣,很有挑戰。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客觀,慎重的評斷。整個過程需要大半年,但每個教授從進入學校到升等為止,這六七年就是為了把研究、教學以及職業上的領導力建立起來。審核不能通過,就一定要離開學校。
留學生:除了永久職的考核之外,每學年對教授都有相應考核?
史維:每年一次,我現正在著手做這事,每年春天這個學期結束前,所有教授一定要交一份年度成果報告,包括教學內容、發表論文情況、有無社會貢獻和其他方面成績,非常全面。經過系、學院再到我評審,用來決定新一年的工資。兩三年前,教員工資與香港政府公務員類似,每年增加比例是固定的,現在要經過考核,幅度也不一樣。比如助理教授剛來學校薪資較低,也需要時間適應,學校對他的鼓勵大于評審,前兩三年支持他適應。科技大學的學術文化是希望資深教授幫助新加入的教授同仁站穩,上升。
留學生:教學部分呢?
史維:教學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有不同方面。學術研究就只是學術研究而已,可學習卻有很多不同做法,若要每個人在所有方面都同樣接受很困難,我們要求按量才適任,支持同事最杰出擅長的方面,真正推進,其他方面不做一樣的要求。
科大氣質是什么?
留學生:作為一名一流大學的管理者,你覺得構成大學最重要的是什么?
史維:大學之所以是大學,最為重要的有以下幾點,一是教育學生,教育學生是傳授知識;二是我們是做科技知識研究的,這是創造知識的層面,希望創造的知識能傳授給學生,這也是我們特別強調研究的原因,不是說只為了學校名聲,我們特別堅信,最好的老師應該也是知識的原創者,學問有相當一部分是原創者貢獻,當然也有更大的權威和更廣闊的知識。科技大學是研究型大學,我們不只傳授,我們也創造,創造成果與其他學校的同仁分享,知識交流會有更多回報;另外我們希望把師生的研究成果貢獻社會。很多大學都很強調這一點,我想這是不同的時代。在這里是沒有層級概念的,我們強調研究的獨立性,如果聘請此人當最基層的助理教授,絕對不是來幫教授打工,這是最大的忌諱,我們絕不允許,否則這個人就沒前途了。
留學生:科大如何落實撥放的研究資金,是否有嚴格的制度規則?
史維:當然,香港的大學科目使用經費,規劃和系統非常嚴明,基本上不可能擅自挪用,或另作他用。科研經費對每位教授來說不見得很多,但使用效率比較高。與美國大學相比,香港又有優勢。美國大學的學校運轉相當大一部分需要依靠科研經費部門支持,但香港有教資會、社會籌款,我們不需要把科研經費分撥一部分去運作學校。
留學生:你覺得,作為一所世界知名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的氣質是什么?
史維:從我的角度,科大的與眾不同當然和它年輕有關,可也不只是年輕,學校的同仁想努力把科大發展得更出色,這個企圖心非常旺盛。如果教授不杰出,教育和研究不杰出,學校只是空殼子。說到底,學校只在做兩件事情:教育出杰出的校友,成為有貢獻、領先、開拓的社會公民;教授做出高價值的研究。其他所有行政機構,是支持者,協助我們的同仁和學生達成目標。學校沒有其他任何任務,學校的任務就是培養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