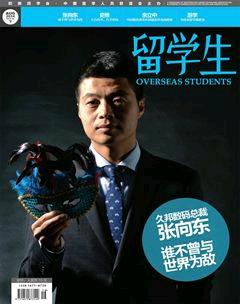海獅樂園
胡剛剛

人類認為動物低等,說不定動物還覺得人類可笑呢
天空把多余的顏料傾倒進大海,令海水變得更加湛藍。揉碎了晨曦的冷風喚醒了靜謐的碼頭,海鷗開始放聲歌唱。靠近碼頭的水面上漂浮著許多木板,木板上布滿了黑壓壓的海獅。一只海獅懶洋洋地橫臥在一塊木板上,把滾圓的肚皮翻過來曬太陽。突然,它被旁邊木板上兩只扭打得正歡的同伴所吸引,只見它們互相頂著胸脯,揚起腦袋,不遺余力地把對方往木板外面拱,兩個烏黑油亮的肉球在此起彼伏的吼叫聲中震顫不停。幾個回合之后,“撲通”一聲,其中一只終于落水。
說時遲,那時快,坐山觀虎斗的海獅猛地扎入水中,緊接著一躍而起,如炮彈般,把剛才的勝利者一下子砸進了海里。在飛濺的浪花中,它面對大海,得意洋洋地昂首高歌起來:“嗷!嗷!嗷!”誰料一曲未完,它就被另一位挑戰者從背后偷襲成功,毫無防備地栽進水里。待它探出頭來時,發現自己原先享受日光浴的地盤早被占據,而旁邊的木板上,一輪新的戰斗已經拉開了序幕。觀望片刻之后,它似乎有些氣餒,戀戀不舍地扭身向遠處游去。
這樣的場景,每時每刻都在舊金山漁人碼頭上演。這些海獅來自何方?又為何而來?有一種說法認為,1989年的洛馬普列塔地震,促使大批海獅放棄了原先的棲息處“海豹巖”來此避難。可后經證實發現,第一批海獅早在地震前幾個月就已定居漁人碼頭,所以海獅的光臨與地震并無關聯。
另一種說法認為,灣區素來氣候宜人、風平浪靜、食物充足、環境安全,所以深受海獅們的青睞。這種說法似乎一直被人接受,直到2009年入冬之時,所有海獅毫無征兆地消失,令漁人碼頭頓時空空如也,人們才開始重新陷入思考。正當學者們排除了氣候變化、食物匱乏、天敵威脅等種種因素,為它們無緣無故地離去而困惑不解時,它們卻在來年春天安然無恙地全部回歸了。從此,它們延續了這個習慣,冬去春來,每年如此。人們猜測它們的遷徙是為了獲取更充足的食物來源,但是沒人知道確切的原因,就像沒人知道它們當初為什么會突然出現在漁人碼頭一樣。
那么它們的“互搏”又是為了什么呢?是為了爭奪陽光?爭奪地盤?爭奪配偶?還是純粹娛樂消遣?也許都是,也許都不是。海獅給我們出了一個又一個謎語,至于答案,恐怕只有它們自己最清楚。
不過它們的到來,無疑推動了當地旅游業的發展。人們在路邊為它們修建了雕塑,豎立了標牌,開展了教育活動,讓漁人碼頭成為了舊金山著名景點之一,每天吸引著成百上千慕名而來的游客。
海獅們知道自己的一舉一動正在被窺探嗎?它們知道自己在人類的世界中早已名揚四海了嗎?也許它們不知道,也許它們不在乎。我們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研究其他物種,卻連自己身上的許多奧秘都沒搞清楚。我們不了解的事物比已經了解的要多得多,“子非魚,安知魚之樂”,人類認為動物低等,說不定動物還覺得人類可笑呢。其實,大家不過是在塵網中掙扎的蜉蝣而已。“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于我歸處。”與其冥思苦想,不如順其自然的好。
太陽升高了,海獅團隊愈發壯大,擂臺賽也愈演愈烈。碼頭旁的店鋪陸續開張,香噴噴的早點氣味在咸腥的海風中彌漫開來。岸邊游客漸漸聚集,各式相機快門噼啪作響,淘氣的孩子們樂此不疲地模仿著海獅的叫聲。在轉身離開之前,我向海面望了最后一眼,一只雪白的海鷗從喧囂的木板上方滑翔而過,在蕩滿了藍柑橘甜酒的清澈中,繪出一道長長的波瀾,然后振翅遠飛,融進燦爛的陽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