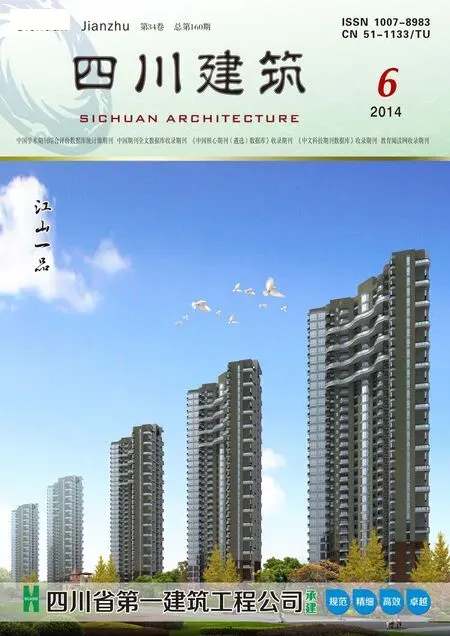地標性建筑設計中的具象化與反理性設計審美傾向
李承來,凌 云,石 巖
(青島理工大學,山東青島266000)
1 地標建筑的概述
地標是指某地方具有獨特地理特色的建筑物或者自然物,游客或其他一般人可以看圖而認出自己身在何方,具有古代北斗星一般的指示作用,例如摩天大樓、教堂、寺廟、雕像、燈塔、橋梁等。國內外有很多知名的地標建筑:如巴黎的凱旋門,美國的聯合國大廈,中國的天安門、東方明珠電視塔等。
地標建筑同其它類型的建筑物一樣,同樣具有兩個層面的內涵:一個是精神層面,一個是物質層面。既然能夠成為地標性建筑,筆者認為也應該從這兩方面來定義:建筑本身是物質層面的最好體現者,高度一定要高,規模一定要大,這僅僅是就它的外表而言。美國的自由女神與英國的大本鐘雖然仍然是地標性構筑物,那是因為城市建設者對其周邊的風貌進行了很好的保護。以其現有的體量而言,放在高樓林立的建筑群體里面,已經很難產生地標性的作用了。
2 地標建筑的三方面功能
現代城市由于人口的聚集,必然形成高密度的都市建筑群體。如果地標建筑想要脫穎而出,除了體量高大外,必然要表現出其設計手法上特殊的一面。要成為“地標”,就要表現出建筑所具有的“場”。筆者認為一個項目能否成為“地標”,要看它是否具備以下三方面的功能:
(1)“地標”性項目對一個區域、一個城市的影響更多地應該表現在其對文化的影響上,它應該是一個“文化策源地”,要看它是否改變了城市的面貌,是否給區域帶來了活力。建筑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建筑帶給城市的改變。
(2)它應該是一個“約會中心”。“地標”項目應該是人們進行各種活動首先想到的聚集地點、活動中心,這是其重要衡量標準。一個“地標”性項目應該能夠滿足人們商務、愛情、聚會、娛樂等各種活動需求,而不是一個與大眾相割裂,僅有漂亮外觀的高層建筑。它應該是融合于城市之中,并能夠影響城市發展進程的,與時尚潮流相融合,并能引領潮流的。
(3)它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城市外景地”。一個地標性項目可以成為一個區域、一個城市的標簽,能夠大量地出現在各類媒體中,以及影視作品里,成為這個城市的代表,是城市里的一道風景線。
在過去滿足以上三個條件的地標性建筑物比較容易出現,尤其是具有歷史性事件的場所,如鄭州的二七廣場(圖1)等。然而到了現代,由于設計手法的多元化與新思潮、新理念對人思維的沖擊,新的地標性建筑也層出不窮的涌現出來,大有“你方唱罷我登場”的趨勢。從大的審美趨勢來說,其中某些建筑具有較為明確的“具象化”與“反理性”趨勢。

圖1 鄭州二七紀念堂
3 地標建筑的“具象化”
3.1 從早期嘗試到現代社會的建筑“具象化”
首先談一下地標建筑的“具象化”。在世界建筑史上,有很多次具象的嘗試。最初18世紀的法國建筑師設計過以男性性器形狀作為平面的妓院。隨著技術和材料的發展,建筑師能戲仿和具象化的物體越來越多。20世紀80年代,美國建筑師弗蘭克.蓋里為廣告代理公司設計的總部大樓(圖2),入口處是一個立著的望遠鏡,這棟建筑為設計者贏得了1989年的普利策建筑獎,被評為“他的建筑是現代社會及人們矛盾價值觀的獨特表現”。近期,在英國倫敦Fenchurch街道上一棟摩天大樓的外形與諾基亞2 600手機極其相像,已經成為了倫敦新的地標建筑(圖3)。可以肯定的說,從建筑審美學角度來看,這幾棟建筑具有非常明確的具象性特征。

圖2 蓋里總部大樓

圖3 倫敦Fenchurch街道摩天樓
而這句話似乎同樣能用在中國的許多新老地標性建筑身上。從早期的“沈陽方圓大廈”與“福祿壽天子大酒店”,到中期的“北京盤古大觀”和“鳥巢體育館”,直至近期的淮南“琴屋”和“四川宜賓五糧液酒瓶樓”,這些建筑本是同樣是活生生的中國當下矛盾價值觀的體現。
3.2 李祖原的具象化設計
其實說起具象性的地標建筑,不得不提到一個人,那就是臺灣設計師李祖原。自從20世紀90年代爆發新建筑浪潮以來,具有象征主義的趣味就操縱城市建筑設計,并制造出各種各樣的具象建筑,由此形成較為特殊的建筑審美浪潮。李祖原的戲劇性在于,一面在臺灣推出高雄85大樓、中臺禪寺、臺北101大樓等具有悉尼歌劇院一般的仿生學特征的上乘之作,足以表達設計師的良好素養,一面卻在中國大陸推出沈陽方圓大廈和北京盤古大觀等具象性作品。而沈陽方圓大廈還先后入列英國《衛報》、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旗下網站的世界最丑建筑排行榜。有人說,這是設計師在中國語境中發生自我分裂的樣本。
筆者看到李祖原回憶當時的設計構思是這樣的:作為其“扛鼎之作”的北京盤古大觀(圖4),建筑的寓意以龍圖騰為外立面的基本造型,覆蓋五座建筑,南側寫字樓頂部為“龍頭”造型,中間三座樓形成“龍身”,北側是“龍尾”。乍一看,盤古大觀確實有巨龍擺尾的意味。由于其獨特的造型,同時又反映出中國特有的民族文化特征,因此給人印象深刻,立刻成為京城新的地標性建筑。然而有的評論認為,這種特立獨行的形態特征,帶有低俗的審美情調。理由如下:由獨立樓體分解的龍體,不僅因造型破碎導致視覺不適,更因猶如被揮刀斬成五段的“死龍”,而走向吉祥寓意的反面。因此無論在感官經驗還是文化象征方面,它都是徹頭徹尾的失敗之作。而同樣是李祖原建筑師設計的沈陽民營企業大樓,則以外圓內方的古代銅錢造型現世,直白到了只剩下赤裸裸的貪欲的地步。這兩件作品,不僅是具象建筑的奇觀,更是當下中國社會狀況的生動寫照。

圖4 北京盤古大觀
另外“李祖原現象”也折射出“甲方”——中國大陸某些決策者的素質和趣味。甲方往往希望建筑具有很強的標志性與廣告作用,最好是具有轟動效應,引發社會關注。設計師在這個過程中間,也只是起到了操作者的作用,并不是決策者。筆者在從事設計的十幾年當中,經常被甲方要求作出各種各樣的具象建筑類型:如菠蘿、蝴蝶、大象等。其實甲方追求的還是吉祥的寓意和廣告效應,在多元化發展的當今社會,也是同樣應該被包容理解的。
3.3 相對極端的具象化設計
不過凡事都有一個限度,過猶不及。北京燕郊的天子大酒店當屬此類建筑始作俑者,其外立面“福祿壽”三星彩塑。雖然2001年曾以“最大象形建筑”之名,榮登世界吉尼斯紀錄,并獲吉尼斯最佳項目獎。然而就其審美層次而言,過于具象的建筑確實降低了作為建筑藝術的審美層次。再如鄭州的宋慶齡基金會大樓(圖5),干脆直接做成宋慶齡雕塑,內含八層寫字間,完全無視雕塑和建筑之間的專業界限。這種極端的設計手法,也是需要進一步推敲的,或者說有待時間去驗證人們的接受能力。

圖5 宋慶齡基金會大樓
4 地標建筑的“反理性”審美趨向
4.1 “反理性”設計的出現
接下來談一下地標建筑的“反理性”審美趨向。理性是人們接受的普遍觀點,但同樣因為審美疲勞,理性主義建筑缺乏吸引人關注的因素,因而漸漸距離地標性建筑漸行漸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技術理性主義由最初的結構理性主義演變發展起來。于是,建筑的基本原理變成了生產和消費的程序,建筑只是通用系統標準構件、技術的應用,以及最大限度的發揮和表現結構、材料等技術手段。以現代派大師密斯為例:密斯的建筑主要體現在密斯對新材料的結構和構造表現,以及將功能抽象概括在完整有序的、常以方格網構成的大空間的方法上。此種思潮影響之下,現代建筑更多的形體變為直上直下的方盒子或者下大上小符合力學原理的塔形建筑。
4.2 “反理性”審美趨勢對于地標建筑的影響
然而到了近代,由于建筑技術的高度發展以及人們對審美需求的不斷深化,越來越多的反理性(或者說反力學)建筑脫穎而出,并且很快成為具有極具欣賞價值的地標性建筑。當人們駐足在一座現代主義思潮影響之下常見的理性主義建筑的面前,都會有似曾相識的感覺,缺乏對于視覺以及大腦的沖擊與震撼;然而假如站在一座反理性的時尚建筑面前,你會發現這棟建筑你過去是沒有看見過的,腦海中是沒有建筑原型的,因而能帶給你更多的思考。當你長時間的駐足觀賞之后,在映入你腦海的同時,它也就輕而易舉的成為了城市的新的地標性建筑,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引領時代潮流。
4.3 “反理性”的地標建筑的幾種表現形式
4.3.1 尺度與比例
反理性首先是對常規尺度與比例的蔑視。眾所周知,所謂建筑形體處理中的“比例”,一般包含兩個方面的概念:一是建筑整體或它的某個細部本身的長、寬、高之間的大小關系;二是建筑物整體與局部或局部與局部之間的大小關系。而建筑物的“尺度”,則是建筑整體和某些細部與人或人們所常見的某些建筑細部之間的關系。尺度和比例是學生時代,被設計老師強調最多的東西。然而,被評為21世界建筑奇跡中最不理性的建筑,就是庫哈斯設計的西雅圖公共圖書館(圖6)。

圖6 西雅圖公共圖書館
西雅圖公共圖書館是世界上排名第5的圖書館,折板狀的建筑外型呼應西雅圖錯移山脈與轉折河流的地景,11層樓高的體量里結合了傳統書籍與當代網絡的圖書館,是城市中不需預約的公共客廳。同時,也可謂是反理性的極致體現:單純的從超大規模的尺度與極不協調的比例而言,放在建筑設計的課堂里面,估計很難拿到及格的分數。然而,正是這座超凡的建筑顯示了建筑大師庫哈斯的雄心。庫哈斯設計的西雅圖公共圖書館試圖撥開概念的面紗,尋找到其背后的理性支撐。正是通過對圖書館形制的深入反思, 庫哈斯才得以有針對性的提出其空間布局策略,實現了對傳統圖書館從形式到內容的全面顛覆,通過設計實現都市建筑空間與媒體虛擬空間的首次結盟。
4.3.2 懸挑
反理性的其次體現就是超級大的懸挑。過去書本上面寫的懸挑長度往往為4 m上下,這個理論往往適用于傳統的鋼筋混凝土建筑。規范規定通常懸挑梁的截面高度取為其跨度的1/6,因此懸挑的長度往往受到了限制。可是新的技術與實踐(尤其是鋼結構與輕鋼結構)已經完全顛覆了經典的懸挑長度理論。其實最知名的懸挑建筑可能就是北京CCTV大樓。央視新址懸臂鋼結構即兩棟主塔樓分別以大跨度外伸部分在162 m以上高空懸挑75.165 m和67.165 m,然后折形相交對接,在大樓頂部形成折形門式結構體系。懸臂共14層,寬39.1 m,高56 m,用鋼量為1.8×104t,相當于將中國第一鋼廈深圳發展中心懸空建造,施工難度顯而易見。
更為典型的懸挑實例就是剛剛完成的深圳證券交易所營運中心(圖7)。同樣由庫哈斯設計,其獨特的“漂浮平臺”設計成為整座建筑最為矚目之處。大樓外觀為立柱形,分為塔樓和裙房兩部分,其中裙房位于塔樓中間部位,大廈底座被抬升至36 m形成一個巨大的“漂浮平臺”,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懸挑結構(東西向懸挑36 m、南北向懸挑22 m),被譽為世界上最大的空中花園(面積達1.58×104m2),平臺的“腰部”由一條鮮亮的紅色光帶“纏繞”,整體造型猶如一個漂亮的燭臺。漂浮平臺總用鋼量2.8×104t,比中國第一棟鋼結構大廈——深圳發展中心用鋼量還多1×104t。不過有意思的是,這三幢建筑都是由庫哈斯設計的,這個倒是應該引起我們的思考:這么巨大的懸挑帶來結構上的挑戰和巨大的審美學上的沖擊力,在經濟方面到底是否適合當下的中國現狀,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圖7 深圳證券交易中心
4.3.3 扭轉
反理性的再次體現就是超乎想象的扭轉,這里例舉中外各一個實例。近日,有網友在微博上發布照片稱,在京郊發現了一座“(鹵煮)大腸塔”。據了解,該大廈位于大興黃村,名為“興創大廈”(圖8)。此前也有人稱其為“呼啦圈”。其實,這種小尺度的形體扭轉,相對于國外的HSB Turning Torso,真的只是小巫見大巫了。

圖8 北京興創大廈
位于瑞典馬爾摩的扭轉大樓內擁有33種不同形式、共147間公寓,由于大樓從一樓到屋頂共扭轉了90°,所以每間公寓都擁有充足的自然光,這棟大樓的杰出設計,在法國坎城舉行的“世界房地產市場”頒獎典禮中,獲得最佳住宅類大獎。扭轉大樓的正式名稱,叫做HSB Turning Torso,是私人機構所興建的辦公與住宅大樓(圖9),位于馬爾摩的海岸地區,面向松德海峽,總共有54樓。設計者是Santiago Calatrava,他同時也是雅典奧運運動場與紐約WTC新建的地鐵站的建筑師。

圖9 HSB Turning Torso
4.3.4 極端反力學
反理性的最后體現就是上大下小的極端反力學。根據最基本的力學原理,基座大而結實,往上逐漸減小,從力學法則上來說,是最為經典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古埃及的金字塔以及中國的古塔,都是層層收進的意味,給人堅固,牢靠的感覺。然后同樣是到了近代,隨著結構技術的發展,這種經典的審美原則被打破。首當其沖的就是大師賴特的古根海姆博物館。中心展廳逐層向外越擴越大,給人一種動態的穩定感與視覺上的愉悅感。
其實國內最新的建筑:上海世博會中國館(圖10)更是反力學的典范。何鏡堂說:“看到同樣的事物每個人的觀點會各自不同。作為中國館設計者,我認同它宣示了中國精神。一百年中國被人欺負的日子結束了,莊嚴、繁麗的斗拱造型,給人以中國上升與自豪的感受”。高度69 m、總建筑面積16×104m2的中國館,其上大下小的倒金字塔造型,曾經引起了爭議。其實,它的做法的正是中國古建筑的一個經典構件:斗拱。

圖10 世博中國館
斗拱通過力學原理,將梁對外挑屋檐的受力傳輸到立柱,從而解決了大面積挑空屋頂的受力難題。斗拱向外出挑,使建筑物出檐更加深遠,造型更加優美、壯觀。在中國古代,斗拱是區別建筑等級的標志,越高貴的建筑斗拱越復雜、繁華。其實中國經典的構件斗拱本身就是反力學法則的經典元素,只是這種元素在古代是為了承托中國大屋頂的挑檐作用的。另外,諾曼福斯特設計的倫敦新市政廳(圖11),也是上部向外大懸挑的經典案例,具有非常強烈的不穩定性,同樣成為新的地標性建筑。

圖11 倫敦市政廳
5 結論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市場因為需要而存在。同樣在這個過程中,新聞傳媒也起到了巨大的刺激作用。
這個世界多元的,包容本身就是一種社會進步。當前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各種思潮、各種流派、各種審美觀念泥沙俱下。同時由于現在的空氣比以往更加自由,一些條條框框的東西逐漸被拆除、被摒棄,于是呈現出紛繁復雜的態勢:真與假一起登臺,美與丑一并呈現,善與惡相互交融,人們目不暇接,疲于辨別。我們不主張將高尚視為落伍,把低級奉為時尚;同樣排斥將傳統視為老土,把怪異視為新潮。但是我們同樣不主張一種新生事物剛一出現,就因為反駁聲不斷被扼殺。建筑設計也是如此,好的建筑形態會隨著時光的流逝沉淀下來成為經典,一時的花樣也同樣會隨著時間逐漸遠去。既要做得出經得住歷史檢驗的東西,又要有所創新,確實難以企及。相信隨著時代的進步,社會的發展,隨著越來越多的新的高技術的產生,隨著人們審美需求的不斷提高,相信人們會有越來越大的包容度。這才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與本源。
[1] 劉臨安,徐洪武.論古今城市地標建筑的作用[J].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學報,2008,(12)
[2] 朱一丁. 標志性建筑研究[J]. 寧夏工程技術, 2005,(3)
[3] (美)凱文·林奇.城市意象[M].方益萍,何曉軍,譯. 華夏出版社, 2001
[4] 吳煥加.現代西方建筑的故事[M]. 百花文藝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