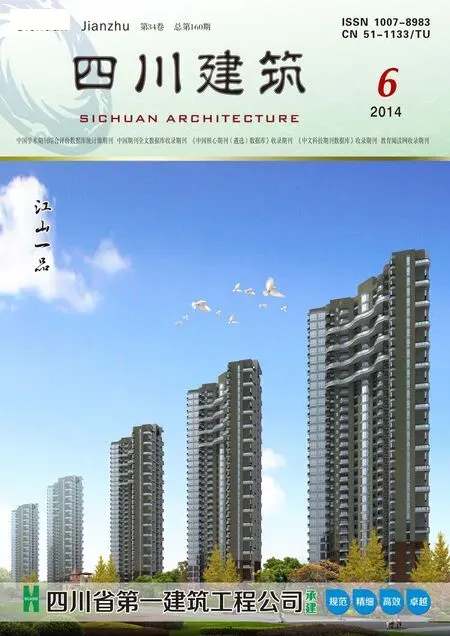矩形閉合型地下連續(xù)墻基礎地震動力響應分析
張世亮
(鐵道第三勘察設計院集團有限公司地質路基處,天津 300142)
1 國內外研究概況
在地下連續(xù)墻家族中,矩形閉合型地下連續(xù)墻是一個較為年輕的成員[1]。1979年,日本在東北新干線飯坂街道高架橋工程中首次采用矩形閉合型地下連續(xù)墻[2],代替了慣用的沉井式基礎。由于其不同于以往的橋梁基礎,有著良好的工程特性,矩形閉合型地下連續(xù)墻得到了日本工程界的高度重視,并已在日本取得了大量的應用[3]。迄今為止,日本已在20余座橋梁的100多個橋梁基礎中采用了矩形閉合型地下連續(xù)墻[4]。
盡管針對矩形閉合型地下連續(xù)墻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尚未涉及其在地震作用下的結構動力響應問題。本文基于PLAXIS 8.5有限元軟件,對矩形閉合型地下連續(xù)墻在地震作用下不同位置的加速度、位移等變化情況進行了研究,并對影響其動力響應的一些相關因素進行了分析,以期為進一步的矩形閉合型地下連續(xù)墻振動控制提供必要的技術參數(shù)。
2 計算模型及參數(shù)確定
2.1 模型的建立
使用Plaxis動力分析模塊可以分析結構在土體中的振動效果[5],本次數(shù)值模擬的結構模型為矩形閉合型地下連續(xù)墻,地基包括黏土與砂土。考慮到反射波的干擾,模型的邊界應遠離所研究的區(qū)域,故在矩形閉合墻靜力分析邊界條件的經驗基礎上[6],加大了水平向的邊界范圍,取為基礎承臺邊長的9倍,豎向取為墻深的2倍,具體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數(shù)值計算模型(單位: m)
由于實際上土體是半無限大介質,需要定義特殊的邊界條件。如果沒有吸收邊界,振動波會在模型邊界處反射,引起擾動。為了避免這種反射,在底部和左側邊界設置吸收邊界。同時,地震用施加在底部邊界上的指定位移來模擬,Plaxis可以通過SMC地震記錄[7]快捷的生成地震。模型采用平面應變15節(jié)點單元進行模擬,時間單位為秒,最終的模型及測點分布如圖2所示。

圖2 有限元數(shù)值模型及測點布置
2.2 參數(shù)的設定
地下連續(xù)墻及承臺采用彈性板單元進行模擬,而土體采用摩爾庫倫模型,由黏滯效應產生的物理阻尼用雷利阻尼來模擬,具體的結構及土體參數(shù)見表1及表2所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通常情況下動荷載是高速的且引起的是小應變,因此土體的動態(tài)剛度通常都比靜態(tài)剛度大。

表1 結構單元參數(shù)

表2 土體參數(shù)
為了盡可能地反映模型真實的情況,在地下連續(xù)墻承臺上部施加均布荷載(50kPa)。計算分兩步進行,第一工序為地下連續(xù)墻受上部荷載的靜力“塑性計算”,第二工序為輸入地震的“動力分析”。為了詳細分析地震作用,在第二工序計算開始前重置位移為0。本次數(shù)值模擬分別選取了典型的地震記錄UPLAND地震波的SMC文件作為激勵輸入,進行結構的動力響應分析。本次數(shù)值模擬采用的地震波是地表東西向水平加速度的記錄信號,具體的波形及參數(shù)如圖3所示。

圖3 采用的地震波波形
3 結果分析
基于前文的基本算例,對UPLAND地震作用波作用下的矩形閉合型地下連續(xù)墻結構動力響應進行分析。
根據(jù)數(shù)值模擬結果,可得出不同動力時間下地下連續(xù)墻整體的位移情況,取30s時結構的最終變形情況作為研究對象(圖4),可以看出閉合型地下連續(xù)墻基礎由于本身剛度較大,其變形存在一定的整體協(xié)調性,在地震的全過程中幾乎都呈現(xiàn)出剛體的變形特性。因此研究其變形可取典型點(圖2所示的測點),分別繪出各地震波工況下結構的位移及加速度時程曲線(圖5)。

圖4 地震波作用下地下連續(xù)墻墻體變形情況
從圖5可以得出:
(1)從整體而言,在兩種地震波下,地下連續(xù)墻的變形都隨著地震加速度的變化而產生起伏,并最終趨于穩(wěn)定。由于土體存在著黏滯效應,墻身位置距離震源越近,其產生變形量也越大。
(2)在UPLAND波下,在前期基礎的水平變形量不大,豎向上呈不斷向下沉降的趨勢。隨著地震波的變化,基礎的水平位移逐漸增大,豎向位移趨于穩(wěn)定,基礎變形整體呈向左傾的趨勢。基礎的最大水平位移值為7 cm,最大豎向位移約-5 cm,其變形也經歷了水平方向上先左至右,豎向上先下后上的過程。
(3)在UPLAND波下,基礎的豎向在地震波加速度從最小變到最大再減小的過程中,都會產生先沉降再上浮的變形過程,其拐點變化時間為該位置加速度到達極值的動力時刻。


圖5 UPLAND波作用下地下連續(xù)墻墻體位移時程曲線
考慮結構本身的加速度變化,繪出地震波作用下地下連續(xù)墻墻體加速度時程曲線,如圖6所示。

圖6 UPLAND波作用下地下連續(xù)墻墻體加速度時程曲線
由圖6可以看出,由于土體的黏滯效應,相同動力時間下,結構的加速度值與地震波的加速度值存在較大的差別,但整體變化趨勢較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UPLAND波在前30 s時間中,相同加速度幅值的持續(xù)時間較長,導致結構在15 s左右的動力時間段的加速度值超過了地震波的加速度值,最大加速度值達到了300 cm/s2,而實際地震波的最大加速度為200 cm/s2,這是地震波共振造成駐波的結果。同時可以看出,在地震過程中,閉合型地下連續(xù)墻墻身的最大加速度位于底部,而頂部的加速度值大于中部,這是因為頂部沒有土體上覆蓋,存在著一定的放大效應。
從基礎的位移方面,結合地震波的變化可知,基礎位移量的大小主要決定于地震波加速度的大小。從監(jiān)測點位移的變化情況來看,基礎水平位移量的大小與地震波相近加速度下的持續(xù)時間具有較大的關系,如UPLAND波作用后期時,基礎水平位移不斷增加(圖5(a));而基礎的豎向位移與地震波下墻體加速度的大小與持續(xù)時間有關(圖6)。
4 結論
基于有限元Plaxis 8.5軟件,對閉合型地下連續(xù)墻的地震動力響應進行分析,得出了以下結論:
(1)閉合型地下連續(xù)墻基礎由于本身剛度較大,其變形存在一定的整體協(xié)調性,在地震的全過程中幾乎都呈現(xiàn)出剛體的變形特性。
(2)在地震波下,地下連續(xù)墻的變形隨著地震加速度的變化而產生起伏,并最終趨于穩(wěn)定。由于土體存在著黏滯效應,墻身位置距離震源越近,其產生變形量也越大。
(3)在UPLAND波下,基礎變形整體呈向左傾的趨勢。基礎經歷了水平方向上先左至右、豎向上先下后上的過程。
(4)在地震過程中,閉合型地下連續(xù)墻墻身的最大加速度位于底部,而頂部的加速度值大于中部,這是因為頂部沒有土體上覆蓋,存在著一定的放大效應。
[1] 叢藹森.日本的一種新型橋梁基礎——地下連續(xù)墻沉井[J].國外橋梁,1990,(2):20-30
[2] 棚村史郎.鉄道橋基礎の特微と現(xiàn)狀[J].橋梁と基礎,2009,43(8):27-30
[3] 吳九江,程謙恭,文華.地下連續(xù)墻基礎在日本的多樣化發(fā)展[J].工業(yè)建筑,2013,43(1):70、144-149
[4] 程謙恭,文華,宋章.地下連續(xù)墻橋梁基礎承載機理[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
[5] R.B.J. Brinkgreve,W. Broere,D. Waterman. Plaxis2D manual books,2006
[6] Qiangong Cheng, Jiujiang Wu, Zhang Song, Hua Wen. The behavior of a rectangular closed diaphragm wall when used as a bridge foundation. Frontiers of Structural and Civil Engineering, 2012, 6(4): 398-420
[7] 曹光喧.NSMP天然地震波SMC文件記錄格式及其應用[J].工程與建設,2006,20(5):502-504